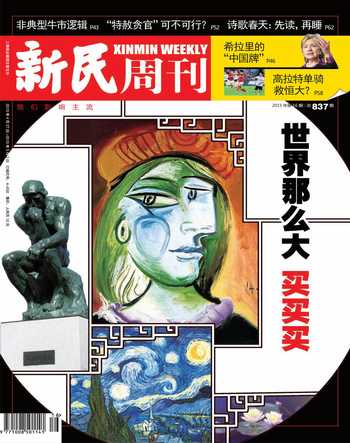阿七婆的書屋
江澤涵
回鄉的第二天,天空洗過似的。
阿七婆家到了,不,是阿七婆的書屋到了。三間小屋,九柜子書,十二張矮方桌,照例座無虛席,有的還得蹲門檻、靠墻壁。木窗邊的一個男孩,正全神貫注地讀著。我拍了拍他的小肩,問阿七婆的去處。他說:“七婆婆去田里啦。”
這兒原本不是閱覽室,而是一個小書攤,也就一鋼絲床的書。
二十年前的一個夏日,阿七婆在山坡上被一場暴雨襲擊,滾下了坡,左腿便落了殘疾。阿七婆想自己也一把年紀,不再適合上山下地。鄉下孩子不是上山玩耍,就是下水鬧騰,正是長學問的年齡呀,可這也怪不了他們,教科書早就啃爛了,其他可看的卻沒有。
阿七婆覓到了商機,她購了兩百冊書,擺個書攤安度晚年。果然,我們都往她那兒趕。一人拿一冊,津津有味地看著,一呆就一上午,只是她一本也沒有賣出去。
書頁皺了,邊角卷了。阿七婆的眉頭也鎖緊了。幾天后,阿七婆改賣書為租書。一天一角錢。可我們還是起早來看,摸黑回家。只有一些大人晚飯后來借。一天就幾塊收入,算上折舊,可賠慘嘍。我經常聽見阿七婆嘆氣,極其輕微,卻綿延而幽長。
再幾天后,阿七婆騰出了一間小屋,村里第一個免費閱覽室成立了。阿七婆扛起鋤頭,拎著籃子,一搖一擺去了菜地。閱覽室無須看管。天黑后,大家自會整理好。大人怕弄亂或丟失,也不借,就關門前來看一會兒。若誰見書掉頁,自會裝訂好的。
書屋的事像生了翅膀越傳越遠。縣里鎮上每年也會送來幾十冊書。在外工作的年輕人來看阿七婆,也會摸幾個小錢,阿七婆都拿去換了書。書屋就越來越擁擠了。幾年后,阿七婆的左鄰獻出了一間屋子。又幾年,右鄰也讓了一間屋子。
這些年來,一所磚瓦小學(如今已改成了村務辦),四個老師,累計有一百多個學生,先后考到了鎮初中,他們的成績令那邊的老師都驚嘆,至于課外積累嘛,也令那邊的孩子羨慕。
這回村里又傳著一件喜事:毛家三兄妹在外歷練五六年,返鄉后建了半座度假村,帶動了全村經濟,還籌劃建一座真正的公益圖書館,并已開始動工,打算聘請阿七婆擔首任館長。
“嗒——嗒——”阿七婆搖擺著回來了。歲月匆匆,她已八十多了,所幸身子骨硬朗,白發挽起的髻子也很整齊,素凈的臉上未見多少老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