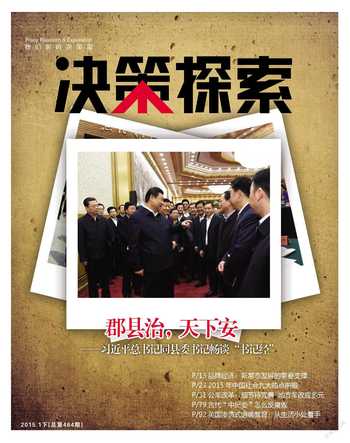誠信是法治精神的重要倫理基礎
楊伊佳 楊河
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要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既重視發揮法律的規范作用,又重視發揮道德的教化作用,以法治體現道德理念、強化法律對道德建設的促進作用,以道德滋養法治精神、強化道德對法治文化的支撐作用。誠信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歷史和現實的實踐證明,培育現代誠信觀念是在全社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建設社會主義法治文化的重要倫理基礎。
法律是人類文明的重要成果,它使得人們在復雜的社會交往活動中有了一定之規,保證了社會在經濟、政治、文化各種矛盾沖突中相對穩定的存在和發展,一個國家法治的水平和程度是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如何的重要標志。
中國共產黨高度重視法治建設,新中國成立不久,毛澤東就親自主持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個根本大法,并著手調研和制定各方面的法律。“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伴隨著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反思和探索,中國的法制建設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歷史機遇,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是,作為國家政治制度和治理體系的核心,中國現代法律體系和法治制度的建設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只能在實踐中逐步推進。相對于發達國家在數百年間積累起來的近現代法治文化,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很多的工作要做,還有較長的路要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轉化的過程中,中國的法制建設面臨著新的形勢。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形成要求建立一系列與此相適應的法律制度,而我們在這方面的工作還不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推進在帶來巨大經濟效益的同時,也將逐漸滋生的利己主義和商品拜物教等觀念通過商品交換原則的泛化滲入了社會政治和文化生活,引發了各種各樣的違法亂紀。近年來,一些政府官員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現象多有發生,權錢交易、行賄受賄、貪污腐敗、侵犯群眾利益的事件屢禁不止甚至逐年增多,已經危及到黨的執政基礎。這固然與法律不健全所留下的一些“灰色地帶”,使事實上的“犯罪”難以進入法律的懲罰范圍有關,但是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的大量存在也說明了中國社會法治觀念的淡漠和法治精神的匱乏。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過程中,在全社會弘揚敬畏、篤信和踐行法律的法治精神,引導人們自覺知法、尊法、守法、執法、護法,是推進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其意義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能超過了法律制定本身。
法治精神本質上是一種對法律權威敬畏的信念,這種信念的倫理基礎是誠信,因為法律所涉及的是人與人之間具有“契約性”的社會關系,它要求法律的制定、執行和監督都必須貫徹誠信的原則,這是法律權威性之公正力量的重要來源。
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要立足中國文化傳統。中華民族具有崇尚誠信的歷史傳統。東漢《說文解字》就專門對誠信做了注解:“誠,信也。”意為誠實與守信二者相通,互為印證。“誠”主要是指“內誠于心”,更多地是對個體的內在道德要求;“信”主要是指“外信于人”,更多地是對社會群體之間交往的道德要求。孔子將誠信視為個人安身立命的基礎,他說:“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論語·為政》)人缺少了誠實守信的品德,就如同車子沒有將車轅與軛連接起來的木銷子而無法行進一樣,在社會上寸步難行。
做人要講誠信,治國也離不開誠信。《左傳》講:“信,國之寶也。”孔子認為一個國家可以“去食”“去兵”,但不能“去信”。他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論語·顏淵》)
何以踐行誠信?中國人講的是以誠達信,即建立在仁愛基礎上的知行統一,強調修身為本,認為齊家、治國、平天下,都以自我修養為根本,誠為自我修養之要義,孟子講:“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孟子·離婁上》)程顥、程頤指出:“學者不可以不誠,不誠無以為善,不誠無以為君子。修學不以誠,則學雜;為事不以誠,則事敗;自謀不以誠,則是欺其心而自棄其忠;與人不以誠,則是喪其德而增人之怨。”(《河南程氏遺書》卷二十五)說明“誠心正意”對于“做人”“做事”“做學問”的重要意義。
始有真誠之心,方行信義之事。信守諾言、身體力行、表里如一是中國人對以誠達信的基本要求。為政者,要取信于民:“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語·子路》)政府官員誠信,民眾才可能誠信。在中國人看來,能否做到“言必信,行必果”關系到一個人的人格高下和事業成敗。
數千年來,這種誠信觀已經成為中華民族的道德基因,一代一代傳承下來,滲透在博大深厚的民族精神中。中國共產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有它的文化底蘊;做老實人、說老實話、辦老實事是中國共產黨員的基本道德準則;牢固樹立和忠實踐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信念既體現了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和本色,也體現了中國人民對先進政黨的道德期盼和要求。正是靠著這種取信于民、說話算話、擔當負責的精神和作風,中國共產黨才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被賦予了執政的重任。
培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誠信價值觀,還需要批判性地借鑒西方誠信觀的合理因素。西方誠信觀念起源于古希臘,誠信被看作是公民最重要的德性之一。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中說:“虛偽是可譴責的,誠實則是高尚的和可稱贊的!”在希臘文明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古羅馬社會,形成了較為完備的法學理論和法律制度,誠信是最重要的法理原則,它不僅存在于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中,也被要求存在于法律之外的一切可能的契約關系中。
羅馬法中的契約誠信理念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守約被視為是人的本性,有約必踐、違約必罰,任何人都必須誠實信用地行使其權利并履行其義務成為基本的正義原則。中世紀誠實信用被視為信奉上帝的基本品質,是對上帝的承諾,誠信被賦予神圣的意義,成為基督教世界的共同價值觀。15世紀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用天職的概念把宗教活動和世俗經濟生活聯系起來,認為誠實信用不僅為上帝所認可,也是在經商中獲利的重要法寶。
資本主義形成于市場經濟的高度發展中,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說:“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詩般的關系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于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害關系,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系了。”為了避免這種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中可能出現的爾虞我詐、唯利是圖、相互傾軋而致使社會失范,西方古典經濟學家一方面提出“經濟人”假設,認為人具有理性,可以做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另一方面又提出社會公正原則,誠信就是實現這一原則的重要條件。這一原則在經濟活動中逐漸轉化為一種特殊的信用資本,形成為一種制度,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康德進一步從哲學上論證了誠信之于人的重要意義,按照“人是目的”這一絕對命令的要求,誠信被看作是一種對他人的完全責任,他說:“如果一個人認為自己在困難的時候,可以把隨便不負責任的諾言變成一條普遍規律,那就會使人們所有的一切諾言和保證成為不可能,人們再也不會相信他所做的保證,而把所有這樣的表白看成欺人之談而作為笑柄。”因此,欺詐和謊言在任何情況都是不允許的。
恩格斯認為,西方現代信用原則的確立,是政治經濟發展規律的要求,他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指出:“現代政治經濟學的規律之一就是:資本主義生產越發展,它就越不能采用作為它早期階段的特征的那些小的哄騙和欺詐手段。……的確,這些狡猾手腕在大市場上已經不合算了,那里時間就是金錢,那里商業道德必然發展到一定的水平,其所以如此,并不是出于倫理的狂熱,而純粹是為了不白費時間和辛勞。”馬克思深刻地揭示了資本主義信用制度的兩重性,指出,資本主義“信用制度以社會生產資料(以資本和土地所有權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壟斷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動力”。這種信用制度的歷史地位就在于:“一方面,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動力——用剝削他人勞動的辦法來發財致富——發展成為最純粹最巨大的賭博欺詐制度,并且使剝削社會財富的少數人的人數越來越減少;另一方面,造成轉到一種新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
西方這種誠信觀發展到今天,形成了三個重要的特性:一是被視為交換正義的重要原則,與西方信用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密切相關,將個人的誠信道德融入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中;二是被視為維系政府與社會秩序的重要基礎,與西方的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密切相關,將個人的誠信道德融入法治社會的運行規則中;三是被視為宗教信仰的重要戒律,與西方的生活方式發展密切相關,將個人的誠信道德融入世俗生活的神圣意義中。
雖然建立在私有制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經濟信用制度和政治法律制度有著自己固有的階級局限性,貫徹于其中的契約誠信觀也不及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觀所要求的自主自覺意識,但是它超越了基于血緣宗法關系的“熟人社會”講求誠信的“私人”空間意義,賦予誠信以基于現代交往關系的“經濟社會”講求誠信的“公共”空間意義,使誠信走進了人們復雜多樣性的職業生活,成為一種制度化的道德律令。這對于我們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進行現代化建設中培育和倡導具有法治精神的誠信觀念,無疑有著十分現實的借鑒作用。
當前,我們已經進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歷史新階段。國家和社會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共同發揮作用,只有將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才能實現真正的善治。法律的權威源自人民的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只有真實體現人民意志的法律才能獲得人民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也只有人民內心擁護和真誠信仰的法律才能有效實施。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作為指導,科學地繼承和借鑒中國傳統文化的誠信觀和西方文化的誠信觀,形成適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要求的現代誠信觀,使之成為在全社會弘揚法治精神的社會倫理基礎,是推進法治中國建設的題中應有之義。
(作者系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博士研究生、教育部高等學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