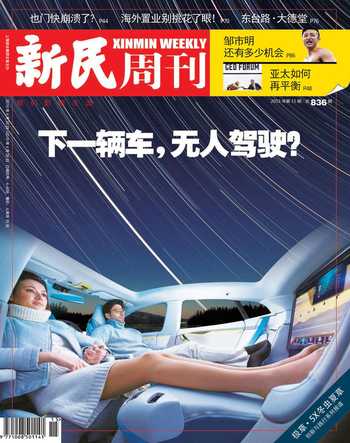到中國去,有拍不完的抗日劇!
闕政
在日本的時候,井上朋子和她同年齡的女星差不多,演的大都是青春愛情劇,因為《導盲犬小Q的一生》而為人熟知。
一個偶然的機會,她來到中國,被趙寶剛導演選中,參與拍攝2007年的抗戰電視劇《夜幕下的哈爾濱》,從此開始了她在中國的演藝事業第二春。
巧合的是,自此之后,她又接連拍攝了多部抗戰連續劇——《京武傳奇》、《斷喉弩》、《尖刀戰士》、《雪狼谷》、《義勇義勇》……幾乎每年都參與一部抗戰劇演出的井上朋子,如今定居在北京,有一個看起來挺尷尬的身份:一位來中國拍抗日劇的日本女演員。
演抗日劇的日本人不止她一個
其實井上朋子最早來的是上海。2006年,她受朋友之邀來滬,游玩的同時,也想謀求海外發展。“當時日本的電視劇連年減產,我想去國外演戲,就在上海找了一對一的語言老師,先學了一年中文。”朋子說。
最初,語言老師有位朋友是雜志社編輯,于是推薦朋子去當平面模特、接拍廣告。2007年時,趙寶剛導演的《夜幕下的哈爾濱》劇組找到她,這部電視劇也成為朋子在中國演藝界的處女作。戲中,她出演一名日本軍官的女兒。
初來乍到的朋子雖然知道電視劇的內容是關于抗戰,但80后的她,本人對抗日戰爭這段歷史也沒有多少概念。“當時只知道是要演一部關于1930年代的時代劇,覺得對自己會是一個挑戰,就接受了。”
但在拍戲過程中,她明顯感受到了來自中國演員的不解。一起演戲的中國演員會問她:你覺得戰爭是中國的錯,還是日本的錯?還有一位演員一直盯著她追問:你知道南京大屠殺死了多少人?“我答不上來。”朋子說,“在日本,沒有人會問我這么尖銳的問題,我覺得有點可怕。而且,拿從前日本軍隊的行徑來攻擊一個個人,我也覺得不太對。”
自稱“連日本的左右翼都分不清”的井上朋子,來中國拍戲的第一感覺就是:許多中國人還是很明顯地討厭日本人。
而她在中國拍抗日劇的選擇,在日本并沒有受到輿論攻擊。“身邊的朋友鼓勵我,在中國要努力演戲。”
當年日本演員香川照之也在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里演過日本軍官,形象不無殘暴愚蠢的一面,但是演完之后,在日本反而人氣大漲,晉升為一線演員。然而井上朋子現在的處境更為尷尬——她參演的一部分抗日劇,未必都忠實于歷史,反而可能有“抗日神劇”之嫌。
對此,朋子也表示無奈:“我對歷史不太了解,也不好多說什么。”有時候她會給導演提意見,但針對的問題大都是表演領域,而非歷史或政治。“有些地方我會覺得演得有點太夸張了,中國電視劇似乎喜歡七情上面的演出,但是日本會比較推崇‘無表情’的表演,會視之為一種美德——就好比說痛哭,哭到后來也是無聲的,在中國表演時可能就需要扯開嗓子哭。不過說歸說,決定權還是在導演手上,演員要服從導演。”
一直演抗日劇,一來是因為形象和語言的限制,朋子的長相很日式,口語還不夠說中文臺詞。二來也是因為,抗日劇的體量太大。“我聽朋友說,中國的電視劇有70%都是抗日劇!”——當然沒有70%那么夸張,但二三成的確是事實。怪只怪抗戰劇容易過審,多少暴力血腥便假汝之名大行其道。
如果留心看抗日劇的話,還會發現一個趨勢:從前在劇中演日本人的一般是中國演員,傳說中橫店的職業龍套們一字排開等待抗日劇“召喚”——換上軍裝貼個八字胡上場,過不了多久就被打死,接著換另一個劇組再死過,一天死七八次都不奇怪……然而現在,很多日本官兵的角色都說得一口流利的日語,看口型絕不是后期配音。實際上,越來越多的日本人加入到了抗日劇的演出。
“我也聽說過,一些來中國讀書的日本留學生,會去劇組演日本人。”朋子說,“抗日劇似乎變成了他們謀求在中國發展的敲門磚一樣。”

要交流,不要獵奇,是井上朋子對兩國的期待。

井上朋子在《中日新視界》擔任嘉賓。
不要獵奇,要交流
最近,廣電總局發話:“對過度娛樂化的抗戰劇不得發證。”看起來,抗戰劇泛濫的熒屏環境將會有所改變。拍了七八年的抗日劇,朋子也覺得有些厭倦:“感覺題材、故事都相當雷同。生命有限,還是要做些更有價值的事吧。”
今年4月,她來到上海,作為嘉賓,出席上海外語頻道(ICS)新創辦的《中日新視界》——這是目前全國唯一一檔由電視臺自制的日語新聞專題類節目,也是去年剛剛謝幕、有著將近20年歷史的《中日之橋》的最新升級版,話題集政治、經濟、文化、科技于一體。除此之外,朋子還去上海外國語大學作演講,與日語專業的學生分享她在中國當演員的心得。今后,她還會以特邀主持人身份亮相《中日新視界》。“除了演戲,我還想把時間花在改善中日關系、促進中日文化交流上。”朋子說。
因為交流一旦少了,獵奇就有了土壤。
中國盛行的“抗日神劇”,日本新聞也播出過其中“手撕鬼子”的片段,稱之為“把打仗拍得像打游戲”。反過來,日本流行的綜藝節目,也會特意選擇探訪中國偏遠的小山村,將“女孩1500日元出售發辮相當于全家一個月生活費”作為嘩眾取寵的賣點。
雙向的獵奇,或是出于心理宣泄的需要,或是出于對優越感盲目的追逐,無不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紙上得來終覺淺。朋子也是要等自己來到中國之后,才感受到真實的中國,真實的中國城市。“剛到上海的時候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適合居住的地方,物質產品基本都和日本同步。”朋子說,“有一次走在路上不小心撞到一個人,對方竟然用日語跟我說‘對不起’,我才知道原來有那么多日本人生活在上海。”
后來在北京定居,朋子的住所鄰近日本大使館。2012年中日矛盾激化的時候,會看到使館附近的反日游行:“警車停滿了一路,一些日料餐廳怕被人砸,掛起中國國旗。我在外面拍戲,旁邊一輛車開過去,車尾會貼著‘釣魚島是中國的’。”
即使小到生活細節,中國人以為的日本和實際的日本,也有不小距離。一般說到日本,總是少不了這些標簽:櫻花、壽司、新干線、和服、漫畫,現在又多了電飯煲、馬桶蓋……朋子身邊的中國朋友有時候也會問一些讓她驚訝的問題——你媽媽在家穿和服嗎?你爸爸會打你媽媽嗎?你們平時都會自己做壽司吧?“和服、壽司、大男子主義,這些仍然是加給日本的標簽。其實我們平時吃壽司也是去壽司店的!”
當然,她自己給中國的關鍵詞,從前也是最常見的那些——世界遺產、萬里長城、故宮、兵馬俑、青島啤酒……現在呢?“現在又加了幾個:紅色、人多、嗓門大,還有依賴手機的低頭族特別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