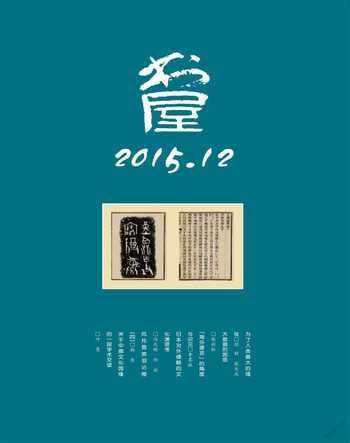黃紹湘:天不容偽
《書屋》雜志在2007年第二期發(fā)表了武漢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劉緒貽的《我研究美國(guó)史的經(jīng)歷》一文(以下簡(jiǎn)稱為《經(jīng)歷》)。劉緒貽在文中一開始就寫道:“我發(fā)表過(guò)研究美國(guó)史甘苦的文章。承蒙《書屋》編輯部的信任,讓我再系統(tǒng)地談?wù)勎已芯棵绹?guó)史的經(jīng)歷。我覺(jué)得《書屋》編輯部的這種意圖必有其理由,所以樂(lè)于遵命。”劉緒貽在該文中總結(jié)了他的經(jīng)歷,強(qiáng)調(diào)他是“發(fā)展馬克思主義”的。為了突顯這一點(diǎn),他全面反駁了上級(jí)對(duì)他的批評(píng),更不惜以不實(shí)之詞,對(duì)堅(jiān)持以馬克思主義研究美國(guó)史的黃紹湘教授進(jìn)行人身攻擊。由于劉緒貽的文章流傳甚廣、影響深遠(yuǎn),致使黃紹湘蒙受了不公正的名譽(yù)損害。
按照劉緒貽在其《經(jīng)歷》一文中所述:“當(dāng)時(shí)我研究美國(guó)史,經(jīng)常感到一種‘緊跟’的負(fù)擔(dān)。美國(guó)史中哪些部分可以研究,哪些部分不可以研究;美國(guó)歷史發(fā)展進(jìn)程遵循什么規(guī)律;美國(guó)歷史上人物和事件應(yīng)如何評(píng)價(jià)等等,都是要有指示,尤其是最高指示作根據(jù)的。違反或背離這種根據(jù),不獨(dú)研究成果不能問(wèn)世,而且會(huì)招引批判甚至禍災(zāi)……還得經(jīng)常打聽關(guān)于美國(guó)的事務(wù)最近有什么最高指示,發(fā)了什么最新文件,以便找來(lái)閱讀,作為緊跟的根據(jù),否則寸步難行。”由此可見,劉緒貽自己當(dāng)時(shí)是以跟風(fēng)的辦法來(lái)進(jìn)行他的美國(guó)史研究的。
劉緒貽在建國(guó)初期就加入了中國(guó)共產(chǎn)黨,宣誓要為了共產(chǎn)主義的事業(yè)而奮斗終生,但是這卻并不一定成為他的真正信仰。改革開放以來(lái)的寬松政治氣氛,才使得劉緒貽能夠暢所欲言。2011年5月,在騰訊《大師》第三十六期上,劉緒貽與沈洪聯(lián)名發(fā)表題為《劉緒貽:一個(gè)自由主義者的生活態(tài)度》長(zhǎng)文,其中劉緒貽明確描述了他目前所真正信仰的主義并不是馬克思主義,而是像瑞典那樣的社會(huì)民主主義:“我當(dāng)時(shí)考慮到,二戰(zhàn)以后,法西斯主義完蛋了,到了九十年代,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也完了。還有一種是美國(guó)的羅斯福新政式的國(guó)家壟斷資本主義,他還存在。還有一種就是民族社會(huì)主義,這四種。這幾種當(dāng)中,從我的想法,我感覺(jué)到將來(lái)整個(gè)人類的前途,主要是向社會(huì)民主主義發(fā)展,就按照瑞典這個(gè)道路前進(jìn)。我就希望大家能夠看了這個(gè)書(按:該書即為劉緒貽在香港出版的《簫聲劍影:劉緒貽口述自傳》)以后,就覺(jué)得將來(lái)這個(gè)社會(huì)應(yīng)該向這個(gè)道路走,只有這個(gè)才有前途,我寫這個(gè)書主要的目的就是在這兒。”
在該文中,劉緒貽還進(jìn)一步表述他的真實(shí)觀點(diǎn):“中國(guó)人他所想的宇宙,都是他空想出來(lái)的,而美國(guó)人他是從一點(diǎn)一滴研究,這樣慢慢積累起來(lái)的,所以美國(guó)他有科學(xué)。”又說(shuō):“因?yàn)槲易鰧W(xué)問(wèn),我是不在乎毛澤東怎么想,馬克思怎么想,我怎么想就怎么想。”
再回顧一下劉緒貽在《經(jīng)歷》一文中是如何評(píng)價(jià)自己的工作的:“(一)我和同僚、研究生一起沖破了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個(gè)禁區(qū)。(二)我成功地為羅斯福‘新政’翻了案。(三)我提出了兩個(gè)新概念。(四)我提出了兩條壟斷資本主義發(fā)展的新規(guī)律。(五)我發(fā)展了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階級(jí)斗爭(zhēng)原理和列寧關(guān)于壟斷資本主義亦即帝國(guó)主義的理論。”
劉緒貽“沖破了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這個(gè)禁區(qū)”的說(shuō)法,十分含混籠統(tǒng),缺乏事實(shí)根據(jù);他也沒(méi)有認(rèn)識(shí)到,在美國(guó)乃至全世界羅斯福“新政”都從未曾有過(guò)什么定案,那么他又從何來(lái)翻案呢?至于他的第三、四、五條,也只是他的一家之言。
劉緒貽在上個(gè)世紀(jì)八十年代初期發(fā)表的涉及馬列主義的文章,很快就受到了國(guó)外的注意。1983年,劉緒貽接到美國(guó)洛克菲勒基金會(huì)的邀請(qǐng),準(zhǔn)備1984年6月去意大利的貝拉焦參加一個(gè)名為“外國(guó)人心目中的美國(guó)史”國(guó)際學(xué)術(shù)會(huì)議,并寫了一篇準(zhǔn)備提交會(huì)議的論文《美國(guó)壟斷資本主義發(fā)展史與馬列主義》。
黃紹湘敏銳地察覺(jué)到了劉緒貽的新觀點(diǎn),而且果敢地在當(dāng)時(shí)“馬克思主義過(guò)時(shí)論”的思潮下,先后發(fā)表了三篇文章,旗幟鮮明地提出要堅(jiān)持以馬克思主義來(lái)指導(dǎo)美國(guó)史研究,并對(duì)劉緒貽關(guān)于羅斯福“新政”的觀點(diǎn)進(jìn)行了未指名的學(xué)術(shù)批評(píng)。劉緒貽隨即以“與黃紹湘同志商榷”為副標(biāo)題,做了反批評(píng)。然后,黃紹湘再以“答劉緒貽同志”為副標(biāo)題,深入展開爭(zhēng)鳴。
之后,劉緒貽沒(méi)有再發(fā)表文章,這場(chǎng)正常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似乎也就到此罷休。但是,2001年劉緒貽在他的《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以來(lái)美國(guó)史論叢》中,附了一個(gè)據(jù)稱是1999年寫的后記,解釋:“此文發(fā)表后,黃紹湘教授曾在《世界歷史》1985年第八期上發(fā)表文章進(jìn)行答辯。我本來(lái)準(zhǔn)備寫文章爭(zhēng)鳴,但后來(lái)聽從了朋友們善意勸告:是非曲直,讓讀者去評(píng)論。于是,我就未再為此專門寫文章。”劉緒貽愿意保留自己的觀點(diǎn)、不想進(jìn)一步爭(zhēng)鳴,本來(lái)是無(wú)可非議的;但是他在該書的序中卻又提出:“要為羅斯福‘新政’翻案就很可能受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的攻擊,因而具有一定的風(fēng)險(xiǎn)。后來(lái)我的確一再遇到這種風(fēng)險(xiǎn)。”劉還稱“頻遭阻抑,屢挨悶棍”,看來(lái)他是把這場(chǎng)正常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稱之為“阻抑”、“悶棍”了。劉緒貽不繼續(xù)與持有不同觀點(diǎn)的人展開爭(zhēng)鳴,卻給對(duì)方扣上一頂“自命為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主義者”的帽子,這種做法實(shí)在令人無(wú)法認(rèn)同,難怪他在后來(lái)要發(fā)表針對(duì)黃紹湘的不實(shí)之詞,也就不再遵循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的正途了。
2012年8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的記者專函向劉緒貽《經(jīng)歷》一文中的以下文字求證:“……此文發(fā)表后,引起較廣泛共鳴,有些出版物全文轉(zhuǎn)載。但是,由于此文對(duì)于‘新政’的看法,和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理事長(zhǎng)黃紹湘教授美國(guó)史著作中對(duì)于‘新政’的看法很不相同,她就寫了《開創(chuàng)美國(guó)史研究的新局面》和《開創(chuàng)我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新局面的淺見》兩文,不點(diǎn)名地對(duì)我的觀點(diǎn)進(jìn)行批駁。1985年,《世界歷史》又先后發(fā)表了我和黃先生爭(zhēng)鳴文章。本來(lái),學(xué)術(shù)爭(zhēng)鳴應(yīng)該是很正常的事情,對(duì)發(fā)展學(xué)術(shù)有好處。但是,可能由于支持我的觀點(diǎn)的人較多,黃先生就不再遵循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的正途,卻寫信給她的朋友、當(dāng)時(shí)中央政治局宋平常委告了我的狀,說(shuō)我把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領(lǐng)導(dǎo)得脫離了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宋平同志將此告狀信批轉(zhuǎn)給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院長(zhǎng)胡繩處理,胡又將信批轉(zhuǎn)給該院所屬世界歷史研究所,也就是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的掛靠單位。該所雖然并不支持黃先生告狀信(盡管黃是該所研究人員),但它頂不住那么大政治壓力,只好將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秘書處轉(zhuǎn)到南開大學(xué)去了事。”
黃紹湘的家人根據(jù)事實(shí),當(dāng)即回函反駁了劉緒貽針對(duì)黃紹湘的寫信告狀、迫使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秘書處遷址的不實(shí)之詞。《南方人物周刊》在2013年3月11日,發(fā)表了題為《劉緒貽 百歲老人看中國(guó)》。該文依然提到了黃紹湘教授的名字及她與劉緒貽之間存在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但是已經(jīng)摒棄了劉緒貽上述不實(shí)之詞。謠言止于智者。
然而,經(jīng)過(guò)我們的調(diào)查,發(fā)現(xiàn)包括“百度·百科”、“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網(wǎng)站”等幾十家網(wǎng)站和書刊,全都未加核實(shí)地轉(zhuǎn)載了劉緒貽《經(jīng)歷》的全文、或者摘登了包括上述不實(shí)之詞的文字。針對(duì)黃紹湘的不實(shí)之詞,就此不脛而走,在美國(guó)史學(xué)界和網(wǎng)絡(luò)上廣泛流傳。甚至于在《百度·百科》詞條“劉緒貽”中,“與黃紹湘論戰(zhàn)”被列為劉緒貽人生的四大經(jīng)歷之一,而且是解放以后的唯一經(jīng)歷。
那么,事實(shí)真相又是如何呢?
首先,當(dāng)時(shí)宋平同志是中央組織部長(zhǎng),并不分管人文科學(xué)、教育、意識(shí)形態(tài)等問(wèn)題。根據(jù)我們了解的事實(shí)真相,黃紹湘作為宋平的同學(xué),雖曾與他通過(guò)信,但是完全沒(méi)有涉及劉緒貽及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的問(wèn)題,更無(wú)告狀之事。
至于劉緒貽認(rèn)為可能由于支持他的觀點(diǎn)的人較多,黃紹湘就會(huì)去“告狀”,這實(shí)在是違反歷史事實(shí)的一種主觀臆想。黃紹湘在學(xué)生時(shí)代就為了抗日救國(guó)成為“一二·九”運(yùn)動(dòng)骨干,由清華大學(xué)全體學(xué)生選舉為北平學(xué)生救國(guó)聯(lián)合會(huì)代表,后來(lái)加入了共產(chǎn)黨(那時(shí)劉緒貽也在清華大學(xué));她由黨組織資助赴美留學(xué)時(shí)又積極參加美國(guó)共產(chǎn)黨中國(guó)局領(lǐng)導(dǎo)的進(jìn)步活動(dòng)(那時(shí)劉緒貽也在美國(guó));解放前她在國(guó)民黨統(tǒng)治區(qū)的白色恐怖下積極從事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地下工作(那時(shí)劉緒貽也在國(guó)統(tǒng)區(qū))。北京師范大學(xué)張宏毅教授在1996年評(píng)論和介紹黃紹湘的專文中特別肯定: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時(shí)期,“一邊倒”之風(fēng)刮得正烈,黃紹湘在1951年公開發(fā)表文章《評(píng)〈美帝破壞條約的歷史上的罪證〉》,反對(duì)隨意摭取歷史史例,作為揭露美國(guó)的“歷史罪證”。黃紹湘在這篇文章中指出:“歷史上的一切制度、現(xiàn)象、政治人物、個(gè)別問(wèn)題都由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臍v史條件所規(guī)定,我們著手分析時(shí),必須依據(jù)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木唧w歷史條件,去評(píng)定它們(或他們),不然,就會(huì)陷入簡(jiǎn)化主義或公式主義的錯(cuò)誤,就是非歷史觀點(diǎn)的方法。”她在文章的末尾總結(jié)性地指出:“我們研究歷史,尤其研究其他國(guó)家的歷史,要站穩(wěn)科學(xué)的歷史的立場(chǎng),絕不可以牽強(qiáng)附會(huì),曲解歷史,因?yàn)槿魏瓮鈬?guó)史的研究,在國(guó)內(nèi)還是嶄新的園地,我們對(duì)于任何專題的研究,如果不用冷靜的頭腦,馬克思主義的‘實(shí)事求是’的態(tài)度來(lái)處理,就會(huì)發(fā)生嚴(yán)重的偏差,引起學(xué)術(shù)界的混亂現(xiàn)象的。”
黃紹湘從青年時(shí)代就信仰馬克思主義,并以此作為研究美國(guó)史的指南,在不同歷史時(shí)期,她始終不跟風(fēng),她也從不畏懼屬于少數(shù)派而去與當(dāng)時(shí)所謂的多數(shù)派直面抗?fàn)帯|S紹湘早已將個(gè)人的生死置之度外,她還有何懼?她又何需去“告狀”?當(dāng)馬克思主義過(guò)時(shí)論甚囂塵上之時(shí),她接連發(fā)表數(shù)篇堅(jiān)持馬克思主義的文章,招致某些人的忌恨,個(gè)別人甚至在背后辱罵她為“馬克思主義的僵尸”,她聽到后只是付諸一笑,不予理睬。這樣錚錚鐵骨的共產(chǎn)黨員,豈能是某些人(即使也有共產(chǎn)黨員的稱號(hào))所可以嚇倒的?因?yàn)閷儆谏贁?shù)而去“告狀”之類的話,栽在黃紹湘的身上,真是令人匪夷所思。
作為一位歷史學(xué)家,劉緒貽理應(yīng)尊重客觀史料。那就讓我們回顧一下有關(guān)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秘書處遷出武漢大學(xué)的史料吧:
1990年3月9日,劉緒貽在給北京師范大學(xué)黃安年教授的信中談到:“從心理上說(shuō),我對(duì)研究會(huì)有感情,秘書處留在武大我或許感到安慰。但是,我只是研究會(huì)五個(gè)顧問(wèn)之一,我只愿意就如何加強(qiáng)研究會(huì)的工作提出建議,我不能、也不會(huì)干預(yù)你們理事會(huì)的任何決策。下屆理事會(huì)為了加強(qiáng)研究會(huì)的工作,決定把秘書處放在哪個(gè)學(xué)校,我都沒(méi)有意見。超過(guò)以上范圍的話,就不是我說(shuō)的。”
時(shí)隔十七年之久,在2007年初,劉緒貽在他的《經(jīng)歷》一文中,卻對(duì)此公開發(fā)表了與他在1990年3月9日所說(shuō)的完全不同的說(shuō)法,即那些針對(duì)黃紹湘的不實(shí)之詞。
那么,劉緒貽的“超過(guò)以上范圍的話,就不是我說(shuō)的”話,又是從何而來(lái)的呢?請(qǐng)讀者參考我們查到的以下旁證線索:2015年3月19日,黃安年教授發(fā)表文章寫道:“由于眾所周知的非學(xué)術(shù)因素,1989年后秘書處被迫由武漢大學(xué)遷往南開大學(xué)。……對(duì)于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秘書處由武漢大學(xué)遷往南開大學(xué)的細(xì)節(jié),相信在劉先生自述(下卷)中會(huì)有他自己的回憶。就我所知,由于有關(guān)人士對(duì)于研究會(huì)學(xué)術(shù)自主和學(xué)術(shù)問(wèn)題不同見解的非學(xué)術(shù)性的粗暴干預(yù),迫使秘書處改址,使學(xué)術(shù)問(wèn)題政治化,這既非廣大會(huì)員的愿望,也實(shí)際上造成了對(duì)劉先生和武漢大學(xué)美國(guó)史研究室集體的感情傷害。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的主管單位即中國(guó)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曾暗示我:他們深感沉重壓力,如果研究會(huì)秘書處不遷往南開,那么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能否存在都會(huì)成為問(wèn)題。我感到在當(dāng)時(shí)特殊的政治氣氛下,非學(xué)術(shù)因素的思考一時(shí)讓我們難以清醒、自主和抗命。”按照黃安年的文章,“有關(guān)人士”不僅“迫使秘書處改址”,并且威脅到“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能否存在”。不知黃安年所指的“有關(guān)人士”為何許人也?對(duì)黃安年做暗示的“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的主管單位即中國(guó)社科院世界史所的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又是誰(shuí)呢?黃安年對(duì)這些問(wèn)題應(yīng)該有所回答。
經(jīng)由劉緒貽等人之口,那些針對(duì)黃紹湘的不實(shí)之詞以訛傳訛,損害了黃紹湘的名譽(yù),已是不爭(zhēng)之事實(shí)。我們出面要求劉緒貽和黃安年這兩位資深歷史學(xué)家,對(duì)其進(jìn)行史料的求證工作,這應(yīng)當(dāng)是合情合理的吧?在他們還沒(méi)有對(duì)此作出反應(yīng)之前,請(qǐng)?jiān)试S我們提供一些“秘書處遷址”的相關(guān)事實(shí)吧:
我們?cè)诰W(wǎng)上查到了《中國(guó)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大事記(1978—2009)》,系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秘書處文,發(fā)表于《美國(guó)史研究通訊》2009年第一期;學(xué)術(shù)交流網(wǎng)/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2009年12月27日發(fā)布。該大事記中寫道:“1986年,8月2至9日,我會(huì)在蘭州召開第五屆年會(huì),此次會(huì)議選舉產(chǎn)生第四屆理事會(huì),由十九名理事組成。理事長(zhǎng)為張友倫,副理事長(zhǎng)為顧學(xué)稼、齊文穎、李世洞,李世洞兼任秘書長(zhǎng),并聘請(qǐng)宦鄉(xiāng)等五人為顧問(wèn)。”“1990年,……根據(jù)新理事會(huì)的決定,研究會(huì)秘書處由武漢大學(xué)遷至南開大學(xué)。”“秘書處地址:武漢大學(xué)1979—1990,南開大學(xué)1990—2002,廈門大學(xué)2002—至今。”
從以上史料記載,我們認(rèn)為:南開大學(xué)知名美國(guó)史專家張友倫教授,1986—1996年任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第四、五、六屆理事長(zhǎng),南開大學(xué)在世界歷史研究分工中側(cè)重北美、美國(guó)史,這才是美國(guó)史研究會(huì)秘書處從武漢大學(xué)遷到南開大學(xué)的真正原因;況且秘書處遷移,是由第五屆新理事會(huì)決定,這與劉緒貽等人的所謂“世界歷史所頂不住壓力”的說(shuō)法,出入太大,實(shí)在令人驚詫。
我們還特別以電子信件的方式,就此事向一位當(dāng)時(shí)的副理事長(zhǎng)求證,他的回答跟我們分析的一樣,根本否定有什么“壓力”:“……關(guān)于劉緒貽所說(shuō)美國(guó)歷史研究會(huì)由武漢大學(xué)遷往天津一事,我認(rèn)為劉的看法是不對(duì)的,想系他的猜測(cè)。因?yàn)槭澜缡匪懿涣四敲磳挘膊粫?huì)去管。因?yàn)檠芯繒?huì)之類的組織并非官方的,而是民間的。武漢離開北京較遠(yuǎn),人手也不多,而天津南開的美國(guó)研究人員要多些,辦事的人手當(dāng)然也多一些。所以就由南開的人來(lái)辦事,實(shí)際上所辦的事,就是發(fā)發(fā)通知,聯(lián)系一下各地的同行而已。其他什么都沒(méi)有,也沒(méi)有人想爭(zhēng)這么個(gè)差使。辦事機(jī)構(gòu)設(shè)在某地,絕不意味著該地就是中心。劉可能是多疑了。他以前常說(shuō),什么什么人不讓他發(fā)展馬列。他說(shuō)這個(gè)話,就說(shuō)明他的疑心病有點(diǎn)多……”由此可見,向當(dāng)時(shí)決定“秘書處遷址”的理事會(huì)成員求證,并不是一件難事。
在此還需要特別指出的一點(diǎn)是:劉緒貽在他的《經(jīng)歷》一文中,用了約百分之二十一的篇幅,談到他研究美國(guó)史遇到的主要阻力,這就是“‘左’傾教條主義的勢(shì)力仍然雄厚”,其中,劉緒貽以三百六十五字針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的黃紹湘,一千六百零四字針對(duì)他當(dāng)時(shí)的上級(jí)。讓人深思的是,某些人在網(wǎng)站上卻偏偏瞄準(zhǔn)了劉緒貽用字最少的“阻力”黃紹湘,大加宣揚(yáng)一些不實(shí)之詞,這是因?yàn)辄S紹湘的數(shù)篇關(guān)于“羅斯福新政”的文章,史實(shí)詳盡、論點(diǎn)清楚,是某些人無(wú)法公開、正面駁倒的。他們只能匿名于網(wǎng)上反復(fù)轉(zhuǎn)載劉緒貽的不實(shí)之詞,把一場(chǎng)公開的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發(fā)展為混淆是非的人身攻擊。歷時(shí)八年之久,如此興師動(dòng)眾,誰(shuí)能相信這是一個(gè)偶發(fā)事件呢?
人沒(méi)有什么事不能做出來(lái),只是天不容許人作偽。
(此文中所有引用的資料,均有確切出處。因篇幅所限,無(wú)法在此刊出。有興趣的讀者,請(qǐng)發(fā)電郵給huangshaoxiangworkshop@gmail.com,索取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