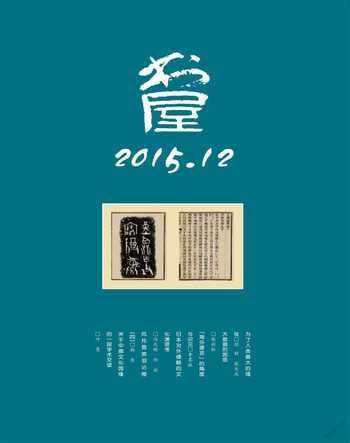從沈從文到孫機
湯銳
1934年,三十二歲的沈從文完成小說《邊城》,名滿天下。但1949年后,他卻轉向文物研究(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工作),寫下了《從文賞玉》、《唐宋銅鏡》、《龍鳳藝術》、《戰國漆器》、《中國古代服飾研究》等書。他的后半生心血都花在了“花花朵朵壇壇罐罐”上,而其小說衣缽反倒在弟子汪曾祺手中發揚光大。
八十年后的2014年,八十五歲的孫機出版了新書《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孫機是沈從文的弟子,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員。
正是受沈從文的影響,孫機才考取北大歷史學系,以整理文物為一生志向。“遙想半個世紀前的那個正午,從絞纈、輿服一直說到歷代文物,沈從文和他的小世界里風物殊勝,無疑對孫機產生了強烈且恒久的吸引”(李樂樂《物質文化,不止是放了個炮仗》)。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一書是中華書局出版的,布面精裝,典雅大方。此書沒有前言,直接進入主題。書末有作者一篇簡短的“后記”,交代了寫作緣起:“和一位年輕同學閑聊,談起這方面。他說,我看古代沒有什么不得了的,四大發明不就是放了個炮仗造了張紙嗎?聽到這話不禁心底一震。中國古代的物質文化成就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基本國情;本應成為常識,本宜家喻戶曉。對這位青年而言,無論用大專著或小冊子替他補補課,似乎都是必要的。因此使我有勇氣將這幾篇不成熟的文字發表出來,聊供讀史者格物之一助。”
中國人修史記事,歷來偏重于大人物、大事件,又受重農輕商思想之影響,忽略生產技術、物質文化。《史記》有《食貨志》和《貨殖列傳》,算是一大創舉。然后來的子部書中,《茶經》、《夢溪筆談》、《天工開物》、《農書》等有關科學技術、格物致知的專著仍是少數,他書多圍繞《詩經》、《楚辭》中描述的植物、動物進行研究,有點狹隘、局促。
雖說“早晨起來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但記述研究“柴米油鹽”的人反倒稀缺,或不屑,或不想,或覺無足輕重,文人們似乎更愿意“琴棋書畫詩酒花”。清代樸學興盛,稍有改觀,然范圍過于狹隘,且多迂腐之見。而現代第一部《中國科學技術史》還是英國人李約瑟編寫的,在劍橋出版;中小學歷史教材對此篇幅不多,到現在我只記住了四大發明和黃道婆織布。
《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上述缺憾。且與沈從文專著一本一主題不同,此書“已經初具通史的規模,橫向分出農業、紡織、建筑、器具等十個章節,縱向展示五千年來文明變遷,內里五臟俱備、脈絡完整,可以拿來作考古與文物學的入門書”。孫機的寫作初衷達到了;不僅達到,還是上乘之作,無愧其師。“本來文物專家談古事,內容不脫古雅、古趣,這些都是當行本色。而與‘古’字相異,‘物質文化’卻是一個新晉詞匯,它不同于‘文物’的具體、微觀,更強調一器一物背后的文化場景與時代意義。……更能‘使考訂之物事密切系連于歷史的主線’,從而勾畫出一幅骨架勻稱、血肉豐滿的歷史畫卷”。
如第一章“農業與膳食”,作者大處著筆:“世界上有三個農業起源的中心地,一個是兩河流域,一個是中美洲,還有一個就是咱們中國。中國是粟和稻,也就是小米和大米的故鄉。”接著再寫農具、五谷(九谷)、蔬菜、果木、主食菜肴、烹調方法,娓娓道來,不蔓不枝,如撒沙作畫,舉手間輪廓即具,接著便有山高月小、春風楊柳之細景。
寫古代文化之書,要么失之艱澀難讀,要么失之淺薄空疏,《中國古代物質文化》卻文質相兼,深入淺出,它既是一本優秀的普及讀物,又是一部極具分量的學術論著。一方面孫機是專家,另一方面這本書的基本內容是他在國家博物館講座的講稿,故既廣征博引,言必有據,又行云流水,通俗易懂,引人入勝,讀來輕松而有收獲。本書沒有附引用書目,不過所引之書當數百上千,經史百家,順手拈來,可見作者知識之淵博、視野之開闊。
晚清以降,學者重視收集研究金石甲骨、簡牘封泥,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更以實物資料與文獻記載相互取證,被稱為“二重證據法”。孫機最善用此法,而后出轉精,視野也更開闊。
例如本書寫杏:“杏也是我國古老的果蔬。《管子》說:‘五沃之土,其本宜杏。’《山海經》說:‘靈山之下,其木多杏。’湖北光化五座墳西漢墓曾出土杏核,這時杏已是常見的果類。從世界范圍看,盡管出產野杏的地域很廣,但我國最先栽培這種果蔬卻已經得到公認。”
翻看本書,你還會知道,不少日常菜蔬都是從外國傳入,如辣椒,明末才傳入,西紅柿十九世紀中葉才作為蔬菜栽培。若生在明初期,即便為湖南人,也不可能嗜辣如命。而白薯傳入中國的故事更具傳奇性。如此這般,都使人興味盎然。
可貴的是,孫機偶爾也“跳”出來一下,站在現代人的角度審視“古代物質”。例如第二章“酒、茶、糖、煙”最后一段說:“吸煙不利于健康,已成為人們的共識。但一下子禁絕似乎很難做到。退而求其次,那就先控煙吧。然而現實情況是,控亦不易。中國控煙辦公室主任楊功煥說:‘從做控煙以后,我覺得確實是非常難。’‘實際上就是有利益集團,會使它很難做。’此外,‘煙民’的心態也是一堵墻。曾定居紐約的美術家陳丹青說,‘我總被問到為什么回國,說句老實話,很簡單:回國能抽煙’。所以,控歸控,抽歸抽;這兩條平行線不知何時才能交叉起來,有前者把后者管住。”
正如李樂樂說的:“比較而言,孫機收拾起考古、文物,鐘靈毓秀也許不及乃師,可貴卻在更專注與平穩,從一粒紐扣拆解到九個香爐,都有他自家的一副神氣,得其所歸。尤其是針對學術上的謬見或誤傳,孫機更能保持一種撥亂反正的‘耿介’,甘心去做文物界的清道夫,或曰掃地僧,拂盡落葉見清秋。”
孫機厚積薄發,此書一出,洛陽紙貴,半年時間便加印兩次至一點七萬冊,還是供不應求。一本偏學術的書能有如此大的市場反響,可見其質量之高。去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中央電視臺科教頻道聯合舉辦的“2014中國好書”推選活動落下帷幕,三十種書目入選,《中國古代物質文化》便居其一。推選理由是:“孫機先生以其淵博的知識底蘊、曉暢的文筆,系統總結并闡釋了中國古代輝煌的物質文化成就,復原了五千年生活文明場景的變遷脈絡。本書不僅有很高的學術價值,而且對大眾讀者也有可貴的傳統文化普及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孫機有位女弟子揚之水(原名趙麗雅),曾任《讀書》雜志編輯,被稱為“京城三大才女”之一,進入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后也轉向研究文物考古,主要方向是先秦文學與古代名物研究,著有《脂麻通鑒》、《詩經名物新證》、《詩經別裁》、《古詩文名物新證》等書。她用的也是“二重證據法”——用考古學的成果來研究文學作品。
薪火相傳,文化不滅。從沈從文到孫機,再到揚之水,花花朵朵越開越盛,壇壇罐罐越積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