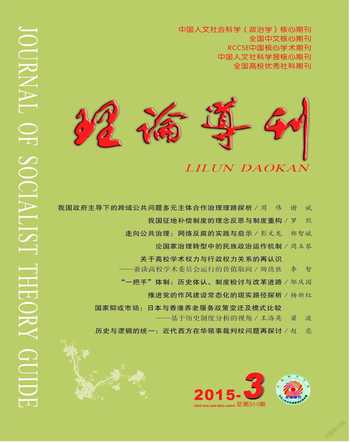歷史與邏輯的統一: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再探討
趙亮
摘要:有關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各種議題,近年來學界研究進展是不平衡的。在此情況下,如若單純依靠新近研究成果去簡單拼接歷史,可能造成結論與事實的偏差。網絡時代下的信息傳播突破了紙質媒介的限制,很難避免學術爭論的社會性擴散甚至被異化曲解。這提示我們應當緊密跟蹤學界研究進展情況,及時發現和厘清錯誤認識形成發展的內在邏輯,有針對性地更新辨正思路和論據,以期動態地確保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關鍵詞:領事裁判權;司法主權;學術研究;歷史與邏輯;社會化傳播;結論與事實
中圖分類號:D926204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002-7408(2015)03-0103-05
基金項目:中共北京市委教育工作委員會2014年首都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一線專項課題“大學生中國近現代史觀培育路徑研究”(BJSZ2014ZC249);共青團中央“青年馬克思主義者培養工程”專項課題2013年重點課題“網絡環境下90后大學生骨干的行為特點分析及培養路徑研究”(2013TZYQM001);共青團北京市委2013年北京共青團及青少年工作研究課題“網絡環境下90后大學生骨干的行為特點分析及培養路徑研究”(2013YB10);首都師范大學2013年青年教師教學研究項目“大學生中國近現代史觀培育路徑研究”(02613560910/024)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簡介:趙亮(1983-),男,河南鶴壁人,首都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教育學院講師,法學博士,華東師范大學政治學博士后流動站在站人員,研究方向:中國近現代史和中共黨史。
引言
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的確立和發展,不僅是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破壞,且“關于國內一切政治上、經濟上皆具有重大之危害”,是近代中外“不平等條約之尤深切明顯者”。而對近代歷屆中國政府而言,姑且不論其主觀上是否意識到此問題的嚴重性,實際上一直在為限制直至收回西方在華此項特權而努力。推動國內(開明官僚和知識精英)對領事裁判權問題的關注和研究自19世紀后期就已起步且經久不衰。新中國成立以后,這一問題又成為意識形態建設的重要素材,研究熱度依然不減。或許正是因為此項研究的起步和進展始終與某種政治需求相伴,因而至晚在1980年代后期有學者開始質疑長期以來相關研究的“客觀性”問題。應當說,領事裁判權在華存廢歷經百年,幾乎橫亙整個近代中國歷史,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至深至廣,采取更多的視角和方法去研究它,不僅可行而且必要。也正因為如此,越來越多的學者致力于對相關問題進行更加具體、微觀的考察。然而,微觀研究畢竟只涉及某個階段的某個方面,甚至是次要方面。用大量微觀研究成果拼接歷史,難免會推導出錯誤的結論。近段時間來,一篇名為《“治外法權”①百年真相》的文章在互聯網和微博、微信平臺上被大量轉載。該文認為領判權確立的原因是“洋人對中國式野蠻司法的拒絕”與“清廷推卸包袱般扔掉對洋人的司法管轄權”,而領判權適用范圍的進一步擴大“讓華人嘗到了免于拷打與律師辯護的好處”,至于領判權的撤廢則是由于中國“二戰中和英美是盟友”,“這個夢多少讓人覺得欣慰——至少這回算是摸對了方向”。依此邏輯,國家民眾為撤廢領判權的百年抗爭倒成了歷史的“反動”。這篇文章引發網民熱烈討論,甚至不少人直呼“毀三觀”。這是值得注意的,因為它不僅關系到我們該如何認識那段歷史,更關系到如何認識現時法治建設的道路走向。而上述文章之所以引起社會受眾關注,不僅因其觀點“驚世駭俗”,更因其以貌似“實證”的方法來得出觀點,顯得“有憑有據”。這值得學界反思。在網絡時代,信息傳播突破了紙質媒介的限制,一些新觀點尚未接受更加全面論證就被放置網上,而社會受眾借助新媒體手段的“口口相傳”又為這種觀點迅速累積信度。如果這種觀點恰好是錯誤的,那無疑會導致受眾的思想混亂。還有很多新被挖掘的史料,實際上只是歷史的個案,或是僅能反映歷史的某個截面,但若將其突兀絕緣地置于社會受眾面前,也可能被推導出背離歷史邏輯的結論。凡此種種都提示,在網絡時代下研究歷史問題,要不斷地基于具體研究進展來重新梳理歷史發展脈絡,動態地確保歷史與邏輯的統一。我們欣喜地看到,也確實有學者在做這樣的工作。不過針對近代西方在華領判權問題,這樣的工作還比較少,有些駁議思路和論據的選取也不夠恰當合理,不僅不利于說明問題,甚至可能進一步導致認識的混亂。有鑒于此,筆者認為有必要基于相關研究的進展情況,進一步厘清相關錯誤認識形成發展的內在邏輯,再對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進行有針對性的探討。
一、“全襲西法”:考察領事裁判權在華存廢史的危險邏輯
針對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近年來學界研究成果可謂蔚為大觀,尤其引起關注的是其在中國的確立、與清末司法改革的關系以及撤廢等幾方面內容。
關于領事裁判權在中國的確立,西方自身給出的理由主要指向中國司法生態惡劣甚或中西宗教信仰不同,具體如《中國叢報》、胡夏米和顧盛等對其時中國司法狀況的評論,都是國內學界競相引用并加以批駁的“經典案例”,在此不再贅述。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實證研究的興起,帶動不少學者從微觀視角開拓批駁論據,對近代前后中國涉外案件處理情況進行細致考察,試圖以此駁斥所謂西方要求取得領事裁判權是因為中國司法粗鄙不公的論調。邱濤進而提出,之前學界重點論證中方處理涉外案件的合理性、合法性,卻沒注意批駁外方行為的錯誤。而通過對德蘭諾瓦案件的細致考察,一方面證明中方在合法、公正地處理案件——這無疑是對美方所謂中方處理案件不公的駁斥,另一方面也證明恰恰是美方自身在“妨礙司法公正”。這種研究思路看似合理實則牽強。因為無論當時還是現在,也無論中方還是外方,都不會僅憑幾件涉外案件的處理情況就形成對一國司法體系的總體性認識。邱文中說在處理德蘭諾瓦案件過程中,一度“委曲求全的是中國官員”而非美方。這固然利于說明中方并不偏袒本方,但能夠說明中國司法的公正嗎?會不會反過來更給其時美方攻擊中國司法的不規范留下口實呢?實際上學界早已公認,西方對其時中國司法生態的某些指摘不無合理成分。如若不存在這些問題,那近代司法改革的意義又何在呢?還須注意,一國自身存在司法不公問題,不代表它會放棄對別國司法不公的指責。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說,不管是考證中國處理涉外案件的公正性,還是批評西方當事者乃至西方國內的妨礙司法公正問題,都不足以證明西方以中國司法不公為由要求領事裁判權只是借口。這種研究思路不僅缺乏說服力,反而可能推促受眾更加走向反面——即更加堅信西方的理由。
關于領事裁判權在中國的確立,近年來學界亦強調對其時中國政府“主動”讓渡此項特權的反思。如賀其圖考察了19世紀早期中國處理數起英人涉嫌在華命案的情況,認為這開了“英人在中國犯法中國無權單獨裁決”的先例,“為西方國家破壞中國的司法打開了方便之門”。郭衛東則考察了鴉片戰爭后期中英進行善后交涉的情況,提出在此過程中中方“令人難以置信”地“自動出讓了這項重大主權”,“將在華英人的審判權從中國完整的司法主權中割裂出去,拱手讓給英國”,證明“中國若干權益的喪失,不完全是外國侵略者的強制掠取,很大程度上是清朝統治者的主動奉送”。毋庸置疑,上述反思成果對進一步還原領事裁判權在華確立的具體過程至關重要,但是否就可輕易得出西方領判權的取得是中國政府“主動奉送”的結果,這無疑需要更加全面的考證。而缺乏了對西方要求此項特權真實意圖的考察,將上述研究成果突兀地置于受眾面前,就可能推演出這樣的論斷:鑒于中國司法狀況,為避免本國僑民遭受不公對待,西方要求取得在華領判權。事實上中國政府則在近代以前就已開始部分出讓這項主權,近代初期領判權的確立只是這種出讓進一步發展的結果。
有關清末司法改革,學界研究推進至現時,早已公認其推動中國司法進步的積極意義,認為它“改變了中國沿襲兩千多年的行政與司法合二為一的傳統”,“揭開了中國近代司法的序幕”。大家爭論的核心問題是領判權在其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很多學者提出收回領事裁判權是晚清政府決心修律的(一項)原因。值得注意的是長期以來不少學者的論證依據都是1902年9月5日中英《續議通商行船條約》(即《馬凱條約》)第12條中提及“一俟查悉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103換言之即西方此種允諾促使晚清政府啟動司法改革。曾憲義、李貴連和吳永明等都是持此觀點。但事實上,晚清政府于1902年3月11日即已發布第一道“修律”上諭,103若考察其對司法改革的醞釀,則時間還可進一步向前追溯。正是基于這些考證,張鳳磊、葉反修等學者明確否認清廷修律源于西方允諾,高漢成更進而提出領事裁判權“始終只是晚清主持改革者推進法律變革的手段”,司法改革“服從和服務于新政這一整體政治局勢”,其啟動“本身并沒有自己額外的起因和目的”。
但實際上,迄今尚鮮為學者提及的是,至少早在同治七年,英、美等國即先后向清政府表示,鑒于“各國在中華通商,洋人有犯法之事,仍按各國律例遵斷,于中外均有不便”,“期望將來中國律例悉改為寬大平和,則外民亦可受中國官管束”。由此可見,僅依靠理順《馬凱條約》與清廷宣布修律的先后順序即妄下結論說司法改革與西方允諾沒有關系,無疑給自己設下一個邏輯陷阱:既然有史料顯示于此之前西方就有允諾,那若無法證明再早之前中方已有修律想法,那就說明中方修律仍是源于西方允諾。再者,一些學者提出收回領判權是司法改革啟動的原因,并未把《馬凱條約》作為依據,也不認為與西方允諾有根本關系,而是立足清廷視角,考察其對領判權認識的變化過程,因而得出上述結論。綜上所述,中方修律究竟源于西方允諾與否,固然有待商榷,但采取《馬凱條約》案例已無法說明問題。而邱濤等學者進而采取這種辦法借以說明領判權在華作用的有限性、客觀性,那就不僅不能說服讀者,反而會加劇相關思想認識的混亂情況了。
有關領事裁判權的撤廢,也是近年來學界比較關注的問題,特別是民國時期,不管政府還是民眾均表達出收復此項主權的強烈意愿,抗爭“趨于高潮”,可供研究的檔案和文獻非常豐富,而這段歷史區間的領判權問題恰恰是新中國成立后長期以來學界研究的薄弱環節,因而近年來尤其引起學界關注。但伴隨相關研究成果的大量涌現,有兩個問題愈發值得注意。
一是領判權得以撤廢的原因。一方面,在大量研究表明民國時期歷屆政府接續為收復司法主權而努力的同時,很多研究則顯示從德國到俄國(蘇聯)再到英美日等國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廢除卻都似國際政治形勢變化的結果。另一方面,很多研究又證明如同晚清時期一樣,在民國時期,西方“漸進放棄”領事裁判權的允諾依然存在。1921年華盛頓會議上中國代表團提出撤廢領事裁判權議案“得到了各國的同情,被列入大會議題”,且根據大會決議,會議結束3個月后,“列強就要組織代表團來華考察中國法律和司法”,只是中國政府鑒于國內其時司法狀況“不能令人滿意”加之國內政治形勢,一再要求推遲考察團來華時間。且考察團最終基于中國司法生態依然惡劣而反對撤廢領判權——姑且不論這種理由是否正當而單看其指摘的一些司法狀況本身,確有不少屬實的成分,更勿論周鯁生所說其時中國的司法改革舉措“多半是紙上的官樣文章,與事實都隔得尚遠的”。有鑒于這些情況,一味地說考察團1926年才來華是因為“列強的敷衍、拖延”、考察團對領判權“此種非法特權的嚴重危害絲毫未揭露,卻對中國的法律和司法進行嚴厲的批評”,不僅無法信服讀者,反而會加劇這樣一種看法的形成:西方具備撤廢領事裁判權的誠意,中國政府雖然為收復司法主權不懈努力,但不能有效改善司法狀況,這使西方不能作出還權決定,只是由于國際政治形勢的變化才陸續還權。在此邏輯情境下,如果再聯系到學界關于日、中撤廢領判權成、敗的反思——日本是在憲政改革并完全順應西方要求進行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成功收回領判權的,那就不僅易使人進一步認為徹底照搬西方司法體系的重要性,還會使人產生這樣的認識:日本情況表明,要使中國司法狀況得到根本改善,僅依靠架構司法體系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依照西方模式架構政治制度。
二是西方在華領判權撤廢后中國是否保全司法主權。綜觀相關研究成果,針對此問題進行細致論證者很少。誠然,如果只將領事裁判權作為一種具體的司法形態來研究,那其被撤廢后的歷史似無研究的必要——因為不管此項特權享有者是否以其他形式繼續享有此項特權,都已是另外的問題。但是,若從中國司法主權完整性的角度來考察領事裁判權問題,那就必須要著重考察此項特權的實際效應,從此意義上說,領判權的廢除是否就意味著中國徹底收回了司法主權,就很有討論的必要了。而現時很多研究到1943年美英等國廢除在華領判權即戛然而止,很容易給人一種錯覺,即至少中國的司法主權在新中國成立以前就已完整了,更有學者明確這樣來評價,這明顯違背了歷史事實。
綜上所述,近年來學界有關近代西方在華領事裁判權問題的研究,總體而言存在進展不平衡的問題:一些在之前因種種原因研究進展緩慢的問題引發熱議,同時另一些與其存在密切邏輯聯系的問題則少人問津,極易引發社會受眾對原有重大歷史定論的質疑。此外,少數研究成果本身亦存有需要商榷之處,再加上一些學者在學術爭論中駁議思路或論據選取不當,反而可能加劇社會受眾的思想混亂情況。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客觀上就有可能形成這樣一條邏輯線索:領事裁判權的存在使中國司法主權遭到破壞固然是歷史事實,但其并非西方侵略的產物。恰恰相反,西方一直借由領判權促推中國的司法進步。然而,領判權的撤廢并非中國的司法體系與國際接軌,而是國際政治形勢變幻的機緣巧合。要真正實現中國司法體系的現代化,不僅需要堅決移植西方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徹底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唯有此才能為中國的司法現代化提供根本保障。此種邏輯當然是錯誤的,更是危險的,因為它不僅背離了歷史事實,而且會讓人對中國未來道路的走向產生錯誤認識。要扭轉此種邏輯,就必須基于而又不局限于學界的研究進展,上升至宏觀層面,在近代中國司法主權完整性的視角下考察領判權的歷史,揭示歷史發展的真實內在邏輯。
二、“只有自強發奮而已”:13回顧中國收復司法主權歷史的必然結論
不管基于哪種視角研究近代西方在華領判權問題,都不能否認它的存在表明中國司法主權的不完整。從中國司法主權完整性的視角下考察領判權問題,首先要搞清楚領判權確立以前中國司法主權是否已不完整。梁啟超、費正清均認為在近代以前,“治異族人,還以其族固有之法律”,已是中國“法學上之一原則”,“并沒有與舊習慣發生抵觸”。254然而縱觀中國古代法律涉外原則的演變史,在明朝時已確立絕對的屬地主義原則,且即便明代以前存有兼采屬人主義原則的情況,也是統治者“對司法主權的獨立行使”,無論如何都看不出其“和近代領事裁判權之間有任何聯系”或所謂“中國傳統的繼續”。誠然,近代前夕中國政府在處理部分涉外案件時有外方參與司法過程,但這只是隨機決策的結果,“化外人有犯、依律擬斷”的涉外司法原則并沒有改變。至于進入近代以后領判權的確立是否中國政府的“主動奉送”,單看江南善后交涉過程似是如此,可若聯系其交涉背景就絕不能這樣下定論了。毫無疑問,沒有鴉片戰爭就不會有此交涉。再具體一些說,鴉片戰爭爆發之際英國政府已明確向中國提出確立領事裁判權的要求,也應看到清政府進行江南善后交涉“是在防止戰端再起”。交涉中清政府基于各種考慮竟不惜犧牲司法主權,這無疑值得后人反思,但若由此得出近代司法主權的喪失是中國自己造成的,那就太荒謬了。作為鴉片戰爭背景下產生的一項外國在華特權,它歸根結底還是西方“靠武力建立起來”的,250毫無疑問是西方對華侵略的產物——也正是從此意義上說,這與近代土耳其的領判權問題完全不同性質。
至于西方所宣稱的要求此項特權的理由,與其針鋒相對地論爭中國涉外司法是否公正,并沒有抓住問題的要害——因為即便中國司法不公正,也絕不意味著中國必須放棄涉外司法主權(長期以來一些學者于此問題上的糾結,不得不說是被套入了其時西方列強所設定的邏輯圈套之中)。對此,實際上德蘭諾瓦案中一群美商已經說得很明白:“我們認為在這個案件的處理中存有偏見”,但“我們一旦置身于你們的海面上,我們不得不服從你們的法律,盡管它是這樣的不公平”。因此要駁斥西方理由,關鍵在于直接指明其真實意圖。其實只要宏觀地考察一下近代中外關系史就不難發現,鴉片商人和傳教士構成了其時在華外國人的主體。如當時美國在華商業機構中,“除了一個名叫奧立芬的公司外”,“其余的都在經營這種罪惡貿易(鴉片貿易,引者)”。而大多數在華傳教士只是以從事傳教活動為掩護,主要任務是收集各方面情報,為西方逐步染指遠東出謀劃策,“在東方他們有一句口頭語:開始是教士,隨后是領事,再后是將軍……只要看一看中國這件事就夠了”。正是他們積極建議本國政府要求在華確立領判權,并為之積極營造輿論。由此可見,西方要求領判權歸根結底還是為擴大在華侵略服務。
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說,西方在華領判權確立的手段和目的均非正當,而中國司法主權完整正由此遭到破壞。而在領判權確立以后,從單純法權意義上說,不僅西方法律由對在華僑民的懲罰權逐步發展至全面管轄權,且適用原則由“屬人主義”發展至一定程度的“屬地(各國在華租界和公共租界)主義”,對特定地域內的無約國僑民乃至華人也得以實施一定管轄,證明中國司法主權完整性遭到進一步的破壞。僅從此意義上就必須明確領判權在華存在的不正當,更勿論其在華司法人員素養的參差不齊、一些司法機構的異化、案件審判中的本國利益至上與物質利益至上以及司法程序本身的很多弊病。從更宏觀的角度看,如果說中外不平等條約中其他內容都是對西方特權的有限性規定,那么領判權的確立則使這些特權具有無限延展的可能——毫無疑問,有什么特權是“無法無天”不能涵蓋的呢?難怪有學者說,近代中外“所有不平等條約特權中,領事裁判權處于中心地位”。或許正是出于這種擔心,其時中國政府一直極力反對外人在中國內地居留。但隨著小農經濟的日益解體,各項資源逐漸向中心城市集中,成為經濟鏈條的終端,西方列強通過租界控制城市經濟,漸次實現對中國內地和鄉村經濟的掌控。正是在此背景下,領判權對中國經濟社會的破壞性亦愈廣愈深。如近代西北地區煙毒泛濫,從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領判權的存在使毒品貿易鏈無法斬斷。而近代財政金融專家童蒙正則指出,中國“實業不振,溯其原因”,亦“半由于此(指領事裁判權,引者)”。
由上述可見,近代西方領判權在華的確立及發展,造成并逐步加深對中國司法主權的破壞,進而也造成并逐步加深對中國經濟社會進步的破壞,這是不爭的歷史事實。至于所謂領判權促進了中國的司法進步,這完全不是歷史的邏輯。誠然,外人在中國土地上設置法庭、施行其本國法律,使國人見識到了外國的司法運作程序,也促使越來越多的人反思中國既有司法體系的問題,但這都是國人對外來事物信息進行選擇性加工的結果。對此,歷史的邏輯應當是發現國人近代意識的覺醒,而不是領判權對華有益,否則就是陷入了“強權即公理”的庸俗進化論。
至于近代司法改革是否基于撤廢領判權的考慮,綜合學界研究情況來看,至少目前無法排除這種可能性。而且正如上文所說,即便完全是基于這種考慮,也不能得出領判權對華有益的結論。更為重要的是進行如下辨析:首先,假設西方允諾為真,那么中國法律到底該如何與西方法律“同一”呢?孟德斯鳩說:“為某一國人民而制定的法律,應該是非常適合于該國人民的。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法律竟能適合于另一個國家的話,那只是非常湊巧的事。”各國法律彼此不同,“我同于甲,必不能同于乙”,實現中西法律“同一”“必不能行”。其次,不管西方允諾真假,是否中國移植某種西方法律體系就能增加撤廢領判權談判的砝碼?事實很清楚,即便國民黨政府時期已建立起“六法體系”,仍然無濟于事。有資料顯示,直到1942年上半年,因擔心“戰后美國國民(包括法人及團體)在中國的權益得不到保證,屆時會缺少‘討價還價的籌碼’”,美國政府仍不愿就撤廢領判權問題與中方談判。第三,西式法律體系的構建是否將中國帶向法治社會?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早在民國時期就已為徐道臨、樓邦彥等學者所指出。而學界研究進展至今天,大家也早已認識到,司法進步與社會進步無法割裂開來,必須以政治進步為前提。所以核心問題在于,政治進步該如何實現?
一種頗有市場的觀點是:近代日本堅持實行政治、社會和司法制度的全盤西化,由此不僅收回了領判權實現完全獨立,更建立了強大國家和法治社會。鄰國歷史證明,中國也應遵循此條道路。然而筆者以為,這種觀點忽略了對一個重要問題的探討,那就是在近代西方列強看來,中日兩國的價值是否可以同日而語。毫無疑問,中國的國土面積、人口規模和資源總量遠非日本可比,對其時西方列強來說,侵略中國的收益要遠遠大于日本。歷史事實很清楚,西方放松控制日本的過程,恰恰是其騰出更多精力加緊控制中國的過程。盡管義和團運動使西方放棄了瓜分中國的圖謀,但相比日本,中國的崛起無疑是其更加擔心的。正是從上述意義上說,西方不僅不會放松對華控制,更不會給中國崛起以機會,說日本的迅速崛起是其全盤西化的必然結果,這不是歷史的邏輯。同樣是基于歷史的邏輯,我們應當看到,伴隨國際政治形勢的急劇變化,雖然領事裁判權在華終得撤廢,但是中國司法主權并未實現完整。由于日本侵華,美英在華特權基本名存實亡。如何于戰后在華攫取更多利益,是其時西方特別是美國對華決策的核心思想,放棄在華領判權只不過是基于此根本目的的變通之法。眾所周知,二戰后的中美關系絕非平等,《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簽訂不過是美國鑒于世界情勢變換了侵犯中國利益的形式而已。國與國關系都不對等,中國又何以確保司法主權完整?1946年美軍士兵強暴北京大學女學生沈祟的事件清楚表明,即便沒有了領判權,西方仍能憑借強權肆意踐踏中國司法。
究竟該如何收復中國的司法主權,實際上近代以來對此有深刻體會者不在少數。張之洞嘗言:其實“專視國家兵力之強弱、戰守之成效以為從違”。康有為則謂:“只有自強發奮而已”。13還有人說:“只有一個激烈的法子,就是革命。”他們的主張各有差異,但從中皆可引申出一相同觀點:“全襲西法”必不可行。歷史的事實是,司法主權的收復和民族獨立的實現,歸根結底依靠的是自主探索。亦同樣是依靠自主探索,中國才切實走在民族復興之路上。也是從此意義上說,依法治國也是中國堅持自主探索得出的結論,絕非為法治而法治。未來在依法治國道路上的探索,借鑒外國先進做法和經驗固然重要,但若因迷茫于實際進程中的困難和挫折,而寄希望于照搬西方的法律乃至政治制度來實現中國法治目標,那就如同近代國人寄希望于全襲西法來收回領判權一樣,“萬萬無此理,亦萬萬無此事”。
三、余論
古人云:鑒于往事,資于治道。近代中國歷史不僅是追求民族獨立的革命歷史,也是不斷積累治國理政經驗的歷史。對近代中西關系,我們除卻考察侵略與反侵略問題,也應更加注重反思中國內政外交能力與西方的差距。這方面研究的深入,不僅利于發掘歷史進程的更多層面,也會為國家的未來發展提供更多有益借鑒。比如對于領判權問題,我們從“對外法律談判視角”專門考察一下中外圍繞其撤廢的長期交涉中都采用了哪些具體的談判技術,以此為切入點總結近代中國政府在國際舞臺上爭取各項法律權益的經驗教訓,這對我們今天處理涉外歷史遺留問題無疑具有重要意義。而考察一下近代中國司法改革的歷史進程,也無疑會對我們今天推進法治建設有所啟示。問題在于,基于不同學科背景乃至不同目的去考察一系列有明確側重性的研究成果,所得出的結論也往往千差萬別。今天的一切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必定是經由或相關于昨天而來。我們研究過去的問題可以基于很多價值取向,不是非要得出歷史結論,但要得出歷史結論就必須依據歷史的邏輯。歷史虛無主義思潮之所以值得我們警惕,不僅在于它歪曲了歷史,更在于它會誘發出很多有關現實乃至未來問題的錯誤認識。此種思潮的出現和發展,不僅是西方意識形態輸出的問題,而且我們國內的媒體、受眾和學界也都有很多要反思的地方。特別對于學界來說,一方面學者不僅要考慮研究的目的和口徑,也要更加注意其成果可能側生的社會影響;另一方面歷史教育工作者更有責任和義務不斷地跟進和梳理學界研究進展,不斷地研究相關學術信息社會化傳播的路徑和特點,增強教育研究工作的問題意識和針對性。
注釋:
①“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并非同一概念。治外法權(Exterritoriality)指“一定的人和房舍雖然處于一國領土之內,但在法律上被認為是處于該國之外,因而不受當地法律的管轄,該原則適用于外國君主、國家元首、外交使節和其他享有外交特權的人”,“在較窄范圍內也適用于在另一國領土上的訪問軍隊以及在外國水域內的軍艦和公有船舶”,可見是一種對等的外交待遇。而“領事裁判權”(Consular Jurisdiction)則指“一國通過領事等對處于另一國領土內的本國人民根據其本國法律行使司法管轄權的制度”,這突破了對外交人員的限定,是對所在國司法主權的破壞。近代歷史上中國政府一度混淆了二者概念,是由于西方列強為“攫取在華領事裁判權”而“有意混淆兩者之間的區別”,以“借治外法權之名,欲獲‘領事裁判權’之實”。至于中國政府何時開始明晰二者區別,還有待學界進一步考證。
參考文獻:
[1]何勤華,李秀清.民國法學論文精粹(第6卷)[M].法律出版社,2004∶276.
[2]陶廣峰.關于列強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幾個問題[J].比較法研究,1988,(3).
[3]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撤廢領事裁判權運動[M].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29∶39-48.
[4]GWKeeton. The Development of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M].London·New York·Toronto,1928∶107-108.
[5]列島.鴉片戰爭史論文專輯[M].三聯書店,1958∶39.
[6]梁敬錞.在華領事裁判權論[M].商務印書館,1930∶3.
[7]邱濤.領事裁判權的歷史淵源和歷史作用——關于《“治外法權”起緣》一文相關論點的駁議[J].北京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
[8]賀其圖.鴉片戰爭前的中西司法沖突與領事裁判權的確立[J].內蒙古民族師院學報(哲社版),1994,(2).
[9]郭衛東.鴉片戰爭后期中英善后交涉[J].社會科學研究,1996,(4).
[10]趙玉環.論沈家本對清末司法改革的貢獻[J].東岳論叢,2009,(7).
[11]朱壽朋.光緒朝東華錄(第5冊)[M].中華書局,1958.
[12]《法律史論叢》編委會.法律史論叢(第三輯)[M].法律出版社,1983∶198.
[13]李貴連.清季法律改革與領事裁判權——兼論沈家本法律救國思想[J].中外法學,1990,(4).
[14]吳永明.清末司法現代化變革原因探析[J].江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2).
[15]世續.德宗景皇帝實錄[M].中華書局,1989(影印本)∶536-537.
[16]張鳳磊.試論清末修律研究中的兩個問題[J].山東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5).
[17]葉反修.晚清修律動因的若干思考[J].河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3).
[18]高漢成.晚清法律改革動因再談——以張之洞與領事裁判權問題的關系為視角[J].清史研究,2004,(4).
[19]英國公使節略[M]//籌辦夷務始末 同治朝(卷63).同治七年十二月,第48頁.
[20]張仁善.論民國時期收復司法主權的法理抗爭[J].法學,2012,(2).
[21]張仁善.半個世紀的“立法秀”——近世中國司法主權的收復與法律創制[J].政法論壇,2009,(2).
[22]李啟成.治外法權與中國司法近代化之關系——調查法權委員會個案研究[J].現代法學,2006,(4).
[23]周鯁生.領事裁判權問題[J].東方雜志,1922,(8).
[24]陳一平.近代中國領事裁判權的形成與收回[J].麗水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0,(1).
[25]華友根.帝國主義在華領事裁判權的形成、廢除及其斗爭[J].史林,1991,(2).
[26]李育民.晚清改進、收回領事裁判權的謀劃及努力[J].近代史研究,2009,(1).
[27]盧俊松.簡論領事裁判權制度的產生演變與消亡[J].前沿,2011,(18).
[28]馬克思·韋伯.學術與政治[M]. 馮克利,譯.三聯書店,1998.
[29]梁啟超.論中國成文法編制之沿革得失[M]//飲冰室合集文集(第16冊).
[30]費正清.劍橋中國晚清史(上)[M].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254.
[31]肖梅花.中國古代法律涉外原則初探[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4).
[32]張志讓.在華領事裁判權及其撤廢問題[J].世界知識,1935,(6卷).
[33][美]丹涅特.美國人在東亞[M].商務印書館,1959∶75.
[34]孫曉樓,趙頤年.領事裁判權問題[M].商務印書館,1937∶158.
[35][美]F.R·杜勒斯.1784年以來的中美關系史話[M].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1946∶21.
[36][英]楊國倫.英國對華政策[M].王慶成,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245.
[37]李育民.近代中國的領事裁判權制度[J].湖南師范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5,(4).
[38]馬長林.晚晴涉外法權的一個怪物——上海公共租借會審公廨剖析[J].檔案與歷史,1988,(4).
[39][美]魏斐德.上海警察(1927-1937)[M].章紅,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62.
[40]吳圳義.清末上海租界社會[M].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18.
[41]施丟克爾.十九世紀的德國與中國[M].喬松,譯.三聯書店,1963∶21-22.
[42]吳圳義.上海租界問題[M].臺北:正中書局,1981∶177.
[43]褚宸舸.中華民國時期西北地區的煙毒及禁政[J].福建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學報——社會公共安全研究,2000,(5).
[44][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M].張雁深,譯.商務印書館,1982∶6.
[45]張元濟.外交報匯編(第1冊)[G].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09∶167.
[46]王淇.一九四三年“中美平等新約”簽訂的歷史背景及其意義評析[J].中共黨史研究,1989,(4).
[47]徐道鄰.假如政府肯全面革新[N].申報,1949-02-06(1-2).
[48]樓邦彥.如何能粉飾得了太平——由召開行憲國大想到種種[J].觀察,1948,(5).
[49]張國華,李貴連.沈家本年譜初編[M].北京大學出版社,1989∶199.
[50]張晉藩.二十世紀中國法治回眸[M].法律出版社,1998∶207.
[51]勞乃宣.桐鄉勞先生(乃宣)遺稿[M].文海出版社,1969(影印本)∶899.
[52]張仁善.論民族主義與近代中國司法主權意識的覺悟[J].河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3,(1).
【責任編輯:宇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