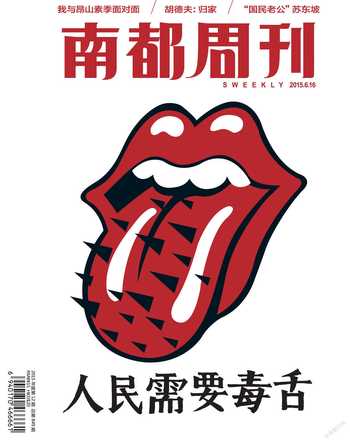小說是我的,電影是姜文的

南都周刊:為什么在海外寫北京?你寫的北京與老舍、王朔有關系嗎?如何評價中國大陸寫作者對北京的描寫?
張北海:這本小說設法表達兩個主題——無論這是否符合歷史事實——即俠之終結和老北京的消逝。因此,雖然我人在紐約,還是選擇了我的出生地、抗戰前后的老北京,作為小說的地理背景。與此同時,也可將當年北京的一些訊息,傳達給當今年青一代,也就是說,八十多年前,北京曾經有過這么一段日子。
《俠隱》和老舍或王朔的關系不大,但《駱駝祥子》敘述的老北京,是我的參考之一。
至于如何評價大陸寫作者對北京的描寫,前輩或當代作家任何抒情式的感性文章,無可厚非,其他,我沒有資格發言。
南都周刊: 姜文看中的是北京還是武俠?為何一個海外作家寫北京的小說引起了老北京人姜文的共鳴?
張北海:我想姜文應該看中了小說的某一方面,否則他不會去拍。小說是我的作品,電影是以導演為主的創作。我覺得應該,也必須讓姜文放手去拍。
至于為什么一個海外作家寫老北京的小說,會引起老北京姜文的共鳴,我也只能猜測,大概姜文有他某種感性或浪漫的情懷,也正偷偷地向往那個遠去的時代。
南都周刊: 寫的時候有沒有想過復原北京的氛圍、味道、生活方式?
張北海:我盡量設法做到這一點。《俠隱》是一部寫實作品,既然我把歷史背景設在抗戰前后的北平,又把一個俠士放在一個二十世紀真實社會,那1930年代北平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風俗習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市容街道,等等,就不但在所必需,而且成為書中一個重要角色,但北京,或你我,都無法回到從前,允許我借用王德威教授評論《俠隱》那最后一句話:“瞬息京華,求諸他日,惟有夢寐,惟有文章。”
南都周刊:《俠隱》里老北京生活方式是兼收并蓄的。連大小姐都跟美國女孩兒差不多,現在都很難做到吧。
張北海:任何敘述都不容易,都難達到作者期望的境界,但既然你已經指出我“筆下的老北京生活方式是兼收并蓄的”,那這部小說的敘述至少有了如此一個反應,關于“大小姐都跟美國女孩兒差不多”,想想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西風已經滲入至少諸如十里洋場、天津、北京等等大都市,西裝革履已非異服,連旗袍都開始有了腰身,再想到書中大小姐藍蘭,就讀的又是北京美國學校,那就更加必然了。
南都周刊:如何評價現在的北京?理想中的北京是怎樣的?
張北海:我離開北京六十余年,雖然不時往返,但遠在1974年第一次回北京的時候,就已經感到陌生了,而且不僅僅是牌樓城墻的消失,連我幼年喜愛的小吃,都難再嘗到。至于現在的北京,大約兩年才回去一次的我,更沒有資格評論。我多半是看老朋友,辦點事,和吃(倒是真有好的),連街都少逛。
南都周刊:你愿意將《俠隱》與哪些武俠小說放在一起?
張北海:《俠隱》如果能和張恨水的《啼笑因緣》放一起,盡管我會臉紅,但也會高興,他不但是我的前輩,而且是最早一位作家把武俠人物(該書關氏父女),寫進了二十世紀通俗小說的。
南都周刊:武林高手比較少見的職務是編輯。《俠隱》這樣安排有什么特別用意嗎?
張北海:是有用意。武林高手,不提別的,也要吃喝拉撒睡,更不提一文錢逼死英雄漢,同時,這是刻意安排的身份掩護。
南都周刊:《俠隱》其實非常類似于“純文學”,比如說大多數時候興趣并不在故事情節而在人物與環境。而武俠小說屬于通俗小說,為何將兩者結合起來,有難度嗎?
張北海:我寫的是一部通俗小說,而非“純文學”,單憑它是武俠小說,就已經和嚴肅文學搭不上邊了。我只是一個說故事的,站在中國傳統小說那些前輩巨人的肩膀上,設法為武俠人物在現代或當代存身,探求一個可能。
南都周刊:在聯合國工作的愉快嗎?感覺是很正規的工作,在工作中有卡夫卡那種對現代辦公室制度感到反感嗎?
張北海:在聯合國工作相當愉快,同時,因為工作需要,經常遠去他國為國際機構會議服務,更給了我一個難得的機會去看世界,擴大視野。至于有沒有卡夫卡那種對現代辦公室制度的反感,對我來說,有時肯定會有,但我的個性和人生觀或許減輕了一些反感,也就不會因此而苦惱。
南都周刊:陳升在歌中稱你為嬉皮,如果是真的話,這種氣質與聯合國的工作合拍嗎?
張北海:陳升那首歌應該是朋友之間善意的戲稱,我當然不能算是真正的嬉皮,只不過因為走過了那個時代,免不了多多少少感染上了一點點味道而已。
至于這種氣質與聯合國工作是否合拍,我只能說,在國際機構工作二十五年,它容忍了我,我也容忍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