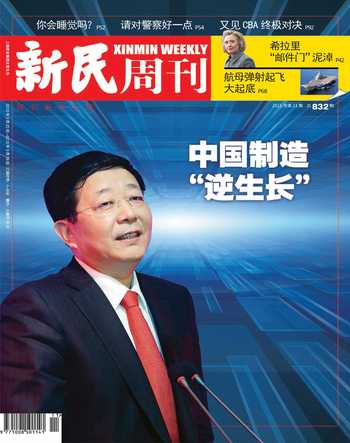“學而優則仕”的“新常態”化
和靜鈞

2015年新一輪高層次人事調動中,多名大學校長步入仕途,“學而優則仕”重回輿論中心而備受關注。
這其中有北大校長王恩哥,履新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組成員。清華大學校長陳吉寧,2015年2月27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上表決任命為環境保護部部長。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長懷進鵬,2015年2月起擔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校長侯建國,被任命為科技部副部長。北京工業大學校長郭廣生,2015年1月出任北京市委副秘書長,屬正局級干部。曲星,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原院長,2014年底被任命為駐比利時王國特命全權大使。
“專業對口”
這一批從“學界”躍升入“仕途”的知識精英們,給人們的第一印象是,他們都步入了對口專業領域的領導崗位。
如王恩哥身為著名物理學家,履職中科院領導工作,應如魚得水。生態科學家陳吉寧赴任環保部部長,順理成章,強化了環保部的專業決策能力。著名計算機軟件專家、中科院院士懷進鵬,擔任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正好可以發揮其專長。著名化學家、中科院院士侯建國被任命為科技部副部長,也沒有偏離其專業特長。一直從事國際關系研究的曲星,改任駐外大使,更是一個再合適不過的任人唯賢之佳例。
新一輪人事任命所體現出來的“專業性”是無與倫比的。在過去,也不乏高層次的“學而優則仕”之諸例,但“專業對口”并非是優先議程,有的甚至升任為與其之前知識背景完全不同的領導崗位。
“專業對口”化,歸功于中共中央辦公廳2014年11月印發的《2014-2018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綱要》首次明確提出要從高校及科研院所等單位里,培養和選拔黨政領導班子成員,其中指導思想就是“優化領導班子知識專業經歷結構”原則。
“優化領導班子知識專業經歷結構”這一原則,使學界中頂尖專業人才吸納入專業對口的高級領導崗位成為可能,而“優化經歷背景”,也使具有高校或科研院所行政領導經驗與經歷的高級專業人才走上“仕途”成為可能。
筆者注意到,2015年新一輪人事任命中走入仕途的學者們,無一不是已經擁有了充分的行政領導工作經驗,這一經歷,使其能快速對接新領導崗位。
“學-仕”的演變
“學而優則仕”一語來源于古代賢哲孔子的學生子夏一句名言中的后半句話,完整的話應是“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意思是“學好了,還有余力,就不妨當官、行公職”。
現在,再沒有人關心“學而優則仕”的原義,這一詞語已經定格在“學習優秀者當官”的教條主義原則里。
在孔子時代,并無“科舉”這樣入仕渠道,“上品無寒門,下品無高第”是常態,普通學人能否入仕,全憑“學好后又無余力”,若有余力,可向貴族及門閥自薦。
而隋唐以來沿襲下來的“科舉”,社會體系生成了這樣一個給普通人“入仕”的便捷及公平渠道,它不再依仗于人身依附與人際關系,只要在學問考核中擊敗競爭對手,就有可能高第,“學優者入仕”,天經地義。
農耕文明的一大特點,就是判斷一個人是否對社會真有價值,是問其是否步入仕途為官,以官階等級為標準。至今中國社會仍然有這樣的傳統觀念,它有其社會適宜性,并不全是負面的。一個對公職崗位漠然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工業化文明程度最高的西方國家,每隔一兩年掀起的轟轟烈烈的選戰,觸及全社會各階層,本質就是“入仕戰”。
現代社會向熱心于公職工作的有志人士提供了入職渠道,“公考”就是現代社會幾乎所有國家都普遍采用的選拔方式。公務員考試中,學優者及分高者勝出是鐵定的游戲規則,這保證了競爭的公平公正。
然而,“公考”勝出者,領到的只是“準入證”,而非是“委任狀”,絕大部分競爭者除了知識、年齡上有優勢之外,公職服務所需的專業經驗、社會經驗、政治經驗都相當缺乏,“公考”勝出者并不能使其快速勝任領導崗位。
而在古代,“公考”勝出者,都會委以七品芝麻官及以上的官位,一日及第,立即光宗耀祖。
現代社會分工細化下,公務員也被分類為事務公務員、技術公務員、政務公務員。進入事務公務員及技術專業公務員序列的,甚至都不會讓進入者有“入仕”的感覺。在行政官僚體系下從最低層一步步升遷到處級以上的官,一般都要經過十年。往往社會經驗累積到一定程度后,其專業知識能力卻隨著時間原因變得生疏,專業水平也下降。
這使傳統的“學而優則仕”這一通道,在“公考”體制下并不能充分地體現出來,社會上出現了“學優者不能入仕”的通道堵塞之壓抑感。
在“公考”體系之外,開辟新的入仕綠色通道,顯得異常重要。
在西方,政務高級公務員多半是隨著政府組閣而產生,又隨著政府內閣屆滿或倒臺而離去,不是終身制。組閣中常啟用學界中名聲顯赫的人物,也是常態。
如曾在小布什時期擔任總統安全顧問及國務卿的賴斯,從政之前是知名蘇聯問題專家、斯坦福大學教務長。奧巴馬的首席經濟顧問是前哈佛大學校長薩默斯,奧巴馬的能源部長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朱棣文。頂尖專業人士的加盟,大大提升了領導團隊的決策科學性及專業性。
在當下日新月異的科技變革與知識經濟驅動的治理環境下,“學而優則仕”不僅不過時,反而更加重要。
“旋轉門”作用
現代社會治理體系中一個重要環節就是“智庫”體系,智庫推出思想產品,政府采購。
當前政府采購智庫思想產品的佳例不多,其中重要一點就是智庫思想產品尚不能達到令決策者信服的地步。
制約智庫產出質量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智庫研究人員基本上清一色為單一背景的學者,他們多是“書齋思維”,缺乏實用性。
筆者注意到,甚至一些國內算一流水平的智庫中,擔任主研任務的學者,大多沒有從政經歷,即使有,也只是擔任過低級職位或事務性職位。
西方智庫往往羅織了一大批曾經“學而優則仕”的高級官員,這些退休或離職下來的高級官員,仍然具備超級科研專業能力和專業水平。他們熟知學界、政界、商界,他們的從政經歷正好提供了“旋轉門”作用,使其在智庫中更能創造出影響決策者的研究成果。
中國未來新型智庫建設中,就需要借鑒西方“旋轉門”制度,其中多選拔專業人士擔任重要領導職位,就是一個必須的措施。
以往的經驗是,通過“掛職”的方式讓優秀學者參政。然而,實踐表明,一眼就看到結果的“掛職”并沒有令“掛職者”獲得深刻的職業體驗,為期一年半載的“掛職鍛煉”并沒有令“學而優則仕”落地生根。
為了有效發揮“旋轉門”效應,應鼓勵“學而優而仕”渠道獲得重要領導崗位的學者們,在服務公職五年之后進入智庫,這樣更能發揮其特長。然后,如有條件,可以隨時召回擔任相應的重要領導崗位。
防止過度“行政化”
3月9日,全國人大代表、安徽工業大學商學院教授楊亞達在參加代表團會議時,提出大學老師許多都想著當官,她曾見到一個副處長職位,有20個博士、副教授去爭,教育行政化色彩現在越來越濃了,教育去行政化迫在眉睫。
報道中指出,在教育領域,很多“正統”學者都把做官入仕作為最終的選擇與歸宿,而把學術當做階梯和手段,對行政職位趨之若鶩。
也有人指出,高校學者熱衷于當官,其中一個原因是級別待遇差異促使。調查顯示,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的教授其年工資收入比不擔任行政職務的教授高18%,擔任或兼任行政職務的副教授比不擔任行政職務的副教授高25%。
高校中的行政崗位也存在級別差異,比如院長、校長都是由國家或者省上任命,相對應的有部級、副部級、廳級、副廳級等級別差異,再往下同樣也是,比如處長、副處長等。
學者在高校及科研院所中謀得內部一個行政領導崗位,這應不算本文中所稱的“入仕”,因為它畢竟不是公職崗位,非公務員序列。然而,學校及科研院所都有一個對應的行政級別,這一行政級別與政府行政部門的行政級別是平行的,這使擔任學校里的行政職務,使學者也會產生“入仕”的幻覺。
合理和適度的行政化及行政級別化是現代高校治理的題中應有之義,高校不可能完全去行政化,不可能重返古希臘蘇格拉底式的廣場教育模式。相應的行政級別制,使具備一定行政經驗的高校學者能快速地平行過渡到相應的政府行政部門內任職。
可以想象,若清華大學沒有部級高校級別,清華大學校長很難直接表決任命為環保部部長。我國干部選拔規則里明確了逐級晉升及晉升間隔年限制,高校行政級別制,保證了現有條件下令高校優秀學者從政。
然而,過度行政化畢竟有悖于高校的倫理,一個高校可以以其畢業生的從政率為榮,如美國常青藤聯盟高校中一半以上的畢業生都成為了政商界精英,但很少有美國高校會以其盛產政治家教授為榮,教授忙于行政級別,肯定不是學術之福和學生之幸。
學者從政的新常態
隨著高學歷公務員隊伍的逐漸龐大,干部隊伍的運動式“知識化”已經沒有必要,大規模地從高校教師中抽調人員填補政府行政部門干部隊伍的必要性已經喪失,學者從政將進入“新常態”。
“新常態”下的學者從政的渠道變得越加清晰,只有學識及行政經驗都一流的學者才有可能獲得這樣重要的崗位,這使得高校領導崗位上的個別學者們才可能有機會走上這樣的崗位,減少了學者中盲目從政熱。
“新常態”也減少了學者從政中“暈輪效應”。以往知名學者憑借其卓著的社會聲望,快速步入重要領導崗位,但事后人們發現其并不適合這樣的崗位。強調專業性及經歷,使學者從政之前有了相當足夠時間磨礪,更容易評估其真實品質。
維持“新常態”的力量,應來源于社會的一定流動性。當前社會流動性差,“從一而終”的現象相當普遍,包括高校教師的流動性也相當低。海外的經驗表明,只有個別學者會獲得“終身教授”之職,很多學者還得不斷找新的高校謀職,這一流動性稀釋了學者盲目的從政熱,會令學者回到學術本位。當然,最大的學術本位回歸的力量,就是薪酬待遇的吸引力。(作者系察哈爾學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