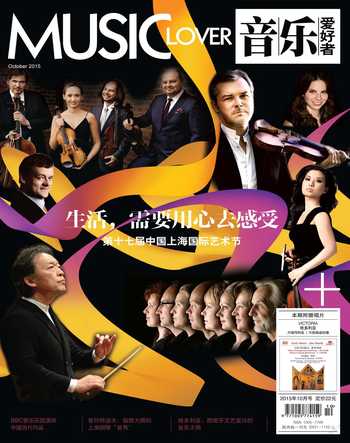王一兵:錄音師中最好的“作曲家”
胡越菲
信封里是一張簡易包裝的唱片和作品介紹,封面上寫著“交響敘事曲《天仙配》,小提琴、大提琴與樂隊,總政歌舞團管弦樂團演奏”。回家后,我打開了CD機,莊嚴的引子之后,優美的小提琴旋律如潮水般涌瀉出來,讓人瞬間就被融化了……
2015年7月,我接到了王一兵老師的電話,她邀請我去山西太原聆聽她的個人交響樂作品音樂會。我如約抵達太原,演出前一天,王老師盡管忙得焦頭爛額,但還是抽出空來,在賓館的房間里接受了我的采訪。
叫“王一兵”是因為“想當兵”
王一兵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山西人,父母都從事法律行業,家里只有她一個人是搞音樂的。那么她是怎么會走上音樂這條道路的呢?“我覺得喜歡音樂是天生的,”王一兵快人快語地說道,“我從小就喜歡跳舞、唱歌。我唱京戲唱得可好了,跳舞時我是領舞,十二歲以前我就長這么高了。”她伸出手比劃道。十一歲,她開始學習小提琴,“官方簡歷上寫著我十一歲作曲,實際上我七八歲時就寫曲子了”。好神奇,怎么會在學樂器之前就作曲了呢?“我身邊有個作曲老師,我六七歲時先跟她學了簡譜,后來學小提琴時才學的五線譜。”小時候,聽著火車行進的速度,王一兵自己就把節奏給弄出來了,這不能不說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天分。
王一兵從小就夢想當兵,這也是她名字中“兵”字的由來。“當年唱京戲時,部隊差點要我,可惜我年紀實在太小了,只有十二歲。”后來,她便把名字中的“炳”字改成了“兵”字,于是從原來的“王一炳”變成了現在的“王一兵”,以表達自己對成為一名軍人的向往。在她心里,自己就是為部隊而生的人,“雖然我沒有當過兵,但我永遠是一個‘兵’”。
十四歲時,王一兵進入了山西晉中文工團擔任小提琴手,同年發表了人生中的第一部作品——一首兒歌《計劃生育好》。“現在想起來有點兒好笑,十四歲就寫‘計劃生育’,不過那是當時的國策嘛。我大哥喜歡寫作,他寫了歌詞,我就給他譜了曲。”王一兵是幸運的,她的處女作剛寫完,她所在的晉中文工團就上演了這部作品,這是多少作曲家夢寐以求的事情啊。

在文工團工作期間,王一兵爭取到一個機會,去中央音樂學院學習三年作曲。“那是我一生中受益最大的時期。”十七八歲,正是如饑似渴地學知識的年齡,王一兵每天的生活就是從這個教室沖到那個教室,“我覺得自己不懂的東西太多了,上課時好多內容都理解不了,我只能先把筆記記下來,回來后再慢慢消化”。當時作曲系一個班十幾個人,王一兵還和譚盾大師有過一段同窗生涯。“他看我是山西來的旁聽生,覺得我挺不容易的,中午就把他的琴房讓出來,給我練琴、做和聲習題。”這件事至今都讓王一兵頗為感動。
回想起過去,王一兵滿是感慨,坦言自己吃了不少苦。“那時沒有進修班,只能自己花錢去旁聽,一門課要二十塊錢,我記得可清楚了,當時我一個月只掙四十多塊錢。”為了省下住宿的錢,她借住在北京的一個親戚家。“那時條件差,我住的地方就是在一個小院子里蓋的廚房,幾平米見方的地方還要做飯,我在鐵爐子旁邊搭了個木板床,平時屋子里有鳥兒飛來飛去,晚上還有臭蟲咬。”除了物質上的艱苦以外,還有精神上的壓力。由于經濟拮據,王一兵只報了三門課,“可實際上我聽了二十多門課,我自己弄了個課程表,把其他各個系我需要學的課都聽了個遍”。因為她教的錢少,蹭的課卻最多,結果被教務處盯上了,每次抓人都是抓她。“我想我這是學習,也沒什么可丟人的,所以前門一來抓,我就從后門逃跑了。”王一兵就在這樣“警察抓小偷”的環境下度過了三年的求學時光,接受過劉烈武、黃祖喜、李吉提、劉霖、耿生廉等音樂教育名家的指導。“我都跟上好老師了,很多教材都是作者本人親自來講,我作曲真正的基礎便是那個時候打下的。”
由于地方文工團離太原市有四五十公里路,王一兵在結婚成家后,覺得來回奔波太不方便了,于是想辦法調回了太原,去科學研究所擔任人事管理。再后來,她又跑去山西廣播電視臺做了一名錄音師。從專業小提琴手到人事管理,再到錄音師,同時,她還是山西省音樂家協會的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會員,這專業跨度也太大了吧。對此,王一兵調侃道:“所以人家叫我‘萬金油’呀。有時我們上午音協開會,記者說,你是音協搞作曲的呀。下午電視臺有活動,我是錄音師,在那兒拉音頻線,沒想到還是同一幫記者來采訪,他們很驚訝地說,怎么又是你啊,你到底是干啥的呀?我說,我也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學了啥,沒干啥。”有人說王一兵是“錄音界中最好的作曲家,作曲家中最好的錄音師”,她自嘲道“最后我就啥也不是,鬧成了個‘四不像’”。
這么說,王一兵顯然是謙虛了。如今,她既是山西廣播電視臺的首席錄音師,又是國家一級作曲家,這樣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王一兵始終堅信,搞錄音的一定要懂音樂。“有人說,搞作曲的么,你在這兒搞什么錄音啊?其實這是他們對這個專業不了解,你要是聽不懂音樂的話,怎么給人家錄音啊?歌手唱錯了你也不知道,樂隊拉錯了你也不知道,到最后合成的時候,你本人的欣賞和審美觀念都體現在你做出來的音頻里面,不懂音樂怎么行啊?”

“寫歌就像洗臉、吃飯一樣平常”
盡管從事的工作專業跨度如此之大,但王一兵從來沒有停止過自己音樂創作的步伐。至今,她已經創作了各種體裁、題材的歌曲三千多首,作品多次在省內外獲獎,比如《海那邊,海這邊》在1999年獲得山西省優秀歌曲比賽一等獎,《故鄉酒》獲山西省“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還出版了歌曲集《獻給祖國的歌》等。她的聲樂作品在形式上有獨唱、對唱、合唱,在唱法上有通俗、民族、美聲,在題材上更是內容豐富、涉及面廣泛,包括《普通士兵》《夫妻是條船》《家鄉的明月,邊關的雪》等反映普通百姓生活情感的作品等,非常值得一聽。
三千多首歌曲?這個數字也太龐大了吧,簡直讓人難以置信。王一兵笑道,這些歌曲大多是2011年到2014年間創作的,“那是我歌曲創作的高峰時期”。她平均一天寫兩首歌,下班回家后吃完晚飯就寫,比專業作曲家還勤奮。“我覺得這是我每天需要干的事兒,寫歌對我來說就像洗臉、吃飯一樣平常,不做我就難受。”她訂閱了一本《詞刊》,看到感興趣的歌詞,腦子里馬上就涌現出旋律了。“現在你給我拿個詞兒來,我可以當著你的面譜下曲子,我不改的,一筆寫成,”她開玩笑道,“如果中國有個作曲速度比賽的話,我敢和任何人比。”盡管創作了那么多歌曲,但王一兵并不是只求數量、不求質量的,“我也要突破自己,不能說昨天寫的東西,今天又重復了”。
除了歌曲以外,王一兵還寫了不少器樂作品,那個速度就慢了許多。“管弦樂作品不比聲樂作品,有好多東西需要仔細琢磨。”比如第二天要演出的交響敘事曲《天仙配》,她就從2003年一直寫到2007年,花費了很多心思,其間修改過三次,因為她“寫的時候老想著要超越自己以前的作品,所以寫寫停停,有靈感了就寫,沒靈感了就停一陣子”。《天仙配》是王一兵的第一部大型器樂作品,2010年由總政歌舞團管弦樂團在北京首演。“那次排練休息時,樂手們一下子就過來把我給圍住了。我心想怎么回事啊,因為我很明白,高水平的樂隊演奏過的好作品太多了,一個地方作曲家寫的作品,他們一般是看不上的。”可是他們很喜歡王一兵的《天仙配》,這讓本來對自己的器樂作品不太有把握的她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天仙配》是中國戲曲的經典劇目,故事講述了董永家貧,賣身傅員外為奴三年。玉帝的七個女兒戲于鵲橋,窺視人間,其中最小的七仙女鐘情于董永,與其結為夫妻。玉帝得知七仙女下凡之事,震怒,令其即刻回宮,否則禍及董永。七仙女無奈,忍痛泣別,留下了千古憾事。交響敘事曲《天仙配》的內容和音樂素材均取自同名黃梅戲,樂曲采用了自由回旋奏鳴曲式的結構,音樂沿著故事情節的線索而展開。代表七仙女的第一主題由小提琴奏出,柔和甜美,富于歌唱性,刻畫了七仙女真摯、純樸、嫻靜的性格。代表董永的第二主題由大提琴奏出,運用了戲曲音樂板腔體的結構,刻畫了董永辛酸、凄楚、孤獨、壓抑的心情。隨后,不祥的定音鼓引出昏聵、殘暴的“天宮”主題,在中國擊樂的伴奏下,音樂作了卡農式的模仿,達到高潮時就像一番群魔亂舞的場面,天國的仙女與人間的凡夫相愛的故事,最終在悲愴凄惻中結束。

王一兵以質樸、感人的音樂語言重新詮釋了這個中國家喻戶曉、優美動人的愛情故事。創作時,她并沒有按照故事發展的順序寫,而是先把七仙女的主題定下來,然后一部分一部分地寫,最后把它們全部銜接在一起。“就和寫歌一樣,拿到詞,我經常從中間的副歌部分開始寫,有時甚至會倒過來寫。”《天仙配》主要是代表七仙女的小提琴獨奏,這是王一兵的老本行了,“我太了解這件樂器了”,小提琴段落的高超技巧顯示出作曲家扎實的作曲功底。代表董永的大提琴與小提琴有一些對位的段落,到了中段的“天宮”主題時,音樂呈現出些許當代的風格,“要和之前的主題產生對比”。王一兵是真正地用自己的整個身心在寫音樂,樂隊排練時,在一旁的她都會被自己的音樂感動到流淚。“別人不理解,說你有啥感動的呀,但我知道自己這里在寫些什么。”只有感動自己的音樂,才能感動他人。
黃山行促成的“佳緣”
采訪中,我了解到,原來這次王一兵與山西交響樂團合作的交響樂作品音樂會,是在那次黃山行中促成的,而在此之前,她和山西交響樂團的團長朱建安,才剛認識不久。
2015年4月,王一兵受到主辦方安徽樂團的邀請,去黃山參加中國交響樂峰會。“我是唯一一位‘特邀作曲家’,還有一位‘特邀演奏家’是小提琴家朱丹。”峰會期間,王一兵向各參會代表贈送了自己作品的CD,這對朱建安團長很有觸動。“河南演藝集團的董事長周虹是搞作曲的,陜西愛樂樂團的團長崔炳元也是搞作曲的,他們很理解作曲家的辛苦——寫了東西沒人演奏,要演奏就得花錢。有一天,周虹老師來到了朱團長的房間,說,山西有個作曲家,你們山西交響樂團怎么不支持呢?她給我們一個一個送碟,我們覺得太不容易了,我也經歷過那個時候。后來朱團長就對我說,哎呀,讓人家罵得我,太不像話了,我一回去就給你報項目呀。”
回到山西,朱團長說做就做,立刻就向山西省文化廳報了“王一兵交響樂作品音樂會”的“惠民演出”項目,文化廳很快批下來了。接下來,王一兵就開始挑選作品、準備總譜、和指揮討論作品、組織排練等事宜,“時間特別緊,我們還插了個隊,不然就要等到12月以后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這次王一兵的個人作品音樂會,除了交響敘事曲《天仙配》以外,還有交響詩《一九四五》和管弦樂作品《山西民歌六首》。《一九四五》是王一兵為了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世界反法西斯勝利七十周年而作,從2013年底開始構思,不到兩年就完成了,這次演出是全國首演。說到這部作品,王一兵略帶自豪地表示:“也許你聽不出它和《天仙配》是同一個人寫的,我就喜歡自己的每部作品都有所不同,每一次都有新的東西給大家。不要局限在一個固定的風格里面,我更希望別人聽了以后會去猜測,這是誰寫的作品呀?”

在中國,寫戰爭題材的作曲家并不多,“因為這個題材不好表現”。《一九四五》在用管樂表現的槍炮聲和敵機的轟鳴聲中開始,樂隊奏出輕浮、放蕩并帶有蠻橫跋扈的敵軍進攻主題。“山西也是抗日戰爭的主戰場,我們平時在屏幕上看到的日本鬼子的形象太多了。”王一兵本來想用口哨,把日本鬼子那種洋洋得意的無賴形象表現出來,但可能因為旋律有點兒復雜,山西交響樂團的團員們吹不了,口笛也不行,最后只能用了短笛來代替。“但我最想用的還是口哨。”她略帶遺憾地說。敵軍主題之后,我軍剛健有力、堅定豪邁的主題出現,并不斷發展壯大,生動地展現了我軍英勇不屈、浴血奮戰的壯闊景象。接著,戰斗的主題與敵軍變形的主題并置交織在一起,音樂逐步推向高潮,描繪出一幅刀光劍影、殺聲震天的大戰場面。在一片混亂騷動中,敵軍節節敗退、消亡,尾聲出現了委婉、優美、舒緩情緒的主題,作為對這場戰爭的一種回憶。最后,全曲在莊嚴而輝煌的樂隊全奏中結束。
眾所周知,山西是民歌的海洋,自幼生長在這片熱土上的王一兵深深地愛著這里的一草一木。她曾于2010年11月和2011年4月與總政歌舞團合作,分別在北京音樂廳和家鄉太原成功舉辦了“晉韻——王一兵個人作品音樂會”,而管弦樂作品《山西民歌六首》就是她作為一個晉中平原養育的兒女,獻給故鄉的深情之作。王一兵選取了河曲民族《黃河水長流》、晉中秧歌《賣元宵》、左權民歌《建立民兵隊》、二人臺《送情郎》、晉北民歌《繡荷包》和交城民歌《交城山》等六首具有濃郁西北風情的民歌,運用交響化的音樂語言加以重新演釋。
關于《山西民歌六首》的選曲,王一兵有著自己獨到的想法。“很多民歌已經有作曲家寫過了,我不想再重復寫了,我選的這六首基本上都是沒有人寫過的。”王一兵是山西左權人,“左權民歌在山西、在全國都是比較有名的,比如大家喜愛的《桃花紅杏花白》就是出自左權民歌”,因此她特意選了一首左權民歌《建立民兵隊》。“大部分民歌都是口耳相傳的,而《建立民兵隊》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創作的,屬于新民歌類,比較特別。”選擇晉中秧歌《賣元宵》,是因為王一兵之前所在的晉中文工團對秧歌類民歌比較熟悉,“秧歌有兩種身份,它既可以算作民歌,也屬于戲曲中的小劇種類,而在晉中秧歌里,《賣元宵》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至于交城民歌《交城山》,“交城山是一個地名,這個地方的民歌特別少,大家知道的好像就這么一首”。這些樂曲或優美動聽,或幽默歡快,或悠遠深情,以富于多變的音樂語言展現了北方民族豪放而細膩的性格。王一兵說,她就是想把這具有濃濃地域特色的山西民間音樂精華帶給聽眾。

如今,王一兵依然在山西廣播電視臺首席錄音師的崗位上勤勤懇懇地工作著,同時也表示會繼續作曲,“我喜歡作曲,我不為任何人寫,我就是為我自己而寫”。有人曾這樣評論王西麟的音樂“他的音樂只有一個聽眾,那就是他自己”,王一兵當時聽了就哭了,她覺得這個太感同身受了。當然,現在王一兵音樂的聽眾可不止她一個人了,繼山西交響樂團之后,安徽樂團、珠江交響樂團和東方交響樂團都將陸續上演她的《天仙配》《一九四五》等作品,她也會將“錄音師中最好的作曲家”的身份演繹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