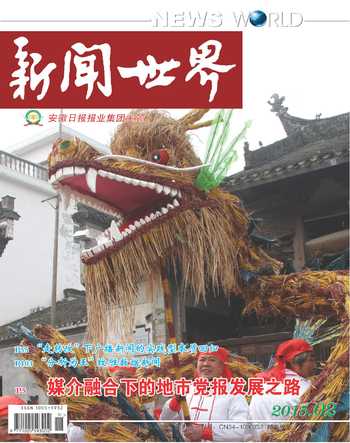從《黑幫暴徒》看黑幫片中的人性回歸
楊靜
【摘要】現如今,生活節奏越來越快,出現的社會問題也日益增多,社會犯罪漸漸開始挑釁社會準則的權威,這些反映在銀幕上,便成了黑幫片的敘事焦點,黑幫成員往往是對抗國家機器的群體,他們身上貼著違法與殺戮的標簽,影片中的槍戰或者打斗場面往往成為觀眾的關注點。隨著觀眾審美水平的提高,黑幫片在創作過程當中漸漸突破傳統的敘事模式,逐漸走上回歸正統倫理道德和回歸人性本真的道路上來。
【關鍵詞】黑幫片人性回歸暴力
警匪片在國外是最暢銷的電影類型,它包括幾種衍生的類型,如犯罪片、黑幫片、驚悚片、懸疑片、推理片等。黑幫片雖為警匪片的衍生產物,但與警匪片仍有不同,這兩種類型所要表達的內容也是完全不同的。警匪片的核心人物一般都以警察為主,他們代表的是社會的正面力量,解除社會隱患與危機,而黑幫片則截然相反,黑幫分子則成了實實在在的中心人物,對于這些社會黑道分子,黑幫片導演大多熱衷于表現黑幫內部的等級秩序、超越社會準則的兄弟義氣以及黑幫與代表社會權威準則的法律界的微妙關系,從而描繪出平日在都市中并不常見的“邊緣”景觀。因此,黑幫片相較于警匪片,更多一層情感,多一些情節,多一份情思,能夠打動人心且生動鮮活。
涉及黑幫分子的影片往往和槍戰、打斗、犯罪有著聯系,在這些場景當中,黑幫分子們往往都是冷酷無情的殺手,沒有人性的惡魔,搶人錢財的強盜,他們為社會準則所不容,所以自成一體,建立起自己的生活準則。兩個社會準則的強烈碰撞造成一次次火拼的發生,最終以社會大眾準則的勝出,黑幫分子的死亡為結束,彰顯出社會的正義。
黑幫片的源頭是1903年愛德溫·鮑特的《火車大劫案》,1912年電影大師大衛·格里菲斯描寫犯罪生活的《豬巷火槍手》,強盜開始作為主角出現在熒幕上,使黑幫片初具雛形,1927年德裔導演約瑟夫·馮·斯登堡拍攝的《下層社會》一片,確立了黑幫電影的基本元素。
現代的黑幫電影,多融合了社會環境因素和歷史文化因素,越來越快的社會生活節奏使人們的生活與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人們的物質生活漸漸豐富而精神生活漸漸空虛,黑幫電影的場面可以使觀眾在影院中盡情釋放生活中的壓力和不愉快的情感,影院往往成為人們尋求放松、追求刺激的場所。
隨著觀眾審美水平的不斷提高,黑幫電影在保留原有的火拼場面、冷酷情節的基礎上,開始有所創新,逐漸賦予了黑幫分子“人性”,讓他們不再只是冷酷無情的殺人工具,漸漸地讓他們的自我認識得到提升,引導他們走向自我救贖的道路,主人公往往在影片的最后所表現出的另類人格使故事情節的發展達到高潮。《黑幫暴徒》就是這樣一部電影。
一、黑幫片的特點
《黑幫暴徒》是一部關于靈魂沉淪與重生的電影,包含領域涉及了家庭教育、弱勢群體的保護、責任等多個方面。它以南非首都約翰內斯堡附近的一個城鎮為故事發生的大環境,講述了從小生活在當地水泥管道中的一名黑幫頭目從冷酷無情到靈魂重生的轉變的故事。大衛在一次搶劫行動中打傷了車的女主人,無意中將車中女車主的孩子帶到了自己家中。從一開始對孩子的束手無策,到最后找母乳喂奶,大衛逐漸找回了善良的自己,從而最終得到了救贖的故事。
電影拍攝在約翰內斯堡,城內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狀況嚴重,約翰內斯堡也是世界上犯罪率最高的恐怖之都。城中的索韋托,是南非黑人最集中的隔離區,為影片提供了殘酷的現實背景。
第一,都市環境。黑幫片從一開始就植根于大城市中貧民區的下層生活。擁擠都市、百姓的低劣生活、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都為黑幫片提供了豐富的現實背景。黑幫片的環境一般是治安較差,人員混雜的二三線城市,行動一般安排在晚上,伴隨著灰暗的天色,落灰的水泥墻或泥土地,狂風暴雨或電閃雷鳴的天氣以及疾馳的深色汽車或摩托車。
在影片開始,可以看到大衛帶著自己的兄弟走在街上,街上繚繞的煙霧給人一種十分朦朧的感覺,讓人明顯感覺到氣氛的壓抑,在背景中暗暗的紅色象征著一種隱性的血腥和殺戮,小鎮看似平靜卻即將被這樣一群反規則的人打破。在大衛劫車的過程當中,他開著汽車在雨中飛馳,這一切都符合傳統黑幫片的模式,然而轉折點就在車上的孩子,孩子的存在使得這部電影充滿了人性的關懷,也使大衛走上了
救贖自我的道路。整個影片的戲劇沖突,并不存在于黑幫分子之間,也不存在于他們和警察之間,而在于大衛陷入了自我矛盾的兩難境地,自身的野性與理智的人性關懷,讓他在做出一次次決定時艱難不定,在他試圖重新調整野性與人性之間的平衡時,自己是注定要失敗的,從另一個角度而言,他也是成功的。
第二,固有的暴力特征。通常黑幫片的故事發生在一些成長環境不好或自幼被邊緣化了的個體或是成長經歷有著共鳴的群體身上,涉及到個人的忠誠,或者與執法人員的博弈,以及與競爭對手亦敵亦友的糾葛。這是黑道人物獨特的生活背景與思維模式,即有事就用暴力解決,生命在暴力面前顯得很脆弱,這種暴力一般發生在無人的后巷、恐慌的人群、骯臟的酒館等。黑幫片中的暴力起著推動著情節發展的作用,與全片的主題息息相關。在電影中,黑幫分子們有著不斷的暴力行為,在地鐵上打劫、大衛打傷同伴、搶劫寶馬車,表面上直接體現出主角的冷酷和殘忍,實際上是在為之后的心靈回歸做鋪墊,這樣看來,觀眾就不會反感這些血腥的暴力行為。大衛打傷同伴是因為同伴的話刺激到了大衛內心最脆弱的部分,大衛渴望但失去了母親的關愛,這是他心底的創傷,這為后來他關心車上的嬰兒做了很好的鋪墊,也為他之后的自我救贖引出了開端。
第三,金錢。所有人的爭斗,最終的目的無非只有一個,那就是金錢。黑幫之間的斗爭僅僅是為了錢,金錢的地位在黑幫片中得到充分的彰顯,但金錢的地位又不僅僅代表物質,有時也蘊藏著情感。影片中錢出現了多次,開始的搶劫是為了生存,中途在寶馬中搶走錢包是為了逃避面對孩子的現實,大衛以為拿走錢就可以結束一切,然而,他轉身再次回到車中面對孩子時,開啟了他人生的轉折點,人性的回歸使他后來搶奶粉錢、拿錢給弟兄解散團體等行為充滿了責任感,這時的錢不再是交易的標簽,而是感情的代言。可以說,本片中的錢并沒有多少傳統黑幫片中錢所具有的功能,錢的含義不再是低俗、物質和骯臟,反而是一種希望,這是《黑幫暴徒》最大的亮點。
第四,地下世界。黑幫片場景多充滿了各色霓虹燈下黑暗的街道和夜總會、疾馳的轎車、骯臟的酒吧以及破舊的民房或居民區,在這樣的環境下,再加上異域風格的鋪陳,使黑幫片充滿了冒險和瘋狂的味道。片中一開始,黑幫分子便在酒吧里賭博,之后大衛幾次出現在混亂的街道、熙熙攘攘的酒吧當中,這無形中交代了大衛成長的社會環境,給黑幫分子的犯罪行為提供了客觀因素,仿佛也只有在這種狹小陰暗的空間當中,黑幫分子的規則才能存在,他們不被正統社會所容納,只能在黑暗的小環境中生存,隨著這些空間的消逝,黑幫分子建立的準則也會隨之消亡。
二、《黑幫暴徒》中的人物設置與人性回歸
主角的回歸。這類影片的結構模式有三種。模式一:青年主角一直從事非法行為,給受害者帶來災難。模式二:主角從事非法行為時遇到喚醒他本性的救贖者,人與人之間的深愛使他受震動。模式三:與同行朋友走上不同的路,青年主角做回善良的自己。《黑幫暴徒》主要屬于模式三,嬰兒的出現喚起了大衛關愛孩子的心,他并未向以前一樣殘忍地滅口,而是開始照顧孩子,孩子充當了救贖者,構成了大衛從幼年到現在的感情橋梁,使主角的內心從根本上得到了升華,融入了大的社會準則。
邊緣人物的關懷。影片中涉及到了很多的社會邊緣人物,流浪少年、單身母親、乞丐等社會上的弱勢群體,不同于以往的影片對弱者的同情,影片中彰顯了這些弱勢群體對生活的熱愛和向往。單身母親雖然一個人撫養孩子,但彩色的風鈴象征著她對生活的熱愛,對未來的希望,生活的艱辛苦難基本上沒有涉及到,當大衛問單身媽媽風鈴的意義時,我們能看到整個畫面是偏黃色的,暖色的光布滿了整個房間,它不僅代表著陽光,也代表著對未來的美好向往。同樣的,當乞丐回答有關生命的問題時,他說:“我喜歡陽光,喜歡曬太陽,就算只有這兩只手,也能感覺到生命的溫度。”整個畫面中,雖然整體光線是偏黑的,但是在乞丐的左側還是有明顯的黃色光照在他臉上,這種對生命的熱情被細膩地刻畫了出來。
在大衛重新回到水泥管道時,他說:“那是我長大的地方。”看到水泥管道上新的流浪的孩子,大衛會想到自己小時候的無助,可是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這些孩子依舊是不被重視的邊緣化群體,這些孩子還是得不到社會應有的關懷,同樣的社會隱患依然存在。
在黑幫片中,黑幫分子和他們毫無指望的城市環境殘酷地暴露了矛盾的價值、困惑的感受,他們在自我的感性與理性平衡的過程中,逐漸被主流文化所吸收,隨之而來的新一批黑幫分子又會重復走上他們的道路。□
參考文獻
①張琪,《群體成長背景下的青年回歸——電影〈黑幫暴徒〉和〈血鉆〉的結構主義比較》[J].《電影文學》,2008(7)
②曹雪,《淺談黑幫片的類型化發展》[J].《電影評介》,2008(9)
③李瑞,《血腥的震撼——淺析現代黑幫電影的暴力審美特點》[J].《電影評介》,2009(9)
④訚瑩,《淺析電影中的暴力元素》[J].《藝術科技》,2013(3)
⑤托馬斯·沙茨著,馮欣譯:《好萊塢類型電影》[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