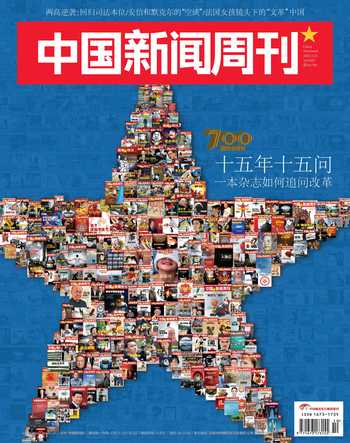教育的功與利
萬佳歡
2007年,本刊記者前往四川邛崍、溫州、北京、上海等地,探討“知識改變命運”這個曾經(jīng)響亮的口號是否還適用于當(dāng)下。經(jīng)濟狀況相對窮困的地方,人們會用更加實際的眼光去考量教育的投入產(chǎn)出比。8年之后,本刊決定重返邛崍,試圖觀察人們對待教育態(tài)度的細(xì)微變化。知識與教育是一個國家未來發(fā)展最重要基礎(chǔ)之一,而如今,教育似乎更加工具化和功利化,它并沒有成為人們上升通道的必然階梯,有時卻愈發(fā)從起跑線上就分化出成功者和失敗者。
知識改變命運是中國的共識。父母不計成本供養(yǎng)子女接受高等教育,但逐漸,教育對于命運的改變似乎不再那么明顯。原生家庭的經(jīng)濟狀況、社會地位決定了孩子們從起跑線開始就迥異的命運,而教育化解階層固化的作用似乎有所衰減
23歲的吳平最近每天都在想:我要怎么換工作?
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從西南民族大學(xué)畢業(yè)還不到一年,好不容易才擠進(jìn)成都一家小公司,月薪2200元,每個月省吃儉用,基本月光。
他想起以前自己曾發(fā)誓給父母寄錢,“現(xiàn)實真是張牙舞爪。”他搖搖頭說。
對于自己現(xiàn)在“混成這樣”的原因,吳平有些迷茫。一開始,他這樣總結(jié):“以前成績不好,沒考上更好的大學(xué)”;但后來想了又想,提起今年春節(jié)期間爆紅的“博士返鄉(xiāng)筆記”:“其實就算成績好又怎樣?博士又怎樣?留在市里的同學(xué),修車賺得都比我多。”
吳平來自四川省邛崍市回龍鎮(zhèn)。2007年,《中國新聞周刊》曾經(jīng)走訪這個距離成都75公里的縣級市。當(dāng)時,鄉(xiāng)村和中小城鎮(zhèn)的人們已經(jīng)開始現(xiàn)實地考量自己在教育上的投入產(chǎn)出,他們明白,“考上大學(xué)”不等于“改變命運”。8年來,這里的人們對待教育的態(tài)度仍然在發(fā)生細(xì)微的變化。他們既想努力掙脫升學(xué)教育模式的束縛,又不得不在傳統(tǒng)教育體制下無奈妥協(xié)。
“以后不如把孩子送去澳洲搬磚”
勉強考上高中后,吳平的成績一直在三本分?jǐn)?shù)線上下浮動。他學(xué)習(xí)一直一般,分?jǐn)?shù)不高不低,馬馬虎虎。他一直不認(rèn)為這是個問題,也沒有考慮過以后自己的出路。一直到高二那年寒假,媽媽突然對他說:“考不上一本二本,就干脆不要念了。”
以這樣的方式,“未來”第一次出現(xiàn)在了吳平眼前,但他對此并不驚訝。在鄉(xiāng)里,讀書、考大學(xué)當(dāng)然是同學(xué)們的首選,可只有成績非常好的孩子才會被家長寄予厚望。
他現(xiàn)在模糊記得高中那幾年的幾則新聞:“清華碩士賣菜”,“北大學(xué)生賣豬肉”,具體內(nèi)容他說不上來,但對成績不好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而言,那些成為一個談資,或者是放棄大學(xué)學(xué)業(yè)的論據(jù)。“大學(xué)改變?nèi)松彼坪跏呛芫靡郧暗恼撜{(diào),在家務(wù)農(nóng)的父母和自己對此都沒有太認(rèn)真。
爸爸對吳平的期待是,學(xué)個有用的技能,有“真本事”,以后好找工作。吳平喜歡看書,中學(xué)時常常讀些小詩,寫點小文章,但文理分班時還是果斷選了理科。鄉(xiāng)里的同學(xué)大多數(shù)都念理科——專業(yè)選擇范圍寬,聽說以后掙得也多。
直到高考前,他才發(fā)現(xiàn),“原來那么多人要上好大學(xué),而好大學(xué)就那么幾所”。考試期間他一直很忐忑,想不到最后竟然超水平發(fā)揮,考上了西南民族大學(xué),一所二本學(xué)校。他興奮極了——無論如何,得到父母的支持到省會上大學(xué)是件好事。每次假期回家跟同學(xué)朋友見面,他都非常自豪。
可他只自豪了三年。大三時,他開始試著找工作,卻剛好遇上了“最難就業(yè)季”。這是在2013年,中國高校畢業(yè)生人數(shù)比前一年多出19萬,創(chuàng)歷史新高,而就業(yè)崗位卻不增反減。吳平發(fā)現(xiàn),有一些企業(yè)甚至喜歡要大專生:工資能比本科低好幾百,“性價比高”。
在長達(dá)7個月的尋找、碰壁、試用和放棄之后,他終于被一家小公司錄用。在這里,他所學(xué)的專業(yè)基本用不上,自己的工作“高中生也能干”。最受不了的是每次回老家,一些高考失敗的同學(xué)經(jīng)常無意間聊起一個以“讀書無用”為中心的話題。吳平每次都訕訕地坐在一旁,心里不大高興,但卻無力反駁。

教育的本質(zhì)是讓每一個人更好地發(fā)展、消除等級。現(xiàn)在我們的教育功利化了,反而在增強等級。攝影/Elizabeth Dalziel
30年來,在他生活的這個小城市,人們對教育的態(tài)度在不停地發(fā)生變化。上世紀(jì)的家長們執(zhí)著于“知識改變命運”,這樣的觀點一直延續(xù)到本世紀(jì)初期:孩子只要上一所大學(xué)就已經(jīng)不錯。
2002年以后,大學(xué)擴招的影響開始顯現(xiàn),邛崍市的教育理念漸漸轉(zhuǎn)變。有人開始現(xiàn)實地琢磨:念完大學(xué)出來找不到工作,還不如讓孩子直接去打工。2007年,邛崍市道左鄉(xiāng)教導(dǎo)主任吳剛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當(dāng)年是不上大學(xué)一輩子受窮,現(xiàn)在是上了大學(xué)馬上就受窮。”
而這之后的8年時間里,大學(xué)生找工作變得越來越難。根據(jù)第三方調(diào)查機構(gòu)北京麥可思公司的調(diào)查,從2012年10月到次年4月間,被調(diào)查的2013屆碩士畢業(yè)生簽約率為26%,本科畢業(yè)生僅為35%,比2012屆同期低12個百分點。
“很多大城市高學(xué)歷的同學(xué)回來,發(fā)現(xiàn)自己還不如在當(dāng)?shù)赜嘘P(guān)系的本地同學(xué)賺得多,這種情況挺普遍的。”25歲的邛崍人楊川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楊川從四川外國語大學(xué)畢業(yè)后,回到邛崍文昌中學(xué)教英語,學(xué)生都是“00后”,而她能明顯發(fā)現(xiàn)自己現(xiàn)在的學(xué)生對成績的追求“沒有自己那一代那樣強烈”。在高中同學(xué)聚會上,她的一個同學(xué)提起最近網(wǎng)上熱議的“澳大利亞留學(xué)不如搬磚”新聞,打趣說:“以后不如把孩子送去澳洲搬磚,另一個當(dāng)電焊工,當(dāng)個國際包工頭。”
對目前的農(nóng)村人來說,所有類似的社會新聞和就業(yè)率數(shù)字都讓他們對高考、教育的態(tài)度走向兩極。“現(xiàn)在很多鄉(xiāng)村家長覺得孩子得上二本、甚至上一本,今后才有可能有出息,”21世紀(jì)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對《中國新聞周刊》說,“上大學(xué)不再是目標(biāo),上一本院校才是目標(biāo)。”
“只有進(jìn)入層級更高的學(xué)校,你才有可能更有出息”
1997年出生的屈志林來自邛崍水口鎮(zhèn)馬湖鄉(xiāng),目前在邛崍二中念高二。他生活在單親家庭,爸爸是“70后”,靠打工撫養(yǎng)他長大,從小就告訴他:好工作就是坐在辦公室里,不用出去風(fēng)吹日曬。
屈志林想過自己的未來:考上大學(xué)后要一邊體驗大學(xué)生活,一邊進(jìn)行社會實踐,這樣“將來找工作更方便,也更鍛煉能力。”他不想上研究生,因為“浪費青春,而且出來以后年紀(jì)大了,家里又沒什么背景,就算考進(jìn)了公務(wù)員,估計升職也有困難。”除此之外,他沒有更清晰的目標(biāo)和計劃。
但在家里人看來,從老家考進(jìn)市里的高中,屈志林已算完成了第一步。
在邛崍,如果成績夠好、家庭條件符合,教育完全可以按部就班。這個城市一共有43所小學(xué),有4所在城里;最有名的初中是市里的民辦學(xué)校文昌中學(xué),最好的高中則是省重點邛崍一中。
好學(xué)校都集中在城市。鄉(xiāng)村學(xué)校雖然近年來有了塑膠跑道、多媒體教學(xué)設(shè)施,但師資力量十分薄弱。杭州師范大學(xué)的研究者容中逵發(fā)現(xiàn),2012年,四川農(nóng)村教師月薪低于2500元的比例分別為81.4%,而當(dāng)年四川省城鎮(zhèn)職工的月平均工資為3160元。“現(xiàn)在成都市里學(xué)校的老師招收的都是北京師范大學(xué)這樣的名校學(xué)生,我們邛崍市里的學(xué)校招一些本省二本學(xué)生,到了城郊、農(nóng)村,師資來源就越來越差。”邛崍市教育局基礎(chǔ)教育科科長張永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在這個縣級市的66萬人口里,中心城區(qū)人口只有16萬到18萬,大部分人都分布在當(dāng)?shù)?4個鎮(zhèn)鄉(xiāng)。25年前,邛崍市的鄉(xiāng)村小學(xué)有329所,人最多時每個年級的學(xué)生達(dá)到15000人,而現(xiàn)在村小數(shù)量已經(jīng)銳減至4所。“銳減原因是生源越來越少。”張永紅說。人口流動越來越大,很多農(nóng)民工帶著孩子外出打工,也有一些家庭遷往城市居住。
21世紀(jì)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這樣總結(jié)近十年來鄉(xiāng)村民眾教育態(tài)度的不變之處:“我們現(xiàn)在的教育制度沒有發(fā)生變化。基礎(chǔ)教育的模式仍然還是升學(xué)教育的模式,哪個地方的資源越好,家長就往哪里搬,農(nóng)村空虛化越來越嚴(yán)重。”
在傳統(tǒng)升學(xué)教育模式下,念書就像“打怪升級”,重點院校們引導(dǎo)學(xué)生一級級往上爬。考上高中的學(xué)生無疑是經(jīng)過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分流——在屈志林的初中同學(xué)里,除了少數(shù)幾個去當(dāng)兵的,接近一半在中考失敗后上了職業(yè)學(xué)校,有的現(xiàn)在已經(jīng)開始實習(xí)掙錢了。但整體而言,普通高中還是家長們的第一選擇。
“對絕大多數(shù)邛崍家長來說,送孩子去念職業(yè)學(xué)校是一種無奈的選擇。”邛崍市教育局基礎(chǔ)教育科科長張永紅說。他介紹,市里普通高中和中等職業(yè)學(xué)校的入學(xué)人數(shù)大概是3:2,這意味著很多中考達(dá)不到分?jǐn)?shù)線的學(xué)生還是選擇用各種渠道擠進(jìn)高中或民辦高中。
就算進(jìn)入普通高中,學(xué)生也要為擠進(jìn)更好的層級而努力——大多數(shù)高中都按成績分為快慢班,比如省重點高中邛崍一中就有“火箭班”。在邛崍百度貼吧,一些學(xué)生們在為進(jìn)入一中的普通班還是市重點平樂高中的“精英班”而發(fā)愁:雞頭還是鳳尾,哪個才能考進(jìn)更好的大學(xué)?
熊丙奇認(rèn)為,中國學(xué)生正在經(jīng)過從中考到高考的一系列分流、分層:初中高中分重點普通,大學(xué)分211、985、一二三本,而輿論、教育的關(guān)注點都在更高的層級上,“只有進(jìn)入層級更高的學(xué)校你才有可能更有出息,”他說,“如果所有大學(xué)生都盯住金字塔尖,中國的教育就只為這很少的一部分人服務(wù)。再這樣強調(diào)升學(xué),教育將面臨非常嚴(yán)重的危機。”
寒門與貴子
高中時,吳平已經(jīng)發(fā)現(xiàn),“高考面前并不是人人平等”。
一些同學(xué)可以有其他的選擇。有幾個同學(xué)準(zhǔn)備自費出國;有些同學(xué)決定報考藝術(shù)類院校或?qū)I(yè),可以以很低的分?jǐn)?shù)考上名校。
吳平幾乎不敢想這些。“那都是經(jīng)濟條件不錯的同學(xué),”他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有個女生從小學(xué)畫畫,我哪有機會學(xué)?”
至于出國,他連學(xué)費都沒敢問過。“當(dāng)時覺得出國是很遙遠(yuǎn)的事。”他回憶。
相較而言,農(nóng)村孩子起點更低,這在英語學(xué)科上有更為明顯的體現(xiàn)。邛崍市文昌中學(xué)的英語老師楊川發(fā)現(xiàn),就英語學(xué)科而言,農(nóng)村來的學(xué)生雖然比城里學(xué)生要踏實扎實、后勁大,但初一剛進(jìn)校時都基礎(chǔ)很差。“有的城里孩子幼兒園就開始接觸英語,或者有參加補習(xí),我講的很多知識他們都懂;但大多數(shù)農(nóng)村孩子除了26個字母,其他都不知道,感覺完全沒學(xué)過。”楊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她的印象里,多數(shù)家庭教育出色的孩子學(xué)習(xí)能力更強、更有目標(biāo)。班里有一個男孩的父親是工程師,而男孩從一進(jìn)校起就對楊川說,自己未來也要當(dāng)工程師,“成為一個像爸爸那樣優(yōu)秀的人”。而農(nóng)村的孩子“更偏向于一定要讀好書,讀一個好大學(xué),讓家里人幸福。”
從官方數(shù)據(jù)看起來,邛崍當(dāng)?shù)氐妮z學(xué)率很低。根據(jù)邛崍市教育局對《中國新聞周刊》出示的統(tǒng)計報表,2014年全市的初中升學(xué)率達(dá)到99.81%,高中升入更高一級院校的比率則是98.80%。“這些年基本都保持在這個數(shù)據(jù)上,”邛崍市教育局高中科科長劉華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即使是農(nóng)村,高中畢業(yè)后出去打工的人才會比較多。”
但研究者普遍認(rèn)為,實際情況會遠(yuǎn)遠(yuǎn)不如官方數(shù)字那樣“看上去很美”。除去流動人口的異地就學(xué)情況無法統(tǒng)計,大量的農(nóng)村留守兒童都存在輟學(xué)問題。“我們原來的很多情況是基于人不流動的體系,跟不上時代的變化了,”熊丙奇說,“也就是思路、做法還停留在以前,但是人已經(jīng)跑到前頭去了。”
在2012年舉辦的“農(nóng)村教育辦學(xué)布局調(diào)整研討會”上,北京西部陽光發(fā)展基金會秘書長提到,四川某縣的幾個村莊小學(xué)輟學(xué)率高達(dá)70%。2009年,西北師范大學(xué)一項關(guān)于甘肅、寧夏、青海三地農(nóng)村留守兒童輟學(xué)現(xiàn)狀的研究表明,農(nóng)村留守兒童的輟學(xué)率占留守兒童總樣本的29%,與2005年相比輟學(xué)比例有所反彈;而且,由于和父母聚少離多,缺乏監(jiān)護(hù)和關(guān)愛,這些留守兒童的學(xué)習(xí)成績大都較差。
2011年,一個中學(xué)教師linyang222發(fā)帖稱“這個時代寒門再難出貴子”,指出“成績都是錢堆出來的”“寒門學(xué)子輸在了教育起跑線上”,引發(fā)熱議。
“現(xiàn)在‘寒門難出貴子’是事實,”邛崍市教育局基礎(chǔ)教育科科長張永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現(xiàn)在的教育,(成績和能力)偶然性已經(jīng)大為降低,讀什么學(xué)校、接受什么樣的教育,造成的不同結(jié)果幾乎是必然的。一般家庭條件優(yōu)越的孩子從出生開始就會比較注意教育,結(jié)果可想而知。”
北京理工大學(xué)教育研究院教授楊東平的研究顯示,以湖北省為例,2002到2007年5年間,重點高校里的中產(chǎn)家庭、官員、公務(wù)員子女是城鄉(xiāng)無業(yè)、失業(yè)人員子女的17倍。
熊丙奇認(rèn)為,中國學(xué)校單一通道分層是造成問題的一大原因:“如果所有人進(jìn)的學(xué)校都是平等的,還會有什么階層固化?上職業(yè)學(xué)校也是一個出路,為什么一定要上重點大學(xué)才是貴子?”
“教育的本質(zhì)是讓每一個人更好地發(fā)展、消除等級。現(xiàn)在我們的教育功利化了,反而在增強等級,”熊丙奇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在學(xué)校分層、生源固化的前提下,教育的目的已經(jīng)變成制造成功者和失敗者,制造貴子和非貴子。”
(應(yīng)受訪者要求,文中吳平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