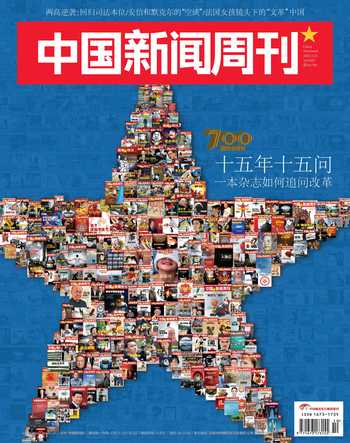“錢學森之問”的余音
錢煒 萇清
2009年10月31日,中國科學巨匠、“兩彈一星”功勛錢學森去世。當時,《中國新聞周刊》以“錢學森的遺產”為主題做了封面報道。這組報道從不同側面表達了“世上已無錢學森”的悲痛與遺憾;與此同時,“中國的下一個錢學森在何處?”這個問題也在中國失去錢學森的時候帶給了人們些許焦慮與茫然。
在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的今天,“錢學森之問”的現實意義愈加凸顯,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深層次上進行挖掘。
在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的今天,“錢學森之問”的現實意義愈加凸顯,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深層次上進行挖掘
2009年10月31日,中國科學巨匠、“兩彈一星”功勛錢學森去世。當時,《中國新聞周刊》以“錢學森的遺產”為主題做了封面報道。這組報道從不同側面表達了“世上已無錢學森”的悲痛與遺憾;與此同時,“中國的下一個錢學森在何處?”這個問題也在中國失去錢學森的時候帶給了人們些許焦慮與茫然。
早在十年前,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前往探望錢學森時,長臥病榻的的錢老發出這樣的感慨:“回過頭來看,這么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學森認為,“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錢學森的這些擔憂被他概括為一個問題:“為什么現在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杰出人才?”
這位科學老人當年的赤誠相問,衍化成這個國家和民族綿長的思索。如今,錢學森雖然離開我們了,可是讓他難以釋懷的世紀之問,言猶在耳。在加快創新型國家建設步伐的今天,“錢學森之問”的現實意義愈加凸顯,這個問題的答案,需要在深層次上進行挖掘。
實際上,錢學森所渴望的“杰出人才”,正是國家目前所呼喚的“創新型人才”。雖然中國的人才戰略強調把培養創新型人才作為科教發展的重要目標,但是沿著“錢學森之問”來回顧近年來的科技人才培養和科技創新發展的現狀就會發現,中國科技發展中存在的諸多問題依然存在,假如不能進一步營造健康的大環境,中國科技發展的某些問題甚至會趨于更加嚴重。
“中國缺乏產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環境”
2014年,中國科技研發人員總量達到380萬人,位居世界第一;國際科技論文數量穩居世界第2位。全社會R&D( 研究與開發)支出達13400 億元,其中企業R&D支出占76% 以上。
教育部公布的2011~2014年全國研究生(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招生計劃通知顯示,中國研究生招生總規模從2011年的560495人,擴大到2014年的631020人,2014年比2011年增加了12.6%。據教育部副部長杜占元透露,自1981年我國學位制度建立以來,30多年間共培養博士研究生49萬人,碩士研究生426萬人;其中近5年培養的研究生數量約占培養總量的50%。
以上一個個數字說明,中國并不缺少科技人才,但是在擁有這樣一個數量龐大的科研人員群體的情況下,為何我們迄今還不能給“錢學森之問”一個有力的答案呢?很顯然,雖然人才培養規模日益壯大,但質量提升緩慢,創新型人才培養的質量并不理想。
錢學森在他人生最后一次系統的談話中曾經說:“今天我們辦學,一定要有加州理工學院的那種科技創新精神,培養會動腦筋、具有非凡創造能力的人才。我回國這么多年,感到我國還沒有一所這樣的學校,都是些一般的,別人說過的才說,沒說過的就不敢說,這樣是培養不出頂尖人才的。”
曾經培養出錢學森的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光是為中國就培養了很多著名科學家。例如,錢偉長、談家楨、郭永懷等等都是從加州理工學院學習歸來的。

對于前輩的感慨,北京大學教授、著名神經生物學家饒毅深有同感,他也認為:“中國成為世界強國不僅需要一般人才,而且需要較多的杰出人才。但是,中國缺乏產生杰出人才的文化環境。”在饒毅看來,中國文化產生的環境和體制埋葬了中國的愛因斯坦、比爾·蓋茨、斯蒂夫·喬布斯……
“中國盛產人際關系自如的小聰明、學習能手的中聰明,缺乏能夠給國家和人類帶來進步的大聰明。改善文化,減少小聰明、增加大聰明,是中國崛起所必需的。”這位新一代海歸的代表性人物認為,“我們缺乏發現、培養、支持優秀和頂尖人才產生的環境,沒有形成一支強有力的優秀人才隊伍,所以尚未建立起保障中國崛起和長期領先的堅強基礎。”
饒毅認為,不僅是和國際比較,中國現在的科技人才成長環境也遠遜于中國近代史上曾經出現過的西南聯大、兩彈一星的智識群體。如果我們比較中國近代史,西南聯大來源于清華大學的數學系,曾同時有陳省身和華羅庚,中國數學的高峰可能不是現在,而是那時。生物醫學研究的高峰是上世紀20年代到30年代的協和醫學院。
饒毅2007年從美國全職回國,他向來以對中國科學文化的大膽批評和反思而著稱,他甚至2011年在中科院院士增選中落選后,公開宣布“將不再成為候選人”,并表示“不做院士照樣可以挺起腰桿”。對于中國培養頂尖科技人才的不利環境,饒毅認為,“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文化上有重大缺陷”。他總結道,中國的文化是“做人的文化”優先于“做事的文化”。
按照饒毅的解釋,做事的文化強調創造性,對人的個性要求比較簡單明了,要講道德、有原則、要誠實,也鼓勵樂觀。這些簡單的為人基準,在少年兒童期間教育好,以后都要遵循,無需經常琢磨。
而做人的文化強調處人。在目前的中國,做人提倡的是對上級、對老人、對周圍的圓滑,所謂做人“成熟”和“聰明”,而不是講道德。做人的文化,不是絕對不要做事,而是做事不那么重要,特別是和“做人”發生沖突的時候,“做事”就讓位于“做人”了。
1955年8月,中國方面以釋放11名美國飛行員戰俘的條件換取錢學森回國。雖然當時的那一代海歸回國的歷史背景與新一代海歸有所不同,但是,錢學森及其所代表兩彈一星功勛科學家群體的回歸,是在得到國家支持的情況下,大膽做中國人沒有做過的事業的。他們敢于在國外封鎖的情況下,自己探尋出道路,最終為國家立下鼎足之功。
在饒毅看來,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錢學森那一代科學家回國就是來“做事”的。他認為,現在,雖然很多人也號稱做“國家需求”的科學研究,并因而得到強力支持的,但其中既有好的課題,也有一般的課題,甚至還有很差的課題。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是有人把科研項目的立項、評審,變成了服務某些人利益和關系的手段。“識相”和“圓滑”的人得到支持,而創新和做事被學術以外的因素所排擠。饒毅認為,在當代,科學文化的局限已經直接影響中國科學的發展。
科學文化是近代科技革命實踐的產物。16、17 世紀以來,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相對獨立的科學文化系統逐漸形成。科學文化的內涵主要包括科學知識、科學思想方法和科學精神幾個方面,而其核心則是科學精神。
“我們希望中國科學上升的曲線不止三十年”
科學精神是科學共同體在追求真理、逼近真理的科學活動中所形成與發展的一種精神氣質。科學文化的發展和弘揚,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發人們的創新熱情,充分體現科學之魂。科學精神是科學文化創新的動力。
“在中國的科學似乎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今天,也需要看到,近十幾年來,我國科技投入增長很快,但另一方面,中國社會和青少年越來越熱衷于付出少而收獲大的職業,對科學的熱情越來越小。這不限于國內的學子,也包括海外華人在內。也就是說,我們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又出現了新的問題。”
這是饒毅對中國科技事業發展的另一方面的擔憂。對于上述狀況,他認為,可能導致的后果是,我國科學的最高峰就在今后三十年內,原來有熱情的人繼續努力形成中國科學上升的曲線,而隨后,后繼人才的短缺則會形成科學的平臺期或下降曲線,它們的交匯或許將決定我國科學未來走向。
在饒毅所任教的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的錄取分數線遠比生物學專業高得多。他笑言,“蔡元培說過,中國人讀書多為升官、發財。我擔心我們的惡習又復發了!所以我很支持反腐,這樣能讓更多中國人投身自然科學研究!”
在饒毅看來,我們不能忽視社會環境變化引起的新問題,中國離全面小康尚有距離,而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已呈下降趨勢。如何避免下降的曲線不僅是科學界的問題,也是中國社會的問題。“未來的中國固然無需如1956年或1978年那般全社會對科學的熱情,但是如果不未雨綢繆,中華民族在科學上是否會未老先衰呢?饒毅說,“我們希望中國科學上升的曲線不止三十年!但對此不能僅僅依賴盲目的信念,而要改革體制,提高效率、并想方設法消除潛在危機。”
構成對中國科技發展前景的另一個擔憂是,在科技成果轉化方面不盡人意的現狀。饒毅認為,社會上,有些人對科學的實質了解不夠,不打好地基就建樓,急切要求將研究轉化為應用,甚至譏笑和抨擊基礎研究,不知道先進國家在相當大量和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后,才產出少量有應用價值的成果。
的確,中國將不成熟的國內外研究成果莽撞地進行轉化的情況多于國外。甚至有時在國外已被證明不能轉化的東西,卻在中國被善于忽悠者用于牟取私利。這些“轉化”無法長久,也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
以中國干細胞科研的轉化為例,《自然》及《經濟學人》等知名雜志都曾對中國混亂的干細胞市場進行過嚴厲的批評。很多公司在利益的驅使下,鋌而走險,很多治療手段并沒有在國家衛生相關部門得到審批就對病人進行治療。而有些公司則打著干細胞庫、儲存干細胞的名義,向病人索要高昂的費用。急功近利的普遍社會心態不僅讓“愛科學”的純真信念不能與改革開放之初相比,打著科學幌子的商業運作也破壞了公眾對科學理念的尊重。
饒毅說,不科學的東西在中國社會很容易流行,反科學的東西也不時冒出來,甚囂塵上。在我國,科學能否成為文化的核心之一,可能問題還很大。我們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心、對邏輯的嚴密把握、對事物的客觀態度……都“仍需努力”。
錢學森在其生前的最后一次系統談話中說:今天,黨和國家都很重視科技創新問題,投了不少錢搞什么“創新工程”“創新計劃”等等,這是必要的。但我覺得更重要的是,要具有創新思想的人才……回國以后,我覺得國家對我很重視,但是社會主義建設需要更多的錢學森,國家才會有大的發展。
在這次談話的最后,錢學森感慨說,“我今年已90多歲了,想到中國長遠發展的事情,憂慮的就是這一點。”
在錢學森去世五年后的今天,中國新一代領導人分析國內外大勢、立足中國發展全局,作出了創新驅動發展的重大戰略抉擇。
2014年,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指出,“創新的事業呼喚創新的人才…… 要把人才資源開發放在科技創新最優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養、引進、使用等機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學家、科技領軍人才、工程師和高水平創新團隊,注重培養一線創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在中國,錢學森不僅是一位科學家的名字,而且是對科學家這個詞的詮釋。也許,當代科技人才與錢學森那一代人的家國情懷會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但是,以創新為基礎的科學精神是永恒的。這種精神與國家強調科技創新的全局發展戰略具有高度的統一。崛起的中國需要又一個更加燦爛的“科學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