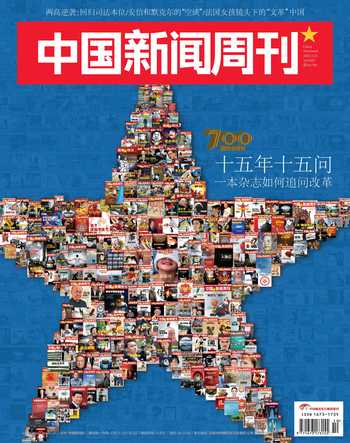如何擴大中產規模
李春玲
中國中產的幸福感正趨弱,在物質生活上的不安全感,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著他們的自我實現:向上流動的渠道不夠通暢,未能形成屬于自己的文化趣味,未能承擔起對社會應盡的責任等。
從“中產被消失”到“中產信念”“中產跑步潮”等,本刊一如既往關注中國中產話題,就是因為中產階層是打造幸福的“橄欖型”社會的關鍵。一個理性、建設性的中產大軍是中國現代型社會的基石。
中產階層的幸福感趨弱,“ 孩奴”“房奴”等種種議論應運而生;與此同時后備軍進入中產的年限在拉長
關于中國中產階級的未來,有許多說法。美林公司曾于2005年預測,未來10年內,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將達到3.5億。同年國家統計局根據人均GDP和購買力給出中產階級的家庭年收入在6萬至50萬人民幣之間的結論。
20世紀90年代末期和本世紀的初期,在某些較昂貴的商品銷售廣告和宣傳品中,“中產階級”這一詞匯成為極具誘惑力的廣告用語,比如,房地產項目的廣告宣稱他們的房地產是“中產階級的家園”或“中產階級社區”;中高檔轎車銷售時聲稱某一品牌的汽車是專為“中產階級”或“專業人士”量身打造;而一個網站的宣傳口號是“我們的目標是成為城市中產階級小區居民的第一生活品牌”。一時之間,“中產階級”一詞成為廣告和傳媒中極為盛行的用語。在商家和傳媒的宣揚之下,中產階級成為都市青年人奮斗的目標,同時,中產階級一詞也成為了大眾話語中的一個流行詞匯。
其實,這種中產形像來源于歐美發達國家的中產階級生活狀態。毫無疑問,在目前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條件下,這種所謂的中產階級絕不是中間階級( 處于中等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 ,而應該是中間階級( 社會學家所定義的中產階級)的上層部分。符合公眾輿論標準的中產階級在中國人口中只占極少數,其比例不會超過10%。
政府領導人和黨內理論家也提出一些類似中產階層的社會群體界定,比如“新社會階層”和“中等收入群體”。2001 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七一講話”中,提出新的社會階層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這些新階層包括: 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非公有制企業中的管理人員和專業人員以及自由職業者等,這一部分人正是中國中產階級中數量增長很快的部分。同時期政府決策者提出的“三個代表”理論,也表示中國共產黨不僅是工人階級的利益代表,同時也是這一部分中產階級成員的利益代表。
新中產,老中產
有一個說法,當代中國社會最富裕的10類人分別是:私營企業主和個體戶;國有企業承包或租賃經營人員;股市上的成功者;三資企業的高級員工;有技術發明的專利人員;演藝界、體育界的明星;部分新經濟的CEO;部分律師、經紀人和廣告人員;部分歸國人員;部分學者、專家。
尤其值得引起人們注意的是私營企業主以及三資企業的高級員工——他們代表中國中產嗎?
劃分中國中產階級的三個標準:依據西方學者的中產階級職業、教育和收入標準來劃分中國社會的中間階層,也就是說,把擁有一定教育水平( 教育標準) 和中等收入水平( 收入標準)的白領職業從業者(職業標準)歸類為中間階層。
不過,在職業分類方面,我們需要注意中國社會的特殊性。當前中國社會存在著相當數量規模的個體工商戶、農業或運輸業專業戶、建筑等行業的包工頭等各種小業主和小雇主,他們通常擁有中等或中等水平以上的收入,但其中有一部分所從事的經營活動屬于半藍領或藍領職業。如果按照嚴格的白領職業界定,他們就被排除在中間階層之外。這類人被西方中產階級理論家稱之為“老中產階級”(與新中產階級相對應)。
我們參照西方學者的分類,即專業人員、管理人員和中小企業主是上層中間階層,我們可以稱之為中產階級;其它白領從業人員以及小業主和小雇主是下層中間階層,下層中間階層又有兩個部分組成: 一個是工薪階層,即中下層白領從業者;另一個是小業主階層,其成員包括各類個體工商戶、農業或運輸業專業戶、建筑等行業的包工頭等。
劃分中產階層的收入標準應該是多少?專家和學者提出的標準差距極大。有些人提出年收入5000 美元以上即為中產階級,而另一些人則認為年收入達到30000 美元以上的人才能稱之為中產階層。由于極大的地區及城鄉收入差距,確定統一的中產階層收入標準是極為困難的,因而,至今為止,依據收入標準劃分的中產階層以及依據這一標準估計的中產階層規模未能獲得廣泛的認同。
不滿足感,不安全感
一般認為,中間階層的發展壯大有助于社會穩定,因為中間階層的成員擁有穩定的收入、體面的工作和相對富足安逸的生活,他們應該對社會及個人的生存狀態較為滿意,不希望發生社會動蕩和劇烈的社會政治變動。這意味著,中間階層這一群體的界定不僅包含收入、職業等客觀指標,同時也涉及個人的主觀認同和社會心態。
一個社會中,不論其客觀指標定義的中間階層人數有多少,如果絕大多數人都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那么這個社會是較為穩定的,人們的社會滿意度會比較高。
然而,中國中間階層的自我認同出現了一個奇怪現象:一些達到了中等收入并從事“白領”職業的人并不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反而認為自己是“被中間”了。僅有約10% 的人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
全國性的抽樣調查數據顯示,當前中國人的地位認同有一種向下認同的傾向,這導致了中間階層的自我認同比例遠低于其他國家。在一些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認為自己是中間階層的比例一般在50%~70%之間,而我們的問卷調查顯示,中國僅約40%的人承認自己是中間階層,而約30%的人認為自己是中下層,約20%的人稱自己是下層階層。

2015年2月,一名中國女孩在美國著名的海水浴場邁阿密海灘玩耍。
這反映出中國中間階層對于自身地位狀況處于一種不滿足、不滿意和不安全的狀態,這樣一種心態在互聯網的各種論壇、博客和跟帖中有充分體現,即許多人表現出對自己的收入水平、生存境遇、工作狀態不滿意,對時政問題和社會現象經常性地發表批評言論。
中間階層會有不滿足和不滿意的情緒,一個重要原因是,許多中間階層成員在評價其自身地位狀況時總是與上層及中上階層的生活境遇相比較,而當前收入差距的不斷擴大導致上層與中間層之間的差距也在拉大,前者中的少數人通過不正當手段牟取巨額財富,這使中間階層成員產生了強烈的不公平感。
導致中間階層不安情緒的另一重要原因是,近年來中間階層成員感受到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壓力和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壓力,其中最突出的兩個壓力是就業和購房。中間階層的中青年成員尤其感受這方面的沉重壓力。以往的大學畢業生奮斗5至8 年應該可以達到一種穩定的中間階層生活水平,而現在他們可能需要奮斗10 年甚至20 年才有可能過上他們所希望的生活。另外,缺乏社會保障也是導致中間階層不安情緒的一個重要因素。一些有房有車、有穩定職業和收入的中間階層成員仍然擔憂他們的地位穩定性和未來的保障,生一場病或者發生意外事故,都有可能導致他們生活水平下降。

實際上,我們的調查顯示,中間階層對個人生活現狀的滿意度還是較高的,70%的新中產階級聲稱過去3 年他們的生活水平上升了。毫無疑問,高速經濟增長使中間階層極大受益,他們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穩步提高,而且他們也預期未來幾年的收入和生活水平還將繼續提高。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于政府的政策和制度持基本肯定的態度,對于政府的治理能力有較高的信任度。他們在公眾輿論和網絡媒體上表現出對政府的諸多批評和不滿,目的只是希望影響政府決策者去調整、修改或強化相關政策。
我們的社會不僅需要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更需要培育一個心態穩定、對個人生活具有較高滿意度、對社會具有責任感的中間階層。控制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緩解中間階層的生活成本壓力和就業壓力,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將有助于社會中間階層的穩定發展。
打造幸福的“橄欖型”社會需要“擴中”
目前中國社會不僅中產階級在人口中的比例很小,而且中間階層的比例也比較低。廣義的中產階級即年收入30000 元及以上水平的中間階層為16.8%;狹義的中產階級即按本文設定的中產標準( 同時滿足職業、教育和收入三個條件) 僅為7.7%!
龐大的低收入農民人口和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農民工群體,以及相當數量的貧困失業人群,制約了中間階層和中產階級的規模。
要擴大中產階級,首先要擴大中間階層,讓更多的農民、農民工和城鎮藍領工人進入中間階層的行列,與此同時,要讓更多的中間階層成員提升職業地位、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而進入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最近十幾年來快速的高等教育擴張、城市化推進以及近年來的經濟結構轉型,都有助于擴大中間階層和中產階級。
但是,目前的擴張速度并未讓急于想加入中間階層和中產階級的民眾滿意。成為中產階級是許多大學畢業生年輕人的夢想,成為城市中間階層一員是眾多的80后和90后農民工的夢想。然而,城市中的高昂房價,不斷上升的生活成本,低層白領職業崗位競爭激烈而且收入偏低,以及自主創業和個體經商環境惡劣,阻礙著年輕人實現他們的夢想。
政府決策者需要系統考慮擴大中間階層和中產階級的思路,從多個層面采取扶助政策,讓更多的中青年人用更短的奮斗年數邁入中間階層和中產階級行列。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