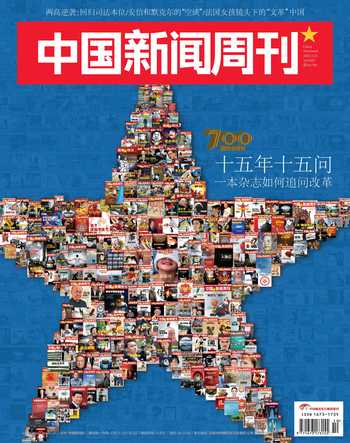安倍和默克爾或是一場(chǎng)“空談”
馮瑋
默克爾此次訪問畢竟不是為了去給安倍上“歷史課”,雙方還商定共同推動(dòng)聯(lián)合國改革,使日德兩國能成為安理會(huì)常任理事國。但日本“入常”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在2008年參加北海道洞爺湖舉行的八國集團(tuán)峰會(huì)后,時(shí)隔7年,德國總理默克爾再度踏足東瀛。此次訪問,默克爾在一天內(nèi)兩次敦促日本“正視歷史”引起輿論廣泛關(guān)注。不過,默克爾此次訪問畢竟不是為了去給安倍上“歷史課”,安倍等在歷史問題上的頑固立場(chǎng),也不可能通過“聽一堂課”而幡然醒悟。
據(jù)日媒報(bào)道,2015年3月9日,即默克爾到訪當(dāng)天,安倍即在首相官邸與其舉行了約兩小時(shí)會(huì)談,雙方就日德外交部門定期舉行協(xié)商,以促使混亂的烏克蘭局勢(shì)趨向穩(wěn)定,達(dá)成了一致意見。雙方還“心照不宣”地批評(píng)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稱“決不允許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xiàn)狀”。雙方還商定共同推動(dòng)聯(lián)合國改革,使日德兩國能成為安理會(huì)常任理事國。
但此次會(huì)談更多的是鋪陳“外交辭令”,日本很難能有所收獲。
日本在烏克蘭問題上“進(jìn)退兩難”
安倍在和默克爾的會(huì)談中,雖然將烏克蘭問題作為重要議題,但沒有提到對(duì)俄制裁。
2014年3月18日,日本政府發(fā)表聲明稱,由于普京總統(tǒng)簽署法令,承認(rèn)克里米亞為主權(quán)國家,因此日本政府決定對(duì)俄羅斯實(shí)行制裁。制裁措施主要有兩項(xiàng):一是停止兩國間有關(guān)放寬俄羅斯人赴日簽證審批手續(xù)的談判;二是凍結(jié)日俄之間新的投資協(xié)定和宇宙協(xié)定、兩國間避免軍事沖突協(xié)定的談判。外務(wù)大臣岸田文雄在會(huì)見記者時(shí),對(duì)為何制裁俄羅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表示:“日本有必要與西方七國集團(tuán)一道對(duì)俄羅斯實(shí)行制裁。”
去年3月19日,日俄兩國共同主辦的“日俄投資論壇”在東京舉行,受烏克蘭問題影響,雙方原定出席的部長(zhǎng)級(jí)官員均未能參加,僅以主辦方代讀兩國首腦致辭的方式進(jìn)行。烏克蘭問題對(duì)日俄關(guān)系的影響,已現(xiàn)端倪。
4月30日,安倍在德國首都柏林訪問時(shí),與默克爾就烏克蘭問題舉行過會(huì)談,雙方就制裁俄羅斯和為烏克蘭局勢(shì)走向穩(wěn)定展開合作,達(dá)成一致意見。但是,5月24日,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圣彼得堡舉行的國際經(jīng)濟(jì)論壇上的表態(tài),“不久前驚訝地聽說,日本加入了什么所謂的制裁——這和日本有什么關(guān)系,我不大明白。談判進(jìn)程就此暫停了。所以我們是準(zhǔn)備好了,日本準(zhǔn)備好了嗎?我不知道。”普京進(jìn)而發(fā)問:“日本是想中斷在北方領(lǐng)土問題上的對(duì)話嗎?”
2014年7月17日,馬航MH17客機(jī)在烏克蘭境內(nèi)墜毀。美國和烏克蘭稱是親俄武裝發(fā)射的導(dǎo)彈摧毀了這架載有298人的客機(jī)。7月28日,日本內(nèi)閣官房長(zhǎng)官菅義偉在記者會(huì)上宣布,鑒于與馬航MH17客機(jī)遭擊墜毀事件有關(guān)的烏克蘭局勢(shì),將對(duì)俄羅斯采取追加制裁措施。8月5日,制裁正式生效,包括烏克蘭前總統(tǒng)亞努科維奇在內(nèi)的40名有關(guān)人員在日本的資產(chǎn),以及與俄羅斯吞并克里米亞、造成烏克蘭東部不穩(wěn)定形勢(shì)的舉動(dòng)直接相關(guān)的兩個(gè)團(tuán)體的資產(chǎn)被凍結(jié),并禁止進(jìn)口來自克里米亞地區(qū)的物品。
然而,那40人中不包括俄羅斯政要,日本共同社還援引日本有關(guān)人士的話報(bào)道稱,在追加制裁方面,日本政府打算暗中向俄方謀求“理解”,使俄方得知日本在一定程度上顧及了俄羅斯。
在因?yàn)蹩颂m問題而對(duì)俄羅斯進(jìn)行制裁問題上,日本顯然進(jìn)退維谷。2014日7月31日,美國副總統(tǒng)拜登致電正乘坐政府專機(jī)出訪中南美的安倍,稱“美國積極評(píng)價(jià)到目前為止日本政府的應(yīng)對(duì)舉措。日美以及G7繼續(xù)保持緊密合作非常重要。”這番話看似稱贊,實(shí)則施壓。由于歐盟與俄羅斯利害關(guān)系密切,可能難以對(duì)俄態(tài)度更加激烈,所以美國更依賴日本。
美國擔(dān)心日俄接近導(dǎo)致G7的團(tuán)結(jié)被打亂。美國更擔(dān)憂在圍繞烏克蘭局勢(shì)的對(duì)俄追加制裁方面,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七國集團(tuán)(G7)的團(tuán)結(jié)一致可能出現(xiàn)松動(dòng),而日本是否樂意為美國“火中取栗”得罪俄羅斯,美國心知肚明。俄羅斯對(duì)日本的處境當(dāng)然也很清楚。7月29日,俄羅斯外長(zhǎng)拉夫羅夫在日本作出制裁決定后告誡日本:“希望在當(dāng)前的國際局勢(shì)下,日本能夠以其獨(dú)立的立場(chǎng)作出自己的貢獻(xiàn)。”
“領(lǐng)土問題談判”被烏克蘭阻斷
顯而易見,安倍不愿意在制裁問題上得罪普京,影響業(yè)已推動(dòng)的日本尋求與俄羅斯解決南千島群島(日稱北方四島)領(lǐng)土問題的進(jìn)程。
二戰(zhàn)結(jié)束已70周年,日俄領(lǐng)土問題為何懸而不決?
1945年8月10日,美國杜魯門總統(tǒng)致電斯大林,提出以北緯三十八度線為界,劃分雙方“對(duì)日受降分界線”。斯大林原則表示同意,但提出一附加條件:延伸三八線,將宗谷海峽以北的齒舞、色丹、國后、擇捉四島也劃入蘇軍受降區(qū)。杜魯門表示同意。8月28日,蘇聯(lián)紅軍驅(qū)離當(dāng)?shù)厝哲姡碱I(lǐng)了這四個(gè)島嶼。由此形成日蘇(俄)關(guān)系迄今難以解開的一個(gè)“結(jié)”。
1956年,雙方發(fā)表《日蘇共同宣言》,代替和平條約確定終結(jié)戰(zhàn)爭(zhēng)狀態(tài)、恢復(fù)外交關(guān)系等。該宣言規(guī)定,日蘇之間恢復(fù)正常外交關(guān)系之后,仍將繼續(xù)進(jìn)行相關(guān)締結(jié)和平條約的談判,待和平條約締結(jié)之后,將齒舞群島及色丹島歸還給日本。
1991年4月戈?duì)柊蛦谭蚩偨y(tǒng)訪日并與日方發(fā)表《日蘇共同聲明》,蘇方首次在文件中具體寫進(jìn)四島名稱,并承認(rèn)存在領(lǐng)土劃分問題。
1993年10月葉利欽訪問日本,雙方發(fā)表《東京宣言》,“宣言”第2款中明確了如下談判方針:將領(lǐng)土問題定位為四島歸屬問題;待四島歸屬問題解決后,締結(jié)和平條約并實(shí)現(xiàn)兩國關(guān)系正常化;將領(lǐng)土問題立足于歷史和法律依據(jù),以根據(jù)兩國間的共識(shí)達(dá)成的諸文件及法律和正義的原則為基礎(chǔ)加以解決。

2015年3月9日,日本東京,德國總理默克爾(左)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出席聯(lián)合新聞發(fā)布會(huì)。會(huì)議前,兩人在歐盟旗幟前談話。
2001年3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和俄羅斯總統(tǒng)普京在俄羅斯伊爾庫茨克簽署了《伊爾庫茨克聲明》,再次確認(rèn)日俄共識(shí)。
2012年12月,安倍再次當(dāng)選首相后,誓言最終解決北方四島問題,并爭(zhēng)取簽訂日俄和平條約,使日俄關(guān)系正常化。2013年2月,安倍晉三派遣前首相森喜朗為特使前往莫斯科,與普京舉行了會(huì)談。會(huì)談中,普京釋放了強(qiáng)化日俄關(guān)系的意愿,稱“俄日沒有簽署和平條約是不正常的”,并表達(dá)了解決北方四島問題的意愿。2013年4月29日,安倍訪俄并與俄方發(fā)表了聯(lián)合聲明,表示兩國將舉行外交與防衛(wèi)部長(zhǎng)級(jí)磋商(2+2),并在能源、經(jīng)濟(jì)領(lǐng)域加強(qiáng)合作。在一年時(shí)間里,雙方領(lǐng)導(dǎo)人舉行了頻繁而又罕見的五次會(huì)談。尤其是索契冬奧會(huì),安倍不顧歐美國家領(lǐng)導(dǎo)人抵制普京的意愿前往索契,給足了普京面子。
2013年11月初,日本和俄羅斯的外長(zhǎng)、防長(zhǎng)舉行了磋商,標(biāo)志“2+2”機(jī)制開始建立,雙方同意推進(jìn)在有關(guān)亞太地區(qū)安全問題的多邊會(huì)議上的合作,日本海上自衛(wèi)隊(duì)將與俄羅斯海軍開展反海盜合作及聯(lián)合訓(xùn)練。但是,“烏克蘭問題”使之中斷,同時(shí)中斷的還有領(lǐng)土問題談判。
日本不敢得罪俄羅斯,除了領(lǐng)土問題,還顧忌能源。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能源消費(fèi)國和進(jìn)口國,而俄羅斯則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國之一,日本7%的石油和10%的液化天然氣來自于俄羅斯。日俄經(jīng)濟(jì)合作最重要領(lǐng)域是能源,尤其在俄遠(yuǎn)東地區(qū),日方已投巨資進(jìn)行能源開發(fā)。如果因政治關(guān)系影響到經(jīng)濟(jì)關(guān)系,安倍更將遭受來自國內(nèi)壓力。
兩廂情愿也難以“聯(lián)手入常”
安倍和默克爾還商定共同推動(dòng)聯(lián)合國改革,使日德兩國能成為安理會(huì)常任理事國,實(shí)際上是想實(shí)現(xiàn)他久有的夙愿。
日本入常雖然在不同時(shí)期的表現(xiàn)有所不同,但理由始終如一:日本承擔(dān)了很大一部分聯(lián)合國會(huì)費(fèi),應(yīng)該在戰(zhàn)爭(zhēng)、制裁以及維和等國際事務(wù)中擁有更多決策權(quán)。
2005年,聯(lián)合國在成立60周年之際曾醞釀改革。時(shí)任聯(lián)合國秘書長(zhǎng)的科菲·安南表示,“日本有望在擴(kuò)大后的安理會(huì)中獲得常任理事國席位”給了日本希望,日本小泉政府迅速聯(lián)合德國、印度和巴西組成“四國聯(lián)盟”(簡(jiǎn)稱G4),試圖通過增加6個(gè)常任理事國(亞洲2個(gè)、非洲2個(gè)、中南美1個(gè)、西歐等1個(gè))和任期為2年的4個(gè)非常任理事國(亞洲、非洲、中南美、東歐各1個(gè))的方式改變現(xiàn)有聯(lián)合國安理會(huì)的結(jié)構(gòu)。但是,由于美國對(duì)日本的意愿“原則肯定,具體否定”,只給面子不給力,使小泉政府終未如愿。
10年后,小泉純一郎親手培養(yǎng)的弟子——安倍晉三再次躍躍欲試。在2013年底通過的2014年度預(yù)算案中,日本政府為“入常”設(shè)置了1.4億日元的“拉票”預(yù)算,以邀請(qǐng)64國的駐聯(lián)合國大使訪問日本,將“金權(quán)政治”玩到聯(lián)合國。
2014年7月底,日本、巴西、德國和印度四國在東京召開外務(wù)省局長(zhǎng)級(jí)磋商會(huì)議,就共同推進(jìn)聯(lián)合國安理會(huì)改革即增設(shè)常任理事國事項(xiàng)達(dá)成一致方針。8月初,在訪問巴西并與巴西總統(tǒng)羅塞夫進(jìn)行首腦會(huì)談時(shí),安倍提議借聯(lián)合國70周年之契機(jī),日巴兩國加強(qiáng)配合,推動(dòng)實(shí)施旨在擴(kuò)大聯(lián)合國安理會(huì)常任理事國的安理會(huì)改革。日本、巴西、德國和印度四國東京召開外務(wù)省局長(zhǎng)級(jí)磋商會(huì)議,就共同推進(jìn)聯(lián)合國安理會(huì)改革即增設(shè)常任理事國事項(xiàng)達(dá)成一致方針。
但是,安倍政府顯然忽略了一個(gè)基本事實(shí):聯(lián)合國是1945年9月在反法西斯的“聯(lián)合國家”的基礎(chǔ)上建立的。聯(lián)合國安全理事會(huì)的主要職責(zé),是在維護(hù)世界和平,促進(jìn)世界各國合作與交流方面發(fā)揮積極作用。日本是戰(zhàn)敗國,是同盟國之“敵國”——軸心國成員。雖然日本在1956年加入了聯(lián)合國,但被稱為“敵國條款”的聯(lián)合國憲章第53條、第77條、第107條,事實(shí)上使日本和其他成員國并不完全享有相同地位。對(duì)此,聯(lián)合國憲章第53條表述非常明確:“敵國系指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為本憲章任何簽字國之?dāng)硣浴!?/p>
已是2015年,但聯(lián)合國改革尚未有時(shí)間表,即便有,不僅日本的盟國美國的態(tài)度依然是個(gè)變量,而且要遭到制裁的俄羅斯不投日本反對(duì)票,近乎天方夜譚。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已非常明確。去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發(fā)言人明確表示:“任何聯(lián)合國會(huì)員國,包括希望在安理會(huì)發(fā)揮更大作用的國家,首先應(yīng)該尊重歷史,對(duì)歷史負(fù)責(zé),不能挑戰(zhàn)世界反法西斯戰(zhàn)爭(zhēng)的勝利成果。”基于一票否決制原則,此次日本“入常”的難度之大,可想而知。
(作者為復(fù)旦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日本研究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