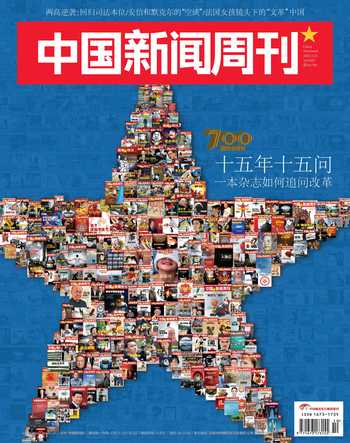一位法國女孩鏡頭下的“文革”中國
吳子茹
20歲的法國女孩索朗日·布朗剛沖出北京飯店,就迅速淹沒在人群里。她手里緊緊抓著相機,努力尋找最佳拍攝點。秋天的太陽明晃晃的,照得人頭頂發熱。寬闊筆直的長安街上,游行的人群情緒激昂。長安街兩側,每個能落腳的地方都擠滿了人。人們整齊列隊,高聲喊著口號。
1966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門。紀念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17周年。作為法國駐華大使館秘書,布朗和一群外賓一起受邀參觀慶典。從北京飯店的窗口望出去,廣場上的陣勢宏大莊嚴。這天也是毛澤東8月18日以來第4次接見全國而來的紅衛兵,超過150多萬學生、市民走上北京街頭游行慶祝。
天安門一側北池子路口的標志性門洞下,一群和布朗年齡相仿的中國學生席地而坐,正等待命令走上長安街。空氣中彌漫著焦急、熱烈的情緒,布朗舉起手里的相機,瞄準這群興奮的學生,按下快門。 一個戴眼鏡的年輕學生,很斯文的樣子,右手高舉一本紅色《毛主席語錄》,突然扭頭看向鏡頭這邊,表情略帶些許好奇。
布朗用鏡頭留下了那個年代無數中國人最真實的形象。時隔半個世紀,這一批照片再次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它們是官方影像外,少有的關于那個年代中國最樸素的影像記憶。
“五一”,1966拍下天安門國慶游行這一年,索朗日·布朗剛來到中國一年多。1964年,中法正式建立外交關系,法國成為少數與中國新政權建交的西方國家。第二年,正在學校學習秘書課程的布朗,得知法國招聘駐華使館秘書,她成功申請到這一職位。這年她剛滿19歲。
布朗的日常工作是協助使館人員辦理與中國相關的公務。但她不懂中文,很難直接與中國人交流。20出頭的年輕姑娘,性格外向開朗,對這座古老城市里的一切都充滿好奇,“尤其喜歡觀察大街上這些人,試著去理解他們。”多年后,她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
中國人大多親和、內向但充滿善意,這是布朗剛到北京不久的感受。她對這個陌生的民族充滿了興趣。這年“五一”勞動節慶典,作為駐華大使館工作人員,布朗和她的同事受邀參加慶祝活動。
這是一次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安排了一系列外賓參觀項目。地點在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里。一連串中國民族特色表演,有“大頭娃娃”舞、人體凌空翻轉的中國雜技、抖空竹、石杠鈴……布朗當然叫不出名字,但她興奮得連續按下手中的快門。
引起布朗興趣的是女孩子們的舞蹈。

北京,準備出發游行的紅衛兵隊伍。攝影/索朗日·布朗
十七八歲的女孩子,臉上涂紅紅的胭脂,人人腰間扎一根皮帶,英姿颯爽的樣子,手里端著木槍木刀一類的“武器”,隨著鏗鏘的音樂聲有節奏地來回刺。這和法國看到的舞蹈不一樣,但以一個外國人的視角看來,這一切都很好玩。就像北京古老的建筑一樣,這都被理解為“異域風情”。
表演者或旁觀者,人們或許都沒有意識到,此時已是山雨欲來。很快,一場席卷全國的“文化大革命”就將拉開序幕。在這場“革命”中,“大頭娃娃”舞將作為“四舊”被批判,而舞臺上這些舞刀弄槍的女孩男孩們,很快就會手持真刀真槍,沖上大街,沖進人們的家里。
這時的布朗沉浸在節日的氣氛中,偶爾有“打倒一切牛鬼蛇神”這樣的標語闖入她的取景框。但非常少。再過一段時間,滿大街都是更為激烈的標語和大字報了。它們作為背景元素反復出現在布朗的照片里。
拍照是布朗與外界溝通的方式。她喜歡攝影,曾用父親的老相機拍過一些照片,但并沒有經過什么專業的攝影培訓。一有機會上街,她就提著相機到處兜兜轉轉,看到有趣的東西就趕緊拍下來。拍人、或者拍景,至于具體拍什么、如何拍,全憑直覺。
相機是一臺賓得,是布朗用自己的薪水從香港買來的。她還購買了大量膠卷,興致勃勃地要記錄自己的中國見聞。這是第一臺屬于布朗日自己的相機。此后,這臺賓得相機留下了大約四百多張中國的照片。
布朗說,自己當時只是學著拍照片,都當做業余習作來拍,從沒想過要發表。但是,她承認自己“有一些天賦”。拍了一些照片后,布朗很快就知道了抓拍的重要。除了光線、構圖等,“抓拍的時機很重要。”
今年初,布朗的攝影集《中國記憶,1966》在中國出版,其中收錄了在“文革”期間拍攝的部分照片。但從技術角度看,多數照片并不成熟,但其中一些照片,拍攝時機的選擇的確讓人驚訝。
“十一”慶祝這天,布朗與一群外賓一起受邀參觀大典。從北京飯店的窗口望出去,大典宏大莊嚴的陣勢盡收眼底。布朗連按快門,拍下了幾張大典開始前的天安門全貌。照片里,遠方電報大樓的時鐘看不清楚,

“徒步長征” 的青年學生。1967年冬,中國政府宣布停止“大串聯”,號召“就地鬧革命”。而因為運力不敷,青年學生們被鼓勵自行回到居住地,于是“徒步長征”成為此時的一道社會景觀。攝影/索朗日·布朗
但廣場上已經凈場,國徽方隊尚未啟程,游行還未開始。天安門城樓上旗幟飛揚,面向廣場的一方依稀已站滿了人。對面廣場的一角,寫著慶祝標語的氣球飄在空中。
“這幾張照片再一次說明,拍攝天安門廣場的重大政治事件,最好的角度就是老北京飯店的房間。”媒體人楊浪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開玩笑說。他為這本攝影集作了詳細釋圖,每張照片都細細考證了拍攝時間、地點和當時的時代背景。
一通講話之后,游行開始,布朗迅速溜到大街上,混入人群中,手拿相機拍下了大量照片。盡管構圖還有些稚嫩,但從照片里人們的反應看來,布朗很善于隱藏自己。“可以看出來這是一個很有天賦的攝影師,盡管當時還很業余。”楊浪這樣評價。
“竟然還有人這樣拍 ‘文革’ ”
“太吃驚了,竟然還有人這么拍’文革’!”楊浪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形容自己第一次看到這批照片的心情。作為一名歷史研究者,楊浪推崇從一些不被關注的角度恢復歷史真實。他熱衷于研究各地墓碑,還出版了一本《地圖的發現》,“這些東西都不被注意,里面藏著歷史的玄機。”
影像是歷史另一個有力的佐證。就算你怎么擺拍,有目的地構圖、用光,人的衣著、環境和時代大背景,是沒有辦法說謊的。
2014年4月,作為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紀念活動,大型攝影展“150年法國人鏡頭中的中國”在北京今日美術館開幕。楊浪跑去看展覽,一張張片子快速掃過去,其中大多數都由于各種機緣看到過,但看到幾張中國“文革”時期照片時,楊浪站住了。
這系列照片有六七張,出自一名叫索朗日·布朗的攝影師之手。從畫面看來,攝影者盡管也有一些攝影天賦,但顯然并不是一位攝影大家。從構圖、用光和畫面內容選取來看,照片大多數拍得隨意而自然,流露著天真爛漫的氣息。
這跟眼下能見到的“文革”照片,質量好一些的比如李振盛、翁乃強等人的東西,“都太不一樣了。”楊浪很興奮。
眼下能看到的“文革”照片,擺拍是主流。物資匱乏的年代,擁有相機的人多半是國家宣傳機構人員,拍攝人物和事件,有一套完整的宣傳要求。
索朗日·布朗的照片不屬于這一類。她不是新聞記者,只是一個相對業余的攝影愛好者,憑借興趣和熱情拍攝的。由于語言和文化的隔閡,她對拍攝的環境、語言等幾乎一無所知。發生在眼前的事情超乎想象。
“我只是憑著興趣去拍,盡量理解這些人、這些事。”索朗日·布朗這樣對《中國新聞周刊》回憶。幾百張照片以散漫、隨意的方式拍下來,卻構成了那個時代最真實的影像資料。
單從攝影本身和藝術價值來說,它們遠不及同在展覽之列的馬克·呂布、布列松等著名攝影大家的作品。但正是照片本身具備的史料價值讓人驚訝,“很少見到有人這樣拍文革。”楊浪評價。
展墻上的作者介紹顯示,索朗日·布朗是當時法國駐華大使館的一名年輕女秘書,業余攝影愛好者。19歲來到中國,拍攝這組照片時,索朗日·布朗才20出頭。 楊浪記住了這段介紹,他希望有機會能看到她更多的照片。
出版人、漢唐陽光總經理尚紅科有一次找楊浪聊天,問他最近有什么值得出版的好書。“趕快去關注一個叫索朗日·布朗的法國攝影師。”楊浪扔過去這句話。他馬上去找布朗談版權。布朗欣然答應在中國出版。不到一年時間,《中國記憶,1966》得以出版。
攝影集里收錄了幾張京津公路上拍攝的紅衛兵照片,讓人尤其記憶深刻。那些紅衛兵幾人一伙,扛著旗幟和毛澤東照片,舉著紅寶書,一路高歌。一張照片里,一輛運柴草的拖拉機經過,幾個人大概是扛得累了,把毛主席像放在車里的柴草上,護著它繼續往前走。另一張照片逆光抓拍了幾個紅衛兵的背影。夕陽下,他們各自背著被褥艱難前行。拉長的樹影和身影、北方冬日郊野蕭瑟的風景,讓他們的背影看上去有些落寞,盡管每人背后都掛著一張經典的毛主席照片。
這已是1967年初,一番熙熙攘攘的“大串聯”后,交通承受不住壓力,中央號召紅衛兵“步行串聯”。布朗去天津辦事,沿路總能看到這樣成群結隊的紅衛兵。
政治和日常生活
1967年,瘋狂在延續。
這年夏天,中國“極左”外交政策導致一系列問題。在國際社會陷入空前孤立的境地。如今提起“文革”外交,讓人記憶猶新的仍是“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
但少有人知道,這年年初,憤怒的北京民眾曾來到法國大使館抗議。中法建交五十年,這是唯一一次雙方沖突事件。布朗的照片記錄了這一事件。
1月底,六十多名赴歐留學生途經莫斯科返國,參加“文革”運動,在莫斯科紅場獻花圈、朗讀贊揚斯大林的“毛主席語錄”,與蘇聯軍警發生沖突。27日,巴黎部分留學生向蘇聯駐法國大使館抗議,途中遭到法國警方拘捕。
1月31日,北京群眾在法國大使館前示威游行。
2月1日到5日,一部分人包圍法國駐中國使館,進行抗議。
法國大使館門外,時時有群眾組織前來抗議。鐵門外擠滿了中國人,有大學生、也有市民模樣的人,人們拿著幾個高音喇叭,群情激奮地喊著口號。對面的布朗起初并不知道他們在喊什么。但很快就從使館外墻壁上的標語上明白了,“打倒法國帝國主義!”——黑色大字標語,配有相應的英文。布朗的鏡頭無數次不小心掃過宣傳欄上、墻上的大小標語,它們作為背景出現在她所有的照片里,她并不明白其中的意思。但這次,布朗第一次將鏡頭對準標語本身。
戴著紅領巾的小學生來了,隔著大使館鐵門,孩子們沖里面揮舞著拳頭。一張張天真的臉上寫滿了激昂。 一場雪后,幼兒園小朋友也來抗議了。在大人的帶領下,他們右手高高舉起,揮舞著拳頭,顯得可愛、稚嫩,又讓人啼笑皆非。遠遠地,布朗拍下了一張全景照。鐵門外的人已少了很多,抗議接近尾聲了。
1965至1968年,布朗在北京四年。官方身份讓她得以在那個瘋狂年代可以四處走動,并用相機記錄下很多瞬間。她甚至跟使館工作人員一起去江蘇南京、山西大同等地參觀。
與法國大使館抗議照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組拍攝民間生活的照片。“文革”時期,這樣的照片很難見到。
布朗的視角從北京古老的城門,到街角廢棄的商店,再到街頭的縫紉機,她的拍攝總體看上去有些漫不經心。鏡頭轉向南京和蘇州時,同樣是1967年,布朗竟然拍起了街頭悠閑的市井生活。除去偶爾闖進取景框里的毛主席語錄,照片里的人們衣著樸素,表情困苦,但看上去卻悠然自得。一個青年以閑散的姿勢出現街頭,這讓楊浪吃驚又興奮。“那應該是當時的’逍遙派’吧?”這張照片下,楊浪這樣解釋道。
“當時是看到什么有意思就去拍什么,沒有刻意去追逐 ‘政治符號’這些東西。”布朗對《中國新聞周刊》這樣回憶當時的拍攝初衷。
作為一名攝影者,她更感興趣的是大街上的人們。“看上去他們穿得并不好,吃得也不好,但個個臉上都很興奮。”布朗無法理解,她只能對路人報以善意的微笑,“盡量去理解他們。”
在南京,布朗拍攝了一位走街串巷賣餛飩的老人。懶洋洋的陽光照著街道,一個老漢,一擔餛飩挑,讓人忘記這是“文革”時的中國。在外國人布朗的眼里,這樣的場景和大街上揮舞的毛主席像、紅寶書不一樣,是另一種讓她覺得親切有趣的東西。
即便身在“大革命”時代,人們的生活還是要繼續。布朗拍攝的照片,讓人難得地窺見了那個時代的市井生活。
攝影評論家陳小波第一次看到布朗的照片時,表示這些照片從攝影的角度上來說,還夠不上他要求的水準。但越仔細研究照片里的細節,感受就越深刻。在一篇為《中國記憶,1966》所作的序里,陳小波這樣寫道:
“小索的圖片在說話,它告訴世界,發生在不久以前的關于中國的故事,它解開歷史不想說或者不能說的一些秘密場景——一個極端年代帶給中國人難以想象的困苦與荒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