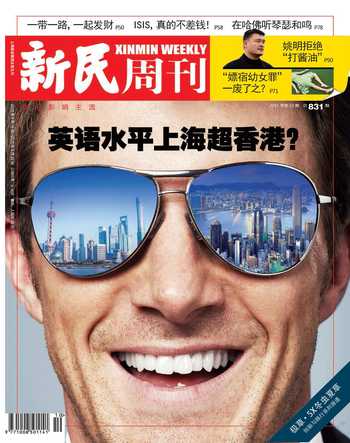何一沙:以靈性閱讀世界
趙子龍


何一沙陶瓷作品《少司命》。
我之所以被何一沙的作品吸引,是因?yàn)樗鼈兩l(fā)著某些我一直所追尋的信息。它們?nèi)缤话谚€匙,一束光,邀請我們在精神荒蠻化的時(shí)代里重新關(guān)注那些我們以為不重要的問題,幫助我們?nèi)ミ€原被肆意簡化的世界。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2011年何一沙創(chuàng)作的作品《破碎之后》——一批用陶瓷做的蛋殼,這些破碎的蛋殼表面描繪著鳳凰的紋樣。這是一件意味深長的作品,當(dāng)觀者面對這些蛋殼時(shí),不再像以往那樣帶著一種風(fēng)雅的心態(tài)去把玩花紋和釉質(zhì),而是一種敬畏感:我們不知道從這枚蛋中飛出的是怎樣巍然壯麗的生靈,不知道它去了哪里,但我們知道它就在這個(gè)世界的某處,在我們?nèi)庋鄣囊曈X之外。何一沙將“陶瓷”這種長久以來被我們視為“工藝”的藝術(shù)形式,轉(zhuǎn)換為一種帶有信仰意義的“圣物”——我們既可以從中讀到一系列關(guān)于“生命”的暗示:道家所說的“生生不息”,佛學(xué)所言的“生命輪回”,基督所言的“復(fù)活”;這些蛋殼如同基督留下的十字架和圣杯,瞬間就改變了整個(gè)世界的維度和邏輯,同時(shí)也檢驗(yàn)、喚醒了這個(gè)時(shí)代的人對精神世界的“靈性”。
何一沙是我所見真正在信仰層面而非文化層面上理解人類文明的藝術(shù)家。她自幼時(shí)起便接受中國古代文化的熏陶,小學(xué)高年級時(shí)又聽父親講述基督的故事,從一開始就將盤古開天、女媧造人等神話傳說與上帝七日創(chuàng)造世界的描述納入了同一個(gè)觀念體系。正因?yàn)槿绱耍覀冊谒淖髌分锌吹降氖前莸摹ⅹ?dú)立的、有性情的、有溫度的神圣感;以及對這個(gè)布滿是非冷暖的世界極大的善意。
日前,何一沙在成都寬窄巷子那個(gè)在全國文化界頗為出名的“白夜”舉辦個(gè)展,向我們展現(xiàn)了她一直用心創(chuàng)作的陶藝作品《九歌》以及一系列關(guān)于《楚辭》的水彩繪畫。在這些作品中,何一沙以裝置藝術(shù)的思維審視“陶瓷”這一古老符號,將其視為一種包括了中國古代“五行”觀念的材質(zhì),萃取出更為復(fù)雜的思想,這本身是對“陶藝”在觀念上的推進(jìn)。傳統(tǒng)陶藝之所以難以進(jìn)入當(dāng)代,是因?yàn)槭冀K無法突破陶瓷的固有概念;當(dāng)陶瓷固化為一種“精湛技藝”的時(shí)候,其原本具有象征意義的觀念密度被大幅削減,最終由形而上的“造物”淪落為到世俗玩味的用具。何一沙以一種儀式化的方式對此作出了改變,比如在《山鬼》中,她巧妙利用了陶與瓷不同的材料質(zhì)感,使二者建立了前所未有的關(guān)系:同出于大地,陶有山川之蒼茫,而瓷有生靈之圣潔。同時(shí),無論陶瓷,均不過分具備細(xì)節(jié)而僅存意象,以陶瓷貫通了中國水墨的氣質(zhì),形制雖小而有泱泱大氣,仿佛溝壑間有大風(fēng)來往。此外,這種立體擺放讓人想起源自上古的“禮”——那些借助日常之物模擬宇宙秩序的儀式,諸如“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太牢之禮”、“以四神守四方”等等,將現(xiàn)代藝術(shù)中的裝置藝術(shù)概念與之進(jìn)行了碰撞和融合。
從《破碎之后》到此次的《九歌》,我能夠感受到何一沙為她自己所建的世界里,始終有一種喜悅感,這種喜悅并非是一種簡單的情緒,而是一種生命與造物主重新建立關(guān)聯(lián)之后的幸福、欣慰、安心。曾幾何時(shí),《九歌》被認(rèn)為“悲歌”用來承載流放遠(yuǎn)方的悲苦,而何一沙將這種“憂傷”轉(zhuǎn)化為“其身仍在天地中”的自足,將孤獨(dú)的苦悶闡釋為與神靈相遇相處的坦然。從她描繪“山鬼”、“司命”那種清新、艷麗的色彩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她筆下的神靈神秘但不可怖,而是在高貴大氣之余帶有自由、善良的氣息,神性與人性交融,而這也暗合著基督思想中的“人神和解”。如果說一個(gè)人究其一生的修養(yǎng)是為了確立個(gè)體與世界、生命與宇宙的關(guān)系,那么何一沙已經(jīng)慢慢朝向了令自己信服的答案,而這正是她所從事的藝術(shù)對于我們這些觀者的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