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土挽歌、都市“浮世繪”與遼闊的美意
曹霞
從2014年的發展狀況來看,可以說文學正在走向一個多元共生、差異同存的時代。盡管生活依然喧囂、浮華、躁動,但作家們卻能夠與之保持一定距離,致力于對中國問題的思考,對時代和社會的觀察,并將之與個人的生存體驗、美學經驗和藝術想象相融合,創作出了既涵括鄉土挽歌、歷史敘事與當下現實,又不乏深刻的精神追問和雋永美意的作品。
從近年的創作來看,隨著城市文明的日益成熟和鄉土社會的巨大變遷,曾經在中國20世紀文學中占據重要地位的鄉土文學的身影正在逐漸淡出。這不僅指此類題材在數量上的急劇減少,而且是指相當擅長鄉土敘事的作家面臨潰敗的鄉村時,他們的經驗在流失、在失效,“鄉村烏托邦”化作了無盡的悲吟和挽歌。
賈平凹的長篇小說《老生》以唱喪歌的歌師見證記錄了陜南鄉村百年來的歷史、人倫和風土變化。歌師這一通人世神冥的職業為小說增添了深邃黑暗的密度,《山海經》的嵌入則與百年鄉村的發展互相映現,繚繞成了古老大地上的悲歌。關仁山的《日頭》是其“中國農民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小說以十二律為結構,以敲鐘人老軫頭的視角和家庭命運的變化,展開日頭村金家、權家子孫圍繞土地和礦產資源的斗爭,輔之以魁星閣建設之曲折和毛嘎子對苦難人生的俯視,交織成悲涼哀婉又不乏宿命感的鄉土挽歌。孫惠芬的《后上塘書》、肖江虹的《懸棺》關注鄉土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衰敗,生活在鄉村和峭壁上的人們被迫搬離,身體與靈魂永遠無法回歸故里。它們所展現的微觀史,正是當下中國鄉村共同面臨的被“現代”、被污染、被損毀和被掠奪的共同命運。
與鄉土題材緊密聯系的還有農民工或其子女進城后的生存問題、教育問題、留守問題等,這也是中國城鎮化進程必然產生的重重矛盾。陳應松的《喊樹》中,城里兒子的結婚需求毀滅了樹的生命,伐樹的老父親患上喉疾,如遭天譴,因為治病的藥就在老樹上。艾瑪的《遠大的前程》塑造了一個受盡生活折磨、在兒子進城后孤獨無助的母親形象,宗利華的《目光穿透荒原》中,村民都進城了,村莊變成了荒原。余一鳴的《種桃種李種春風》和季棟梁的《教育詩》以農民工子女入學難為題材。這是城市生活對照下的“鄉土挽歌”。作家在關注農民工問題時,也揭開了諸多社會潛規則的痛楚與隱患。
作為文學創作的重要題材,“歷史”仍然占據了相當分量,作家的講述和推演帶有強烈的性別視野與個人色彩。嚴歌苓的《媽閣是座城》、張翎的《陣痛》、池莉的《愛恨情仇》、萬方的《女人梨香》在跨度廣闊的時代背景下講述女性的悲情故事與孤絕命運。葉兆言的《很久以來》和葉彌的《風流圖卷》通過女主人公的成長和愛情展現“文革”,意在為那些消失的人立碑畫像,以人性的豐盈對抗“革命”的變幻莫測。同樣是寫“文革”,王松的新知青小說《天眼》描寫黃天病以未卜先知的天眼異能進行詐騙,鋃鐺入獄。“歷史”在這里更多遵循的是人性之惡而非理性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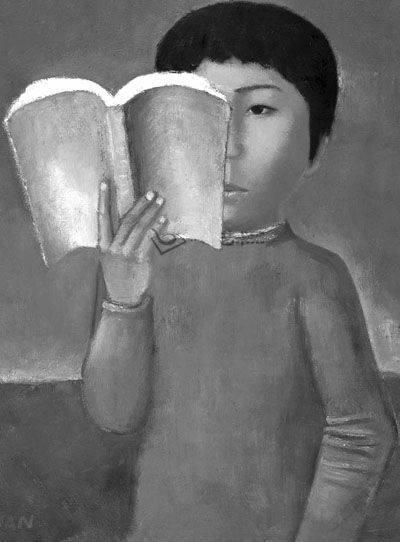
即使是寫“非常”年代,寫抗日戰爭,作家表現出來的也不是單向度的批判傾向,而是更為復雜的關于人和時代的思考。馬金蓮的《口喚》以大饑荒時代為背景,饑餓的記憶、溫暖的拯救、虔誠的感恩與艱難時世中的情誼共同留存下來。王秀梅的《虛構的卷宗》從父親的血統寫起。祖母去日本軍隊尋找丈夫,被日本人強奸,懷上身孕。作家以現代敘事的多角度多時空交錯展現那段充滿屈辱、血腥和濃烈愛恨的歷史,以及“英雄”后代對家族歷史的復雜心態。走走的《失蹤》以“尋找”為主題,通過林森尋找儲安平的故事,呈現出精神的扭曲、政治的變幻和人性的“變形記”。
值得注意的是,70后、80后都對歷史題材有所關注。他們將自己的成長與并不遙遠的過去相聯系——徐則臣的《耶路撒冷》、路內的《天使墜落在哪里》、呂魁的《把那個故事再講一遍》將少年的成長史與鄧小平南巡、金融危機、“非典”等事件相融合,既是中國30年多來的“發展史”,也是“一個人的編年史”。笛安以明朝萬歷年為背景創作了《南方有令秧》。小說的價值觀念、人物衣飾均有史實真實性,語言、敘述和人物性情又保持著作家的個人色彩。這表明,一向被垢病為缺乏“歷史意識”的作家們有能力講述歷史,并且逐漸形成了屬于一代人的歷史敘事風格。
與鄉土敘事和歷史敘事形成空間與時間對照的,是作家對當下新經驗的處理,對都市世情倫理、浮生萬象的書寫。劉心武的《飄窗》以巧妙又頗具現代感的視角觀察都市生活,通過對黑社會老大、保鏢、小姐、知識分子、“革命者”、上訪者等眾生的描述,以及對高貴/卑賤、情感/權欲、無知/知識等多重故事的疊合編結,刻畫出一個繁華表層下涌動著復雜關系和萬千氣象的“小江湖”。
城市的生存壓力和孤獨體驗為作家提供了豐富的題材,能否看到這些,提取出它們的悖謬性與殘酷性,取決于一個作家是否有能力有勇氣對現實發言。寧肯的《三個三重奏》中,酒廠老板的隱匿與逃亡、高官的被審訊都有著強烈的現實對映。方方《惟妙惟肖的愛情》的主線是“讀書永樂派”和“讀書臭屁派”的“戰爭”,陳應松《跳橋記》敘述公胡子在下崗之后遭遇到財物被騙、與妻子離婚等不幸事件,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的主人公一心留在城市努力營生,只想活得有點人樣,最后卻獲罪入獄,田耳的《鴿子血》通過“處女膜”事件涉及少女被迫賣淫的故事,王十月的《人罪》和阿丁的《死黨》以夏俊峰事件為藍本,在小販和城管的對峙以及罪惡/贖罪的轉換中揭開了城市生活的陰郁與苦難。
在情愛敘事方面,城市猶如打開的潘多拉的盒子,有著欲望、金錢、交易與權勢的多重博弈。鄧一光的《深圳藍》、尤鳳偉的《鴨舌帽》、喬葉的《鱸魚的理由》、孫頻的《海棠之夜》、黃詠梅的《走甜》、哲貴的《契約》、吳君的《天鵝堡》、鄭小驢的《贊美詩》等展現了種種情感形態:恩愛的假夫妻、分居兩地的真愛人、揭開乏味婚姻真相的女性、已婚男女的小曖昧、財富誘惑下的婚姻與出軌。諸如此類,直接指向現代人在感情與生存之間的游移和迷失。
作家們并沒有停滯于對城市外部事件的描述,而是深入到現代人的生活肌理,企望通過對“病理”的分析及其釀就的意外事件展現城市的孤獨、陌生與隔離。盛可以《彌留之際》中的劉一心患上飛蚊癥,這讓主人公可以理直氣壯地打別人耳光,張學東《藥食者》中的主人公對藥的依賴危及家庭和婚姻。弋舟的《所有路的盡頭》中,由理想時代逶迤而來的精神重負轉嫁到“弱陽性男人”邢志平的身上,先是弄壞了他的肺,接著弄漏了他的胃,最后干脆向他的乳房下手了。別人都以為他是因為患乳腺癌自殺的,實則是這個男人在深入骨髓的內省和孤獨中毀滅了自己。
不止是要展現“病理”,還要剖析并追問“病灶”自何而來,又有何種精神可以與之對抗。劉醒龍的《蟠虺》講述了對曾侯乙尊盤的尋寶、奪寶和還寶過程,勾連出既有正義也有邪惡的知識分子群像、為名利驅使的官場生態和盜亦有道的民間倫理,“青銅重器只與君子相伴”。人性之高貴終將戰勝貪婪,化解痛苦與無望。古老淳樸的人倫親情和人性的暖意同樣可以抵御艱難世事。畢飛宇的《虛擬》以中學校長的隱痛貫穿文本,那份虛擬的輝煌的奔喪名單化解了父子之間的芥蒂。張楚的《野象小姐》中,在病房工作的護工野象小姐也很不幸,她有個腦癱兒、收入不穩定,卻將生活過得有情有義、熱氣騰騰。葉廣芩的《太陽宮》、蔣一談的《在酒樓上》、文珍的《普通青年宋笑在大雨天決定去死》、張忌的《素人》、舊海棠的《萬家燈火》等通過“浮世繪”的刻畫,既讓我們看到了都市光鮮外表下的痛楚與悲劇,也為我們提供了拯救與精神生活的可能。
作家們對于敘事革新依然抱有強烈的熱情,“寓言性”成為作家表達的有效方式,因其豐富內涵可以概括我們時代的希翼與“病癥”。葉彌的《有一種人生叫與世隔絕》、蔡東的《我們的塔希提》均有理想生活的象征物,對應著現代人的精神困境。魯敏《萬有引力》的故事有著“多米諾骨牌”效應,羅偉章的《門票》由元敘事結構起雙重鏡像,朱山坡的《王孝廉的第六種死法》充滿博爾赫斯式的玄秘氣息,表明作家們在提取時代的故事元素時,并未放棄文學形式的實驗。
除了傳統文學期刊上發表的文學作品外,網絡文學發展至今已擁有了巨大的市場。2014年7月11日到12日,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聯合人民日報社文藝部、光明日報社文藝部共同舉辦“全國網絡文學理論研討會”,《人民文學》等期刊也設置專欄發表網絡文學作品。這表明時代再也無法忽略網絡文學的影響。如何樹立網絡文學的批評標準和價值評價體系、網絡文學和傳統文學如何互相汲取營養、如何使網絡文學成為中國文化軟實力與原創力的有效內容等成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對于詩歌來說,2014年引發最大反響的事件當屬魯迅文學獎。周嘯天的古體詩詞選《將進酒》獲得詩歌獎,某些詩句在網上流傳,被指如“打油詩”,創作水平遭到質疑,連帶評委和獎項的程序、水平和真實性都受到批評。不過,從詩歌創作狀況來看,這一事件只是在網絡和媒體上持續發酵,并未對詩歌界產生重要影響。
活躍在詩歌寫作前沿的有成名已久的老詩人,也有近年引發關注的中青年詩人。他們從日常經驗里提取詩的元素,執著于詩歌語言的創新和意象的美學凝練。西川的《潘家園舊貨市場玄思錄》《醒在南京》加入了粗糙的“非詩”,形成了龐雜混沌的詩風。臧棣發表了“叢書”和“協會”系列短詩,組詩《潛水史和預防針》以智性的語言關注生活細節,使之具有了抽象意味。對于內心的書寫和公共生活的觀察使詩歌更具廣闊氣象。朵漁的詩歌《綠天使》《聽巴赫,突然下起了雨》《這世界怎么了》彰顯了他一以貫之的內心的傾聽與追問。侯馬的《存在》《有一個人他自己還記不記得他是誰》保留了犀利與深邃,并融入了對個體存在感、集體無意識和意識形態的書寫。安琪的《相約》、沈浩波的《月圓之夜》、路也的《城南哀歌》、江非的《每年的這一天》、杜涯的《第二年》在對生命流程、內心景致與世間“異象”的描述里展開了詩人豐富敏銳的感受。
在詩人筆下,世間萬物的存在都打上了主體心靈的印記。在事物與詞語的回聲中,靜默如謎的“物”綻開著神性的召喚與光芒。于堅的《域外集》、呂德安的《在埃及》、藍藍的《希臘變奏曲》以世界各地的游歷或經驗為主題,將域外的風物、景致、境遇內化為對自我與生命存在的本真思考,柏樺的《瘋狂的石榴樹》有著迷幻神奇的一面,吉狄馬加的《我,雪豹……》以雪豹的孤獨堅忍連結起了人類的精神與情感。李輕松的《萬物生》、娜夜的《傾聽之手》、燈燈的《向低音致敬》、馬新朝的《中原詩志》和寒煙、葉麗雋、杜綠綠、楊慶祥、楊方等人的詩呈現出現實生活場景與個人心靈和命運之間的契合,用語言、敏銳與想象道出了我們時代的“秘密”。
從詩歌出版物來看,有楊煉匯集了代表作、新作和譯詩的《饕餮之問》、王家新集合了譯詩精華的《帶著來自塔露薩的書》、商震的首部詩集《無序排隊》。陳先發的《黑池壩筆記》“難以歸類”,是詩人近20年來涉及詩學、哲學、語言學的“詩歌語錄”。湘籍廣東詩人東蕩子去世后,余叢編有《東蕩子的詩》,使人們再一次看到詩人的理想主義情懷以及對光明和真相的呈現。10月31日凌晨,陳超自殺,震動文壇,他的詩歌和詩學論著再次受到人們關注。也許對于一位詩人來說,詩作就是他留給世界最好的憶念。
長江詩歌出版中心自2012年成立以來,已成為重要的詩歌出版機構,2014年出版了《中國新詩百年大典》、榮榮《時間之傷》、李少君《自然集》、余怒《主與客》、陳陟云《月光下海浪的火焰》、大解《個人史》等詩集。北岳文藝出版社的“天星詩庫”主打“60后”“70后”實力派詩人的詩作。2014年出版有雷平陽的《出云南記》、呂約的《回到呼吸》、軒轅軾軻的《在人間觀雨》。詩人們寫故土情熱、性別經驗、時代之痛,他們從自己的生活中捕捉現實物象和日常細節美感,使詩歌成為我們重返生命源頭與體驗生存艱辛和秘密的重要路徑。
“第五屆在場主義散文獎”于2014年6月18日在海口舉行,獎項所提倡的“精神性、介入性、當下性、發現性、自由性”如今已經得到深入和確立。從2014年度散文的發表狀況來看,作家更關注自己生活的實有世界,他們將愛情與親情融入生活片斷,不斷觸及日漸蒙塵的靈魂。張承志的《海上的棋盤》、周曉楓的《海南,海南》、鮑爾吉·原野的《草的汗香》《在落下巴旦木花瓣的土地上》在“物”中寫出了生命的柔韌與廣闊,梁鴻的《云下吳鎮》以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展現小鎮的民間世相和生命形態,汗漫的《婦科病區,或一種藝術》寫愛人住院的經歷,有與死神交鋒的驚心動魄,也有樸素至深的感人力量。《黃河文學》開設“中國當代知名散文家新作展”專欄,刊發知名散文家與實力散文家的新作,發表了耿占春的《沙上的卜辭——來自噪聲的寫作》、周濤的《初雪·冬日陽光》、陳忠實的《神秘神圣的文學圣地》、陳世旭的《時間之上》等。它們涉及閱讀札記、人物印象、鄉村風物和城市體驗,以柔軟、包容和遼闊之美呈現出現代心靈的豐富和復雜。《天涯》的“70后:經驗與時代”“80后:經驗與時代”小輯收入了黃燈的《破碎的圖景:時代巨輪下的卑微敘事》、蔣藍的《箍桶匠的苦難美學》等文章,他們提供的是更具理性、經驗性和個人性的寫作。
從散文出版物來看,沈葦的《新疆詞典》(增訂版)用人文、歷史、地理、動植物等名詞重構一個“新疆”,既有超文本的文體實驗,又展現了獨特地域的詩意,《文學報》《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等選載過部分章節。陳丹燕的《我的旅行哲學》是“行走時代·陳丹燕旅行文學書系”的首發本,融合了旅行與文學之美。東方出版社的“當代散文名家叢書”出版了張煒《古鎮隨想》、筱敏《涉過忘川》、張銳鋒《復仇的講述》、龐培《生命呼吸》、黃一鸞《寄至何方》等。在這些作品中,作家們通過對鄉村印象、現實世界和城市生命體驗的書寫,敞開了隱秘豐富而具有思辨和精神色彩的心靈空間。
文學評論家孟繁華指出,鄉村文明正在潰敗,與此同時都市新文明正在“迅速崛起”。這也意味著當代作家將普遍面臨這樣的問題:如何深入當下現實,將鄉村現代性進程與都市生活轉化為敘事資源,寫出現代都市形態轉換和挪移過程中的生活的復雜性以及人性的微波細瀾?從目前的情況來看,作家們提供的城市經驗與形態雖然還未達至成熟成型,但相當多作家正著力于建構與城市生活同向、為宏偉巨變的時代譜畫肖像的創作路徑,這使當下文學創作充滿了面向未來的無限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