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關系的基本態勢及其問題
倪峰
2015年10月27日,美國拉森號軍艦未經中國政府允許,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中國外交部、國防部對美方提出了嚴正警告和抗議。這一事件發生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一個月后。令人不禁要問,美國為什么迅速變臉,為什么要挑起這場“危險的游戲”。
2015年9月習近平主席對美國進行的首次國事訪問,剛剛為中美關系發展注入了巨大的正能量。在雙方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同意繼續努力構建基于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系,在網絡安全和兩軍關系上實現新突破,在氣候變化、經貿、人文和反腐執法等領域擴大合作。訪問取得了重大成果,使得中美關系發展建立在一個更廣泛同時更堅實的基礎上。但與此同時,隨著中美之間“崛起大國”與“守成大國”范式的進一步凸顯,兩國關系中戰略競爭性要素并未減少,甚至呈現出上升的趨勢,尤其是在網絡安全和南海問題上。
從長期來看,中美兩國政府基本還是按照管控分歧、擴大合作的思路來處理這對復雜的雙邊關系。但面對各種矛盾和風險的不斷聚集,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之路仍任重道遠。
2015年以來
中美關系的發展軌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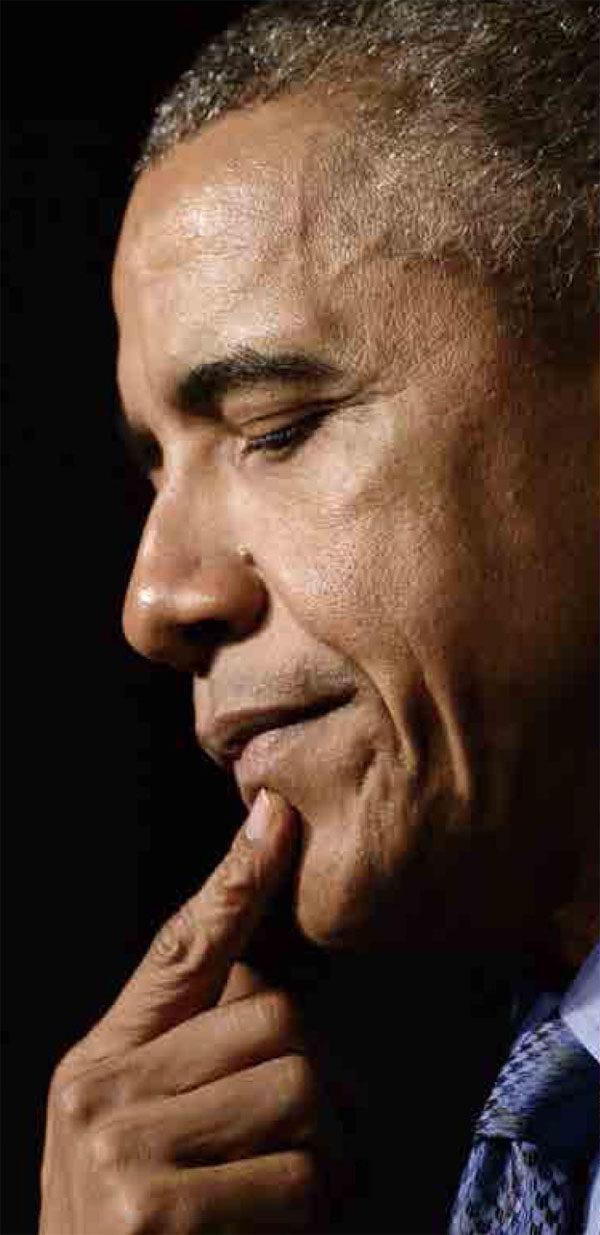
觀察2015年以來中美關系的演進,大致呈現出兩高兩低發展走勢:年初中美關系開局良好,3月至5月博弈的色彩明顯增加,6月以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為契機,兩國關系開始逐步導入高訪時間,9月下旬習近平主席對美的成功訪問為中美關系的穩定發展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10月份美方派軍艦闖入中國南海南沙島礁鄰近海域,又使中美關系掀起新一輪波瀾。
由于2014年底奧巴馬成功訪華,成果豐富,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共識就成為2015年中美關系開局的主題。兩國政府之間溝通交流頻繁,BIT(中美投資協定)談判繼續穩步推進,氣候變化領域合作繼續取得進展,兩軍交流繼續密集展開,尤其2月和4月兩國海軍在南海地區的聯演聯訓對于雙方管控分歧,防止在敏感區域發生擦槍走火具有重要意義。而反腐合作,正成為兩國關系中的新亮點。同時,兩國繼續在朝核、伊核、阿富汗、反恐、聯合國成立70周年系列紀念活動、2015年后發展議程、抗擊埃博拉疫情等問題上保持密切溝通協調。
對于兩國關系中長期存在的一些傳統結構性問題,雙方也沒有刻意糾纏。尤其是在達賴與奧巴馬會面的問題上,雙方都采取了低調處理的方式,使其在兩國關系中沒有激起大的波瀾。
更為重要的是,2015年2月10日,兩國元首在電話互致新春祝賀的時候,奧巴馬邀請習主席于同年9月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提前7個月就發出國事訪問的邀請,這在中美關系史上頗為少見。這表明,奧巴馬從2014年4、5月美對華政策管理失序的狀況中汲取了教訓,用提前宣布高訪的形式對中美關系實施戰略管理,從而也定下了2015年美國對華政策總體上要保持穩定的基調。
與此同時,兩國政府加強務實合作的努力,似乎并不能改變中美戰略競爭加劇的態勢。2015年3月12日,英國宣布申請加入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無意間再度拉開了中美間密集博弈的大幕。對于中國倡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盡管美國內部有不同意見,但奧巴馬政府認為,“中國正試圖在世界上發展最快的地區制定規則,這將使美國的工人和公司處于不利境地”。為此,對亞投行的成立多方阻撓。然而,英國的加入引發了美國盟友連鎖式反應,法、德、意、澳、韓紛紛跟進,美國的阻擾雪崩式潰敗。
2015年4月底,安倍訪美,美給予安倍最高禮遇的接待。雙方正式公布新版《美日防衛合作指針》,共同發表了聯合聲明。雖然聲明中并未點名道姓提及中國,但是字里行間明顯顯示出美日加強同盟的主要動因就是要共同應對中國對美日利益構成的挑戰,放日出山的意圖昭然若揭。在美日首腦聯合記者招待會上,奧巴馬公然指責中國在海洋問題上向鄰國“顯示肌肉”,并再次提及美日安保條約涵蓋釣魚島。
5月,南海問題急劇升溫。5月12日,美國官員表示,美軍正考慮動用飛機和艦船直接挑戰中國對一系列快速擴展的“人造島礁”的領土要求,美國國防部長卡特要求考慮的選項包括出動海軍偵察機飛越這些島礁上空,并派遣艦船駛入有關島礁12海里范圍內。5月22日,CNN播發了美國最先進的P-8A偵察機在中國南海人工島礁上空的錄像。南海問題再度成為中美關系的斗爭漩渦,在日美推動下,南海問題甚至成了G7峰會的議題。
幾乎是同時,“竊密”及“網絡”風波再度襲擾中美關系。5月16日,天津大學一名教授在赴美參加科技會議時被捕,美方稱,“將以商業間諜罪起訴六名中國人”。6月4日,美國官員透露,黑客通過一次大規模網絡攻擊入侵了美國人事管理局(OPM)的電腦,導致400萬現任和前任員工信息被盜。美方認為外國機構或政府可能是此次攻擊事件的幕后主使。12日,美國官員聲稱,與中國有關的黑客似乎進入了存有美國情報與軍事人員信息的機密數據庫。
隨著中美戰略博弈的加劇,尤其是美叫囂將派飛機、艦船進入南海有關島礁12海里領海、領空范圍,兩國間發生軍事碰撞的可能性急劇上升,中美關系由此極有可能被導入一種對抗模式。然而在此之后,中美關系并沒有演繹高臺跳水,甚至在5月底舉行的香格里拉對話會上,2014年雙方唇槍舌劍、“麥克風大戰”的一幕并沒有重現。此番爭議中,雙方把處理爭議的重心更多地放在暢通的溝通管道上。6月3日,奧巴馬在會見一個東南亞青年領袖訪問團時將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強硬立場緩和了下來,他稱:“或許他們(中國)的某些主權要求是合法的。”6月8日至12日,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一行訪美,中美兩軍簽署了陸軍交流機制,談及南海問題、臺灣問題以及“空中相遇”附件等內容。在南海問題上范長龍表示,“望遠能知風浪小,凌空始覺海波平”。南海問題只是中美關系中的一個插曲,中美雙方應登高望遠,關注更多重大的國際和地區問題。
6月23日,第七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和第六輪中美人文交流高層磋商在華盛頓舉行,取得的成果展示了中美關系的積極面和廣闊的合作面,以此為起點,確保習主席訪美成功成為兩國政府處理中美關系的首要工作。9月22日,習主席開始了增信釋疑、聚焦合作、面向人民、開創未來的訪美行程,先后到訪西雅圖、華盛頓,會晤美國總統奧巴馬,廣泛接觸美國社會各界,并發表一系列重要演講,取得了49項重大成果。在中美兩國實力不斷接近,摩擦點增多,一些人看淡、懷疑中美關系發展的前景之際,兩國最高領導人以實際行動和宏大倡議共同向中美兩國民眾和整個國際社會發出了兩國政府努力管控分歧、擴大合作,推動中美兩國相向而行的強烈信號。
當前中美關系
面臨的挑戰及問題
觀察2015年以來中美關系的演進,我們會明顯地感到,盡管兩國間的合作面遠遠大于競爭面,兩國政府都展現出穩定中美關系發展的強烈意愿,但兩國關系仍面臨一系列風險挑戰,管控分歧的任務越來越重,中美關系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美國軍艦拉森號非法進入中國南沙群島有關島礁鄰近海域一事就凸顯了中美之間增信釋疑、管控分歧任務之艱巨和多變。
首先,增強戰略互信依然任重道遠。戰略互信缺失是中美關系中長期存在的一個結構性問題。盡管雙方在增信釋疑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然而隨著兩國實力對比的不斷接近,美方的焦慮感仍在上升。
在金融危機前,美方對中國的擔憂主要基于中國作為一個大國的發展潛力。2009年之后,美國開始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已是現實,在2010年推出“重返亞洲”戰略,從中看出美國開始將擔憂聚焦在中國不斷增長的能力上。而自2014年亞信會議和中國倡導設立亞投行以來,美國在擔憂中國不斷增長的能力的同時,對中國的戰略意圖產生懷疑,即認為中國試圖將美國趕出亞洲,并挑戰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2015年以來,美國戰略界開始炒作所謂的“政治發展方向”問題。冷戰結束以來,歷屆美國政府都奉行以所謂“接觸”為主的對華政策,該政策一個重要前提假設就是,隨著中國經濟現代化,政治自由化也會隨之實現。然而,今天有越來越多的美國人認為,中國的發展方向是與此相反的。總之,對中國能力、意圖、發展方向三種疑慮的相互疊加,在美國國內產生了要求改變對華政策“范式”的呼聲。
第二,“對華政策大辯論”增加了美國對華政策的不確定性。2015年中美關系的演進面臨一個相當特殊的背景,即在美國內一場對華政策大辯論正在如火如荼地上演。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國內曾經歷過對華政策大辯論,一次發生在1995年到1996年間,當時中國經濟進入快車道,同時在1995年臺海危機爆發,遏制派和接觸派爭執激烈,最終接觸派的觀點占了上風,其基本立論是隨著中國融入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體系,中美在政治制度上的差異性會逐漸趨同。另一次是2005年,中國入世后在世界經濟中的分量迅速增加,而美國因深陷兩場戰爭而日益感到力不從心,對中國所謂“搭便車”的行為感到不滿,要求中國承擔更多責任,最終各派在要求中國成為“負責的利益攸關方”上達成共識。
盡管這兩場辯論在形式、內容甚至包括結論上都有所不同,但是有以下幾點是相同或相似的。首先,這兩場辯論都是在中美實力對比差距還較大的情況下進行的,美國在應對中國問題上還保持著相當大的自信。其次,盡管在辯論中存在著相當多的消極雜音,但最終得出的結論都是相對積極的。第三,美國的工商界在辯論中一直扮演著積極的、主導性的角色。
然而在此次辯論中,上述情景均發生了一些重要變化。首先,中美實力對比已經大幅接近,美對華所持有的信心早已被焦慮的情緒所取代。其次,美工商界仍對中美合作抱有期待,但隨著兩國經貿關系競爭性因素的增多,其熱情也已今不如昔。尤其值得關注的是,以商界為首、支持與中國交流的聯盟已不再是主導力量,而由其他一些界別組成的、倡議與中國競爭的聯盟似乎正在成為辯論的主導力量。第三,到目前為止在這場辯論中盡管存在著積極的聲音,但在美國戰略界有愈來愈多人呼吁當局“下定決心”、擔起“領袖”角色、實現“范式轉換”“敢于與中國抗衡”。盡管這場辯論可能要到明年的大選前后才能塵埃落定,但這些問題現在就需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因為這不僅會影響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更重要的是會對下任總統的對華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第三,在中美關系新的問題領域,雙方之間仍未找到有效的破解之道。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美實力對比的加速變化,中美關系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其中一個突出的特征就是兩國間戰略競爭加劇,具體表現是在中美間傳統四大結構性矛盾(戰略互疑、臺灣問題、經貿摩擦、人權問題)之外又出現了一些新的問題領域,如海上爭端、網絡安全等,其中中美鄰海上爭端最為突出。
中美鄰海上爭端是在美國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的大背景下凸顯出來的,其中最突出的當屬釣魚島問題和南海問題。
釣魚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被日本非法占有。二戰后,釣魚島及附屬島嶼(以下簡稱釣魚島)本應在雅爾塔體制下歸還中國。但因冷戰需要在美國單方面主導的舊金山體制下形成釣魚島爭端。對這一爭議,美國長期保持沉默,不愿意得罪中日任何一方。然而,2010年9月釣魚島“撞船事件”發生后,包括希拉里在內的美國官員公然聲稱釣魚島適用于《日美安保條約》。2012年以來,日本右翼分子和野田政府上演購島鬧劇,致使中日關系再度緊繃。就在這一敏感時刻,美國的立場和行動不斷向日方傾斜,致使中日矛盾不斷升級。
南海問題本是南海周邊國家圍繞相關島礁歸屬以及海域劃分存在的分歧和爭端。過去的美國歷屆政府都在這個問題上持不介入態度。2010年7月,希拉里在東盟地區論壇上突然聲稱:“在南海自由航行、亞洲海上事務保持開放狀態、在南海地區尊重國際法,這些關乎美國利益。”美國正式介入南海問題。在美國的撐腰打氣下,一些聲索國氣焰升高,在此問題上采取了一些更具挑釁性的行動,南海地區波詭云譎。
隨著美國介入的不斷加深,東海、南海熱點同步共振,中國與周邊國家民族主義情緒升溫,中美戰略競爭和對抗明顯上升,戰略博弈從局部轉向全局、從言論轉向行動、從心理較勁轉向外交爭奪。
美國的亞太戰略本意是利用小國投棋布子,減輕國內軍費開支縮減的壓力,通過整合同盟體系,“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收益”。但該戰略也被小國利用實施大國平衡。有的國家有恃無恐,借助“中國威脅”提高對美要價,在熱點問題上更加強硬,美國被盟友利益綁架。第三方因素對中美關系的掣肘,使中美在亞太地區陷入了一個惡性博弈的怪圈。
尤其是在最近這些年,南海問題間歇爆發,對中美關系的沖擊越來越大,就在習主席訪美后不久,美國媒體放出話來,美軍計劃近期在中國南海人工島礁12海里巡航,繼而成為既成事實。南海問題再度引發關注。在某種程度上南海問題已取代臺灣問題成為中美發生軍事沖撞的主要誘因。
第四,中美關系是否已演變為“秩序之爭”?2014年上海亞信會議和2015年亞投行出現以來,有關“世界秩序之爭”已成為中美關系中的重要話題,而且越來越熱。一些西方人士斷言,中美關于國際秩序之爭將成為新世紀地緣政治的首要紛爭。
誠然,中美關系已被描繪為“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的關系,然而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新”就在于要打破“崛起國與守成國必然沖突”的歷史魔咒。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本身的發展表明中國并非現有國際秩序的破壞者,而是建設者、參與者、改革者。誠然,由于角色和身份的差異,中美之間對一些相關問題的認知有不同理解,這些不同理解需要溝通、協調、磨合,甚至發生爭執,但這并不意味著雙方之間必然走上秩序之爭的道路。事實上,這些認知差異也不是當前有關世界秩序方面的核心問題。
目前在世界秩序領域面臨的核心問題是世界正在走向失序。無論政治領域還是金融領域,國際合作都在下降。自從冷戰結束后,聯合國從未解決過任何重大沖突;2009年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只留下酸澀的爭議;世界貿易組織自1994年以來從沒在重大貿易談判中達成一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治理方式嚴重過時,因而其合法性越來越多地受到質疑;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脫穎而出的二十國集團,本有潛力成為國際合作的強大機制,如今似乎已迷失了方向。在各個方面,國家、宗派、商業和其他特殊利益都凌駕于共同利益之上。由于全球化影響和技術擴散等原因,傳統的“大規模正規戰爭”和“小規模非正規戰爭”正逐步演變成一種戰爭界限更加模糊、作戰樣式更趨融合的混合戰爭。武裝沖突數量激增,影響范圍從中東蔓延到亞洲其他地區、非洲甚至歐洲。而在這一點上恰恰是中美作為兩個舉足輕重的大國需要共同面對、相互配合的。2014年底,中美在氣候問題上取得的突破,使全球控制氣候變化的努力看到了希望。如果這種方法能復制到其他領域,全球治理就有可能展現與現在完全不同的情景。
總之,中美關系是否已演變為“秩序之爭”仍是一個開放的問題,最終的結局取決于中美雙方在未來的歲月中如何互動。在這個問題上不宜過早做出結論。從理論上講,主要大國力量對比的變化尤其是力量對比的反轉必然會導致世界秩序的變化。然而在歷史的演進中,這兩者之間往往并不是同步發生的,秩序的變化往往滯后于力量對比的變化,而且有時來得相當的緩慢。例如,早在19世紀90年代,美國經濟總量就超過當時的霸主英國,但是確立起以美國為主導的世界秩序則是在50多年之后,而且在這期間幾乎所有順風順水的事情都讓美國趕上了。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美國起初都是置身事外,其本土又遠離戰場,同時與前霸主是血緣上的近親,又是密切的盟友等等。因此,面對這樣一個問題,我們應當保持足夠的戰略耐心和戰略定力,經略致遠,不被一時的炒作所迷惑,持久而又審慎地推進自身的利益,同時爭取為世界的和平和繁榮做出更大的貢獻。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
(責任編輯:徐海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