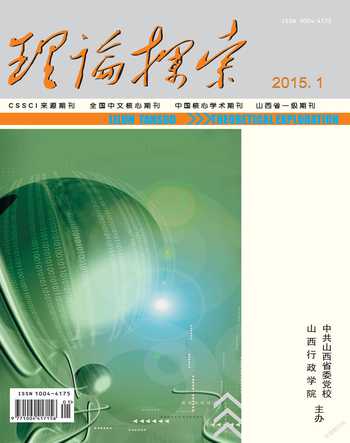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合法性回應
〔摘要〕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我們黨適應世情、國情和黨情變化而提出的一個重大戰略,我們黨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命題,歸根結底就是要回應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夯實并豐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具體來說,主要有三重維度,即制度合理性問題、社會焦點問題及發展的應然性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分別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回應的根本保障、現實基礎及不竭動力。從根本上來說,要消解人治障礙,建設法治中國。
〔關鍵詞〕 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回應,法治中國
〔中圖分類號〕D6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5)01-0080-05
〔收稿日期〕 2014-12-09
〔基金項目〕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環保類社會政治沖突化解機制研究”(13CZZ031),北京市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北京市社會沖突事件發展趨勢及對策研究”(13KDC022),負責人胡銳軍。
〔作者簡介〕 胡銳軍(1975-),男,江西高安人,國家教育行政學院社會科學教研部副教授、碩士生導師、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學理論、傳統政治文化、當代中國政府與政治。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將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確定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又專門研究依法治國問題,明確指出依法治國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這是我們黨第一次提出國家治理現代化這一重大命題,并將法治作為其推進和實現的根本路徑和手段。這既是我們黨執政六十多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三十多年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升華,也是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綱領、新理念、新主張和新任務,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我們黨之所以要提出這樣的命題,歸根結底就是要回應執政的合法性問題,夯實并豐富執政的合法性基礎。合法性指一國公民對執政者的政治統治及其政治制度的認同、服從和忠誠態度。政治合法性是任何執政者都必須時刻面對和解決的問題,一個社會要想保持長治久安就必須從人民那里獲得足夠的合法性資源,樹立起足夠的執政或政治權威。從我國的實踐看,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要從以下幾方面進行合法性回應。
一、解決執政的適應性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回應的基本前提
如果我們用前三十年、后三十年、再三十年來描述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和改革開放的歷程,那么其對應的執政方式和執政理念經歷了或正在經歷一個從方式到理念不斷提升的過程,最終走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目標,反映了我們黨對執政方式的時代調適和對政治合法資源變遷的現實回應。從歷史發展的經驗看,在不同歷史階段和不同社會形態,統治者對合法性資源的依賴程度是不一樣的,如傳統社會主要靠君權神授、血緣認同、習慣和習俗,現代社會則更加依靠制度、法律等,而革命則是任何時代都管用的合法性資源,因為無論從法理還是客觀上講,誰打下的江山誰無疑就應該名正言順的坐擁天下,通俗的講就是“打天下、坐江山”,所以革命是最具有說服力的合法性資源。但革命這個資源不能一勞永逸,換言之就是不能管著好幾代,統治者不能在政權交接或延續幾代甚至好幾代之后,還依然打著革命的旗號去說服民眾,其根本要義在于,不論天下是誰打的,都是人民的,而且打天下的過程中人民群眾是主要的力量源泉,新政權的建立只不過是人民群眾把原來委任的權力收回重新委托給新的信任者的過程,如果新的執政者不能在新的社會建設中逐漸改善民生、給人民帶來福祉,最終兌現對人民的承諾,或者隨著社會的推演而逐漸腐化墮落甚至蛻變為與過去統治者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腐朽集團,人民就同樣可以像以往一樣,通過一定的方式把權力收回,這無論從馬克思主義的人民主權說還是從西方的社會契約說都能得到最有力的證明。所以無論是毛澤東、鄧小平還是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都強調“黨的執政地位不是與生俱來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 。也正是因為此,在我們黨提的四大考驗、四大危險中,執政都是首位的。
我們看到,經過六十多年的建設尤其是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的經濟取得了飛速的發展,人們的生活得到了顯著的改善,但我們也應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些成就主要是通過GDP增長實現的,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建設的常態化性征凸顯,這種發展模式也暴露出一定的問題。一是消耗了一部分人的利益。我們知道,革命的一個最基本要求和精神就是“為國獻身”、“舍小家為大家”,這種精神是革命取得勝利的根本保證,可是如果在建設年代還以革命的模式主導和支配人們的生活,就顯然違背了革命的本義和初衷,因為革命的吃苦是為了人民的幸福。新中國成立后,雖然我們黨一直將國家的飛速發展、改善民生和社會穩定作為執政的第一要義,但由于一段時期沿襲了革命的觀念和模式,過于強調了革命的公益性、強制性、奉獻性和高積累性,一些地方政府就常常可以以“國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名義侵占甚或剝奪人們的利益而不用負任何責任,部分利益集團也常常會打著“公家”的幌子攫取民利并顯得天經地義,久而久之民眾的利益就會慢慢地被“充公”或“貢獻”。比如,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的確調動了許多人致富的積極性,創造出大量的財富。但由于制度約束不夠,隱藏的負面結果就是以犧牲一部分人的利益為代價。二是公權力過度介入和主導的改革,體現的治理模式必然是運動式治理,而這種治理的一個顯著特征就是試錯不斷、動員頻繁。當前,我們已經進入改革開放的深水區,各種問題叢生,改革的難度和阻力前所未有,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說法,就是“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硬骨頭”。不得不承認,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與我們的執政模式調適不及時是息息相關的。顯然,面對這樣的局勢,如果我們還沿襲以往的執政方式和理念,很難再贏得人民群眾的認同,所以,我們的治國理政方式應該向治理轉變,要還權還政于民,給人民更多的民主,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如何回應執政的合法性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第一要義。具體來說要回應以下三個問題:歷史使命性、社會現實性及發展應然性。
二、解決制度合理性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回應的根本保障
我們黨自成立以來就一直在為實現中華民族的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國家的繁榮昌盛和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求索,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經過九十多年的艱苦奮斗,這一使命已經轉換并具體化為兩大任務:一是實現中國夢,建成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是我們的終極理想;二是實現兩個“一百年”目標,即在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年時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在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這是我們的近期目標。這個偉大的歷史使命,正是回應人民的合法性期待,即圓人民真正當家作主的夢想,讓人民真正以主人翁的姿態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而達到這一目標的核心是需要有一套更加完備的制度。因為,“人類的相互交往,包括經濟生活中的相互交往,都依賴于某種信任。信任以一種秩序為基礎。而要維護這種秩序,就要依靠各種禁止不可預見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的規則。我們稱這些規則為‘制度’” 〔1 〕 (P3 )。可見,建構更科學合理的制度體系,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義和營造合法性資源的基本舉措。同時,這一舉動又不是另起爐灶、另走他途,而是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之內進行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使國家治理的制度體系更加完備、更加穩定、更加管用。
現在,新中國已經走過了65年的歷程,從歷史的經驗看,我們正處在一個興衰的關節點上。一方面,我們正處在國家繁榮的興盛點。縱觀人類歷史,世界各國政治制度的鞏固和興盛通常在60年左右,如,英國從1640年發生資產階級革命到1688年“光榮革命”形成君主立憲制,用了49年時間;法國從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獄到1848年二月革命成功,資產階級政權完全獲得鞏固,用了59年時間,到1870年第二帝國消亡、第三共和國成立,則用了80多年;美國從1775年獨立戰爭到1848年贏得美墨戰爭獲得在美洲的主宰地位,用了72年,而至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新體制趨于穩定則用了將近90年時間。從我國歷史看,西漢時期,從公元前206年漢高祖劉邦登基到公元前140年漢武帝劉徹即位,開創西漢王朝最鼎盛繁榮的時期,用了66年時間;在唐朝,從618年唐高祖李淵登基到684年武則天臨朝,創造唐中期的繁榮,也用了66年時間;在宋朝,從960年宋太祖趙匡胤建立宋朝到1023年宋仁宗趙禎即位,實現宋朝的新政和大發展,用了63年時間;在元朝,從1206年元太祖成吉思汗建國到1260年忽必烈正式定國號為元,用了58年時間;明朝時期,從1368年洪武帝朱元璋登基到1425年明成祖朱棣即位,實現明朝的又一個大發展,用了57年時間;在清代,從1616年清太祖努爾哈赤建國到1670年康熙真正意義上理政,創造康乾盛世,用了54年時間。按此規律來看,新中國無疑也正處在一個非常有利的繁榮點上。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不能很好地抓住這樣的機會,利用這樣的機遇,就有可能使這樣的興盛點變成衰亡點,即黃炎培先生所言的歷史周期律點。1945年7月,黃炎培到延安考察時,與毛澤東有過一段著名的“窯洞對”,他認為,歷史演進過程總是存在一個“其興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執政周期律,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或政怠宦成或求榮存辱或人亡政息。毛澤東的回答是: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毫無疑問,毛澤東提出的解決周期律的道路是正確的。中國社會的發展證明,“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 〔2 〕 (P370 ),“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 〔3 〕 (P10 )。問題的關鍵是,我們在發展的過程中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很多棘手的問題都擺在我們面前,如果不能有效解決和應對,其后果可想而知。
顯然,這兩方面,無論哪一方面都需要我們有一個可靠的制度作保障。而我們的制度安排實際卻又不盡完善,以至于在一定群體中形成了大面積的制度焦慮甚至出現了制度崩潰論等夸張論調,當然也有一部分人對我們的制度持盲目機械的樂觀,認為我們的制度具有無限適應性,無需大刀闊斧的改革。事實上,無論是制度崩潰論還是制度適應論,都不可取。客觀地講,我們的制度安排目前主要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制度設計問題,突出表現在:制度缺失;制度老舊;制度相互打架;制度形同虛設,要么是空洞之作,要么是應景之作;有的制度是因人而設、因利益集團而設;有些制度則缺乏現實的可行性、科學性,沒有具體的執行機制,如搶黃燈罰分的規定,還比如有關黨員干部的從政規定,據統計,截至2012年6月,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共出臺了2.3萬多件中央文件,其中中央黨內法規和規范性文件有1178件,但 “四風”問題之所以還如此嚴重,很大程度上跟規定不盡合理、缺乏操作性相關。二是制度執行問題,主要是現實生活中,一些執行者故意規避某些制度規定,選擇性地執法或行事,從而使制度在執行過程中失效,如以黨紀處分來代替或逃避法律處分,處罰輕重因人而定,等等。這既會使大家覺得制度的不公,也會讓人產生僥幸心理,在全社會形成不良的社會風氣。由此可見,制度合理性在合法性建設中意義重大。從實際看,“效率很高但缺乏合法性的社會,如管理良好的殖民地,要比效率相對低但合法性高的政權更不穩定……另一方面,延續幾個世代,長期保持效率的政治制度可以得到合法性” 〔4 〕 (P57 )。顯然,要解決我們黨目前面臨的諸多阻礙“民治”效能的制度性問題,就必須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三、解決社會焦點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回應的現實基礎
目前,我們正處于社會的深度轉型期,這種轉型極大地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改變了我們的社會面貌,同時也給我們帶來了各種各樣的危險和挑戰,這即是我們常說的轉型危機,其中的一個基本現象就是“中等收入陷阱”。世界銀行認為,在當今世界普遍存在這樣一種現象,新興國家突破人均GDP1000美元的“貧困陷阱”后,很快會進入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起飛階段”,但到人均GDP3000美元附近時,由于快速發展所積聚的矛盾和問題將集中爆發,而自身的體制與機制的更新又進入了臨界,難以克服自身矛盾,發展戰略頻頻失誤或遭受外部沖擊,最后經濟增長回落或長期停滯,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的定義和標準,2010年我們國家即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正面臨和經歷著各種各樣的陷阱。
概括起來看,我們遇到的社會焦點問題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發展的可持續問題。包括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產業結構不合理,資源枯竭加快,環境污染嚴重,科技創新不強,農業基礎薄弱,發展方式粗放,貧富差距拉大,等等。以能源消耗為例,據統計,2012年,我國經濟總量約占全球的11.5%,卻消耗了全球21.3%的能源、45%的鋼、43%的銅、54%的水泥;原油、鐵礦石對外依存度分別達到56.4%和66.5%,排放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總量已居世界第一。再比如,我們的基尼系數近十年來一直在0.48左右徘徊。這些問題,使得我們國家的科技發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人文發展遠遠不夠。二是發展的和諧穩定問題。突出表現為教育、醫療、住房、就業、社會保障、安全生產、生態環境、執法司法、社會治安、食品藥品安全等民生問題凸顯,由此而導致的社會失序、結構失衡、道德失范、溝通失暢、信息失真、動力失迷、行為失調、環境失美、農民失地、農村失力等負面現象及其連鎖性社會沖突也頻頻發生。三是黨的建設問題。表現在一些干部領導科學發展能力不強,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少數黨員干部理想信念動搖、宗旨意識淡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享樂主義和奢靡之風等現象屢禁不止,各種各樣的腐敗現象呈多發易發態勢,等等。這些問題直接關系到老百姓的生計和民心向背,沖擊和腐蝕著社會穩定的根基和堤壩,從民意調查就可見一斑。2012年11月,《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以“你看好未來十年中國的發展嗎”為題,通過題客調查網和民意中國網,對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11405名網友,實施了在線即時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未來十年中,最期待能得到顯著改善的問題依次是:醫療(68.8%),教育(62.8%),食品安全(60.3%),收入分配(56.7%),住房(53.5%),反腐敗(53.4%),養老(52.1%)與社會保障(50.4%),環境保護(46.3%),就業(43.5%)。2012年11月,《新京報》與清研咨詢也作了一項“中國未來十年最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哪些”的調查,結果顯示:排在前六位的依然是貧富差距拉大(81.3%),腐敗問題(75.5%),環境污染惡化 (69.9%),醫療改革等民生問題 (61.4%),城市房價居高不下 (57.0%) ,交通擁堵等城市病 (55.8%)。顯而易見,人民的最大焦慮是民享,即如何才能更多更公平地享受到社會發展的成果,改善民生,而要妥善解決這一系列問題,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必由之路。
四、解決發展的應然性問題是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回應的不竭動力
現代化是世界各國發展面臨的根本任務和必經道路,也是我國發展戰略的題中之義,現代化的實現程度直接決定執政合法性的物質基礎和文化動力。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既是實現和滿足現代化的傳統要求,更是回應和建構現代化的新要求。新中國成立后,現代化旋即構成我們黨的指導思想和國家的發展方向,更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人最熟知、最響亮的一個概念,構成當代中國的主旋律、最強音之一,變成了人們社會生活中的常用語、流行語。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化的外延和內涵也在不斷變化,時至當下,我們所要實現的這個現代化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而是中國特色的新型現代化,這就必然要求我們黨對之作出適應性轉變。
從歷史進程看,世界范圍內的現代化經歷了現代化向后現代化、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德性向德性之后的轉變,大致可以分為兩大階段:一是物質主義現代化。其以工業革命的開始為標志,以經濟發展為指向,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農業經濟向工業經濟、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變。二是后物質主義現代化。二戰之后,隨著第一次現代化的推進,科技進步在給人類帶來巨大進步的同時,也給人們帶來了無限的傷害,突出的表現是“貧富差距持續擴大,物欲追求奢華無度,個人主義惡性膨脹,社會誠信不斷消減,倫理道德每況愈下,人與自然關系日趨緊張” 〔5 〕,等等。按照馬爾庫塞的觀點就是人被變成了“單向度的人”,由此而引發的各種“新社會運動”也在美國等地頻頻發生,所以現代化在從工業社會向知識社會、工業經濟向知識經濟、工業文明向知識文明的同時也在人們的促動、反思和批判中由物質文明向精神文明轉變。人們普遍認識到,現代化的主線應該是生產力的解放和人性的解放,只有實現生產力、生產關系與上層建筑統一的現代化才是完整的現代化,而核心是人的現代化。從我國看,我們對現代化的實踐和認識也是曲折而行。近代以來到新中國成立,我們的現代化歷程經歷的是從器物現代化到制度現代化再到文化現代化的試錯轉換。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又提出過很多具體的現代化,并把農業、工業、科技、國防這四個現代化確定為我們的基本國策和目標。然而在具體實踐中,人們普遍有一個這樣的認識和觀念,似乎只要把這些現代化拼接起來,一個現代化國家就自然而然地孕育而生了,并且樂觀和堅定的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和人的問題就解決了。而事實證明,答案并不是如此,相反,正是這種誤識的觀念和單槍匹馬式的零散改革,才形成了當前的諸多矛盾和困境,這不得不讓我們不斷反思:我們到底需要什么樣的現代化?靠什么推進現代化?怎樣實現現代化?
顯然,改革走到今天,現代化的范疇和要義已經發生變化,不僅物質層面的范疇和向量大大擴大,精神層面的內容和層次也大大拓展,人的現代化更是居于其上,歸結到一點就是要使文化的價值比重、價值訴求和價值含量越來越多。事實也證明,無論哪個歷史階段哪個國度,文化在治國理政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歷史也似乎就是進行文化修補、矯正甚至創設的循環過程,比如近代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是以文化的更替來跨越的,即器物發展(洋務運動)——制度革新(君主預備立憲)——文化易幟(馬克思主義),新中國成立后,又開始了一個物質建設——制度改革——文化補課的新循環。無怪乎說,“文化上的每一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 〔6 〕 (P154 ),“對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來說,最持久、最深層的力量是全社會共同認可的核心價值觀。核心價值觀,承載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的精神追求,體現著一個社會評判是非曲直的價值標準” 〔7 〕 (P5 )。所以說,“測試合法性的主要方法,是看那個國家已經培養起一種共同的‘良期延續的政治文化’的范圍” 〔4 〕 (P56 )。我們黨提出的國家治理現代化是蘊含著深層次文化訴求的后現代化,尤其是所引發或要求的各項改革舉措的關聯性、耦合性也就會越來越強,那就必須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這種新型現代化才能平穩持續地向前推進。無疑,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構建起一整套更加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就成了當前非常迫切和緊急的任務,那即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五、建設法治中國是對國家治理現代化合法性問題的根本回應
總之,上述四重問題,既是政治合法性建構的重要內容,也是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題中之義。換言之,要實現國家治理現代化必須對這些合法性問題作出回應并進行妥當紓解,而根本路徑是建設法治中國。其核心原因在于,按照合法性理論,法律是所有合法性資源中最理性、最基礎、作用效率最長久的資源,不僅如此,其他合法性資源的建構都必須以法律資源的獲取為前提和保障。時下,我國的合法性建設中法理不足、傳統和魅力介入有余已是不爭的事實,正如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所指出的:“必須清醒看到,同黨和國家事業發展要求相比,同人民群眾期待相比,同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目標相比,法治建設還存在許多不適應、不符合的問題” 〔8 〕 (P3 ),其中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有些領導干部的人治思維和運用人治手段解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問題還有較大市場,這大大削弱了合法性的基礎。從某種程度上說,除了經濟發展滯后外,對合法性資源形成最大阻滯的就是人治,其特征突出體現在:血緣政治,權力家族化;圈子政治,權力部門化;條子政治,權力人情化;權貴政治,權力商品化;特權政治,權力私有化。這五個特征只是人治主義在權力運行方面的一個縮影,而由此所牽涉的社會和民眾影響則更為廣泛。從表面上看,這是人治主義遮蔽了法治的效率和功能,而本質上還是法治建設的不足。實踐證明:“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法治是治國理政的最科學方式,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和原則:一方面,法律確認的授權模式和制度框架讓人們有自然性認同;另一方面,法律規制的限權原則和權責方向讓人們有信服性認同;再者,法律孕育的權利精神和文化意識讓人們有自我性認同。無疑,回應執政的合法性問題,“還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 〔2 〕 (P379 )。
質言之,國家治理現代化是我們黨適應世情、國情和黨情變化而提出的一個重大戰略也是迫切舉措,表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了新的階段,有了新的目標和新的歷史任務,實質是夯實執政的合法性基礎,豐富執政的合法性資源,而最終的路徑則是建設法治中國。可以說,法治既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基本手段也是根本目標。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已經為此指明了方向,可以相信,假以時日,由法治現代化及至國家治理現代化再至中國夢一定能夠實現。
參考文獻:
〔1〕〔德〕柯武剛,史漫飛.制度經濟學:社會秩序與公共政策〔M〕.韓朝華,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0.
〔2〕鄧小平文選: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3〕胡錦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奪取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新勝利而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4〕〔美〕美西摩·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會基礎〔M〕.劉剛敏,聶容,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5〕習近平. 在紀念孔子誕辰256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上的講話〔EB/OL〕.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09-24.
〔6〕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國外文局.習近平談治國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8〕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責任編輯 周 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