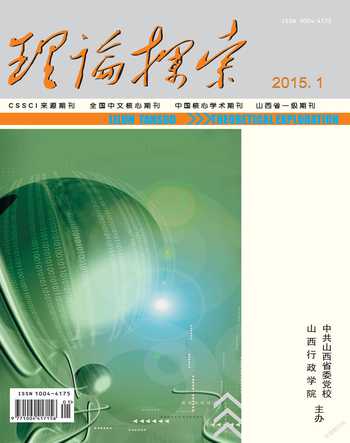為劫財故意殺人的定罪處罰問題
〔摘要〕 搶劫致人死亡是否意味著行為人對死亡結果的罪過僅限于過失,刑法學界的意見并不一致。該問題需要結合法條競合和想象競合等刑法學原理進行體系解釋。如果對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行為按照故意殺人罪和搶劫罪實行數罪并罰,會導致殺人行為受到雙重評價。承認搶劫罪的方法行為包括故意殺人,則會避免定罪的混亂。如此,以殺人的方式劫取財物,即使未發生加重結果也適用升格法定刑。而結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態并非以是否發生致人重傷、死亡的結果為判斷標準,應當以搶劫罪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是否齊備為根據。
〔關鍵詞〕 搶劫罪,故意殺人,法條競合,結果加重犯
〔中圖分類號〕D9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175(2015)01-0115-05
〔收稿日期〕2014-09-10
〔作者簡介〕王鵬飛(1987-),男,山西懷仁人,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為刑法學。
《刑法》第263條規定,“致人重傷、死亡的”是搶劫罪的加重處罰情形。刑法理論界對于“致人重傷”的罪過形式包括故意幾乎不存在爭議,〔1 〕 (P863 )而對于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行為,應當處以搶劫罪一罪還是按照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仍然存在分歧。問題的關鍵在于搶劫罪的方法行為是否包括故意殺人,而僅從文義上理解,難以確切地作出說明。那么,對于該種情形,還需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進行體系解釋。厘清該問題的意義在于,通過明確搶劫罪的行為類型,尋求更為合理的定罪處罰方式,進而闡釋結果加重犯成立與結果加重犯未遂的關系
一、對刑法分則中“暴力致人死亡”的考察
在《刑法》第263條的規定中,“致人死亡”是否意味著對死亡結果的罪過形式包括故意,從字面意義上難以明確。否定說認為,在結果加重犯中,行為人對于加重結果的主觀罪過只能是過失,如果積極追求加重結果,就會使犯罪的性質發生轉變。〔2 〕肯定說認為,通過刑法條文中其他涉及“致人死亡”的規定可以看出,在有些犯罪中,“致人死亡”的結果是因行為人故意實施危險方法而引起,而在有些犯罪中,“致人死亡”的結果只能由行為人的過失行為所引起。因此,依據“致人死亡”的規定不能確定對死亡結果的罪過形式僅限定于過失。〔3 〕 (P560 )目前,肯定說成為刑法理論界的主流觀點。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關于搶劫過程中故意殺人案件如何定罪問題的批復》規定,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以搶劫罪定罪處罰。筆者認為,肯定說解釋“搶劫致人死亡”的方法可以稱為體系性考察下的文義解釋,即通過聯系刑法條文中關于“致人死亡”的含義,說明“搶劫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是否僅限于過失。然而,持否定立場的論者對此種解釋提出質疑,認為僅通過“致人死亡”雖然不能明確行為人對死亡的心理態度,但是即便不能說明僅限于過失,同樣也不能說明其罪過形式包括故意。〔4 〕如此看來,在通過體系考察“致人死亡”的含義之后,對于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的問題仍存在分歧。此種爭論雖然建立在體系解釋的方法上,卻并未明晰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的問題。筆者認為,解決該問題既需要梳理刑法分則中“致人死亡”所具有的含義,又需要厘清其與“搶劫致人死亡”的關系。
搶劫罪的手段行為通常表現為暴力、脅迫等具有強制性特征的行為。那么,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情形能否屬于“搶劫致人死亡”,可以聯系刑法分則中涉及“暴力致人死亡”的規定進行考察。筆者認為,關于“暴力致人死亡”的規定可以劃分為五類。第一類,罪狀描述雖未明確規定“暴力”二字,但暴力致人死亡屬于適用升格刑的法定條件,例如,《刑法》第234條規定的故意傷害罪。在故意傷害罪中,行為人對死亡結果的罪過形式僅限于過失。對此,刑法理論界不存在爭議。第二類,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發生致人死亡結果的情形,例如,刑法分則第二章中的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劫持航空器罪。在該種情形中,“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能夠包括故意,刑法理論界對此亦不存在分歧。第三類,刑法明文規定,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依照故意殺人罪、故意傷害罪定罪處罰,例如,《刑法》第238條規定的非法拘禁罪。從本罪規定可以看出,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可能構成故意殺人罪,也可能構成故意傷害罪,如此意味著暴力致人死亡的性質并非僅限于過失致人死亡。第四類,刑法條文同時規定了“致人死亡”和“殺害他人”的,從而得以明確“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只是過失,例如,《刑法》第239條第二款規定,致使被綁架人死亡或者殺害被綁架人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第五類,“致人死亡”是適用升格法定刑的條件,但是“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是否包括故意,僅憑文義解釋難以明確,刑法理論界仍存在分歧,例如,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情形能否屬于搶劫致刑罰人死亡。
由此可見,刑法分則視域下的“致人死亡”可能意味著僅限于行為人的罪過為過失的情形,也可能意味著方法行為包括故意殺人的情形。按照三段論的邏輯路徑,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是否屬于搶劫致人死亡是待證明的問題。如果體系性地考察“致人死亡”的文義,其罪過形式是否僅限于過失是證明該問題的大前提。否定說的缺陷在于片面地將“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限定為過失,那么,由此作出的邏輯推論便缺乏說服力。然而,僅通過明確刑法分則中“致人死亡”包括的類型亦不能確定搶劫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包括故意。從認識論上看,作為認識“對象”的社會現象的本質,在不同的論域里是不同的,或者說,對象所在論域不同,它的本質就不同。〔5 〕搶劫致人死亡是刑法分則中的特定規定,而在分析“致人死亡”所包括的類型時是以刑法分則的所有規定為視域。那么,本文所言“致人死亡”與“搶劫致人死亡”屬于不同關系界域中的概念,其二者的性質不應該被混同,否則會陷入循環論證。而且,按照三段論法的邏輯推論,根據“刑法分則并未將‘致人死亡’限定為過失”,結論則應當是:搶劫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可能僅限于過失也可能包括故意。由此可見,肯定說以“《刑法》第263條沒有明文將‘致人死亡’限定為過失”為依據,在論證過程中有偷換概念之嫌,并無法合理說明搶劫罪的方法行為是否包括故意殺人。因此,通過體系考察“致人死亡”的文義仍然會留下搶劫致人死亡是否包括故意殺人的疑問,該問題還需根據競合理論等刑法學原理進行說明。
二、法條競合中的“暴力行為”——按搶劫罪一罪處斷的依據
學界對于以故意殺人的方法劫取財物應如何定罪主要有三種觀點:(1)按照搶劫罪一罪處罰;(2)按照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從一重罪處罰;(3)按照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數罪并罰。那么,何種處理方式更合理,應以禁止重復評價原則為指導,根據法條競合和想象競合刑法學原理進行檢驗。禁止重復評價原則是普遍公認的刑罰原則,其意義在于對同一犯罪事實不能采用不同的犯罪構成重復論罪。〔6 〕 (P407 )法條競合和想象競合的基礎則是禁止重復評價原則。張明楷教授指出:刑法理論應當改變方向,與其重視和增加犯罪之間的對立,莫如注重犯罪之間的競合,減少犯罪之間的對立,充分運用想象競合和法條競合的法理尋求正確適用刑法、準確定罪量刑的有效途徑。〔7 〕 (P243-268 )
(一)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的法條競合。搶劫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是否包括故意,刑法理論界存在分歧,然而,對于致人重傷的罪過包括故意,則幾乎不存在爭議。筆者認為,暫且不論發生致人死亡的加重情形,以搶劫致人重傷與故意傷害罪的法條關系為切入點能夠為爭議問題的解決提供思路。
暴力、脅迫等方法行為是搶劫罪的犯罪構成要素,該方法行為是以足以壓制對方的反抗為底限。對于搶劫罪的基本犯而言,行為人為劫取財物而實施的暴力行為不以造成他人傷害為必要,只需達到足以壓制對方反抗的程度即可。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則屬于造成致人重傷的情形。那么,既然搶劫致人重傷依然僅構成搶劫罪一罪,搶劫致人輕傷更能符合本罪的犯罪構成。而且,如果搶劫致人重傷的罪過包括故意和過失,致人輕傷的罪過也就不能僅限于過失。由此,搶劫罪的方法行為可以劃分為三種情形:(1)搶劫的方法行為僅足以壓制對方的反抗,并未造成對方輕傷以上的后果;(2)搶劫的方法行為致人輕傷;(3)搶劫的方法行為致人重傷。同時,以是否造成致人輕傷的結果為標準,搶劫罪的基本犯又可以劃分為無傷害類型和輕傷害類型。當行為人實施的搶劫行為符合輕傷害類型時,無疑也可以說明其實施的強制行為屬于故意傷害,同時符合故意傷害罪的犯罪構成。如此一來,就普通的犯罪構成而言,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之間存在包容關系。而且,根據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同時規定了“致人重傷”和“致人死亡”的情形,進而可以說明搶劫罪的規定完全包容了故意傷害罪的規定。由于搶劫罪的罪狀中還包括劫取財物的描述,則搶劫罪的規定與故意傷害罪的規定之間具有特別法與普通法的關系,屬于法條競合。那么,為劫取財物而故意傷害的行為同時符合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的規定。根據法條競合時適用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處理原則,為劫取財物而故意傷害的行為只能適用搶劫罪的規定。如果按照搶劫罪和故意傷害罪實行數罪并罰,故意傷害行為顯然受到了雙重評價,有悖禁止重復評價原則。
從本質上看,為劫取財物而故意傷害的行為僅適用搶劫罪的規定,是運用法條競合處理原則的結果。筆者認為,運用法條競合原理的意義不僅在于處理一個行為符合數個法條規定時的適用問題,還在于當無法確定某一行為的刑法適用時,假設兩種犯罪規定之間存在法條競合的關系,從而評價應實行數罪并罰還是按一罪處理的合理性。關于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行為的刑法適用問題,刑法理論界未形成一致的見解。那么,可以通過假設搶劫罪的方法行為包括故意殺人,使得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之間形成法條競合的關系,進而比較按搶劫罪一罪處理和實行數罪并罰的合理性。
(二)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法條競合。關于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罪數,刑法學界主流觀點認為應當是搶劫罪一罪(以下簡稱“搶劫罪一罪說”),也有學者認為應當屬于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以下簡稱“想象競合說”)或者按照兩罪實行并罰(以下簡稱“數罪并罰說”)。根據以上的分析,如果構成搶劫罪的方法行為包含故意殺人,則可以說明搶劫罪的規定與故意殺人罪的規定之間存在法條競合的關系。“搶劫罪一罪說”與“數罪并罰說”相對立的基本點在于是否承認搶劫罪的方法行為是否包括故意殺人的情形,換言之,是否認可按照法條競合處理的合理性。
按照“數罪并罰說”的觀點,搶劫致人死亡意味著行為人對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僅限于過失。如果行為人積極地追求加重結果,就會使犯罪的性質發生轉變。那么,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不再是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應當以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筆者認為,雖然依此邏輯可以說明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行為會同時構成搶劫罪和故意殺人罪,但是按照兩罪實行并罰,在定罪處罰的合理性上值得商榷。當行為人以故意殺人的方式劫取了財物并且發生了致人死亡的結果時,如果認為行為人的暴力行為已經轉化了性質,則該暴力行為不能被搶劫罪的犯罪構成所評價。但是,如果故意殺人這種極端的暴力行為不能被納入搶劫罪的評價范疇,作為犯罪構成要素的暴力行為和非法占有財物就不能同時齊備。否則,由于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存在包容關系,則相當于將故意殺人行為按照故意殺人罪和故意傷害罪進行雙重評價,顯然有悖禁止重復評價原則。那么,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行為不符合搶劫罪的犯罪構成,僅構成故意殺人罪。如此一來,即使否認搶劫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包括故意,也不能按照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實行數罪并罰。但是,這便產生一個問題:行為人劫取財物的行為該如何評價?按照上述邏輯,由于構成搶劫罪的要素并不齊備,劫取財物的目的行為似乎只能根據搶奪罪的規定予以評價。但是,搶奪罪的規定只能適用于直接對物使用暴力的行為,并不能因人為地將方法行為與目的行為割裂后,再單獨適用于奪取財物的行為。由此可見,以故意殺人的方式奪取財物的行為亦不能構成搶奪罪。那么,將同時侵犯了人身權利和財產利益的行為僅認定為故意殺人罪,顯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如果否認搶劫致人死亡的罪過形式包括故意,就會產生上述的邏輯矛盾。按照“想象競合說”的觀點,搶劫罪的手段行為應當包括殺人這種最極端的暴力手段,那么,搶劫故意殺人的,成立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的想象競合犯。〔8 〕筆者認為,該種觀點雖然以肯定搶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殺人的情形為前提,卻混淆了想象競合與法條競合的特征。因為,既然搶劫罪的手段行為包括故意殺人,就意味著已經間接地肯定了搶劫罪的規定包容了故意殺人罪的規定。如果按照想象競合處理,則僅注意到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行為觸犯了兩個罪名,卻忽視了搶劫罪與故意殺人罪之間的包容關系。
筆者認為,如果搶劫罪的方法行為包括故意殺人,則上述問題便可以迎刃而解。根據上述分析,搶劫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殺人意味著搶劫罪的規定與故意殺人罪的規定之間存在法條競合的關系。按照特別法優于普通法的原則,將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行為直接按搶劫罪一罪論處,可以避免定罪的混亂。
三、未發生“致人死亡”的結果加重犯未遂問題辨析
出于對結果加重犯構造和性質的不同理解, 刑法學界對結果加重犯未遂的問題未形成統一的定論。該問題的論證主要圍繞行為人積極追求的加重結果未發生和發生了加重結果但基本犯未遂時的法定刑適用這兩個方面的內容展開,搶劫罪的規定也由此成為學界討論的焦點。以下,本文主要分析加重結果對成立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的影響以及結果加重犯的成立、既遂和未遂的判斷標準問題。
(一)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成立標準。搶劫致人死亡是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若行為人積極追求的致人死亡結果未發生,是否成立結果加重犯。對于此問題,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展開了論證。持否定立場的學者認為,加重結果是結果加重犯的成立要件,無此結果就不成立結果加重犯,也談不上有結果加重犯未遂成立之余地;〔9 〕 (P265 )持相同立場的學者還認為,加重結果在本質上是一種“情節”,情節加重犯是否存在即遂、未遂的問題,是由基本犯的犯罪形態決定的,當不具備法定情節時,則不構成情節加重犯,也就無所謂情節加重犯的既遂與未遂形態之分。〔10 ?〕 ?(P109 ?)持肯定立場的學者認為,依照“犯罪既遂模式論”,刑法分則所規定的結果加重犯的構成要件是以既遂為基本模式的,加重結果只能就結果加重犯的既遂形態不可缺少,而不成立結果加重犯既遂并非就不成立結果加重犯,可以因符合修正的犯罪構成而成立結果加重犯未遂。〔11 〕
筆者認為,結果加重犯是某一犯罪行為適用升格法定刑的情形,其成立、既遂還有未遂的情況并非同一層面的問題,而刑法理論界分析結果加重犯未遂的問題,并非僅意在說明某種犯罪形態的存在與否,其最終的落腳點在于確定是否適用升格的法定刑。正如我國學者所言,“討論該問題的目的無非是為了正確地解決刑罰的適用問題。” 〔12 〕 (P150 )按照通說的觀點,成立結果加重犯則適用升格法定刑。那么,問題的關鍵在于確定結果加重犯的成立標準:是否以加重結果的發生為必要。我國《刑法》第5條規定明確了罪刑相適應原則,即刑罰的輕重應當與既往犯罪行為的惡意和損害程度相適應,與犯罪人再次犯罪的危險性程度相適應。〔13 〕 (P20 )那么,適用升格法定刑的實質,是刑法對程度更為嚴重的犯罪行為所賦予的否定性法律后果。換言之,結果加重犯能否成立的關鍵應當從犯罪行為進行考察,如果行為人實施了更為嚴重的行為,即使未產生加重結果也適用升格的法定刑。否定說的不足之處在于孤立地看待加重結果,忽視了加重結果與犯罪行為的內在聯系。在為劫取財物而故意殺人的情形中,如果僅以是否發生致人重傷、死亡結果作為適用升格法定刑的判斷標準,則不符合罪刑相適應原則,與故意殺人罪的處罰也難以協調。〔11 〕筆者贊成肯定說的觀點,即行為人以殺人的手段行為搶劫財物,即使未發生致人死亡的結果時,也成立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而適用升格法定刑。但此種情形能否屬于結果過加重犯的未遂,還值得商榷。
(二)搶劫罪的既遂形態與結果加重犯的關系。未遂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態,那么,刑法理論中的基本犯未遂和結果加重犯未遂實質上都應當是犯罪本身的未遂。根據上文所述,如果行為人以殺人的手段行為劫取財物,未發生致人死亡的結果時也適用升格的法定刑,即成立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但是,該種情形是否屬于結果加重犯未遂,關鍵在于厘清搶劫罪既遂與結果加重犯的關系。對此問題,有必要結合德、日刑法典的規定進行比較分析。德國刑法典第249條和第251條分別規定了搶劫罪和搶劫致死罪。日本的立法模式與德國相同,刑法典也以不同條文分別規定了強盜罪、強盜致死罪和強盜殺人罪。那么,此種立法模式下的搶劫罪與搶劫致死罪屬于法定的不同種犯罪。換言之,基本犯與結果加重犯是不同犯罪的理論稱謂,其中搶劫罪僅指基本犯。如此一來,當某一行為符合搶劫罪基本犯的既遂條件時,如果行為人積極追求的致人死亡結果未發生,則屬于搶劫致死罪未遂,也就意味著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未遂。在此種情形下,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未遂與搶劫罪既遂并不沖突。
我國《刑法》僅以第263條規定了搶劫罪行為類型,并設定了兩種幅度的法定刑。與德、日刑法典的規定不同,我國《刑法》規定的搶劫罪不僅是基本犯的行為類型,還包括結果加重犯的行為類型。那么,搶劫罪的基本犯與結果加重犯屬于法定的同種犯罪,其罪名仍是同一的。因此,在我國刑法理論的語境下,搶劫罪并不等同于搶劫罪的基本犯,搶劫罪與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之間是包含與被包含的關系,即搶劫罪與搶劫罪的基本犯、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在邏輯上是屬與種的關系。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是否存在未遂的問題,本質上是搶劫罪本身應屬于既遂還是未遂的問題。換言之,當行為人以故意殺人的方式劫取財物時,是否發生加重結果并非結果加重犯未遂問題的唯一判斷標準,如果搶劫罪既遂的要件已經齊備,即使未發生加重結果也不存在結果加重犯未遂的情形。
(三)未發生致人死亡結果時的刑罰裁量。德、日刑法典規定中的搶劫罪專指基本犯,則在基本犯既遂的情況下也可能存在結果加重犯的未遂形態。而我國《刑法》第263條規定的搶劫罪,同時囊括了基本犯和結果加重犯的情形。因此,以我國刑法典為根據,搶劫罪結果加重犯的既遂或者未遂,應當根據行為是否完整地實現了搶劫罪的基本犯罪構成事實進行判斷。按照刑法理論界的通說,搶劫罪的方法行為要求達到足以壓制他人的反抗的程度,而且不要求造成他人人身傷害的結果。如果行為人對致人死亡的結果持有故意,其實施的殺人行為顯然符合構成搶劫罪的行為特征。當行為人劫取到財物且發生了其積極追求的加重結果時,其行為完全符合搶劫罪既遂的犯罪構成。而且,此種情形也屬于結果加重犯的既遂,應當適用升格的法定刑。問題在于,行為人積極追求的結果未發生或者劫取財物和人身損害的后果均未出現時應當如何處罰。筆者認為,行為人以殺人行為為手段,具備構成搶劫罪的方法行為要件,發生劫取財物的后果時,則齊備了成立搶劫罪既遂的全部要件。同時,即使未發生加重結果,依然成立搶劫罪的結果加重犯。那么,此種情形成立搶劫罪既遂,應當適用升格的法定刑。而出于對故意殺人未得逞的考慮,量刑時可以根據刑法總則關于犯罪未遂的立法精神,在升格法定刑幅度內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如此處理也能夠與故意殺人罪未遂的處罰相協調。如果劫取財物和人身損害的后果均未出現,則成立搶劫罪的未遂。此種情形屬于結果加重犯的未遂,應當適用升格的法定刑。那么,與成立搶劫罪既遂的情形比較,量刑時可以根據刑法總則關于犯罪未遂的規定,在升格法定刑幅度內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參考文獻:
〔1〕張明楷.刑法學(第4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2〕于志剛.犯罪停止形態中基本犯與加重犯的關系〔J〕.中國刑事法雜志,2009(1).
〔3〕高銘暄,馬克昌.刑法學〔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4〕王 爍.論搶劫罪的手段行為不應包括故意殺人〔J〕.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11(2).
〔5〕王 牧,犯罪概念:刑法之內與刑法之外〔J〕.法學研究,2007(2).
〔6〕陳興良.本體刑法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7〕張明楷.刑法分則解釋原理(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1.
〔8〕陳洪兵.論“搶劫致人重傷、死亡”〔J〕.法學論壇,2013(5).
〔9〕趙秉志.犯罪未遂形態研究〔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
〔10〕于志剛.刑法總則的擴張解釋〔M〕.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9.
〔11〕王志祥.結果加重犯的未遂問題新論〔J〕.法商研究,2007(3).
〔12〕劉之雄.犯罪既遂論〔M〕.北京: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
〔13〕阮齊林.刑法學(第三版)〔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
責任編輯 楊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