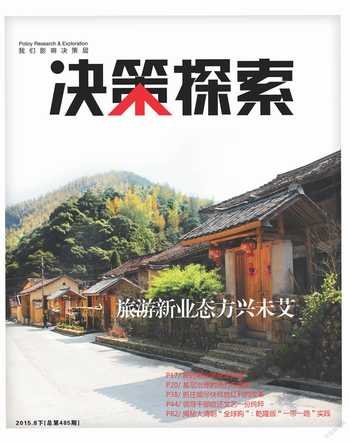“微時代”的文學使命
張奎志
當前,我們進入了一個“微時代”:微博、微信、微小說、微電影、微媒體、微廣告、微支付、微消費、微管理、微投資、微生活、微課程、微公益……可以說,“微”已經成為一種生活方式,成為當下的一個重要標志,也成為理解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詞。如果說,傳統文化是以“大”為特征,在以福特主義為綱領的現代化大工業時期,“大”成為備受推崇的發展方式、文化訴求的話,那么在新世紀,“微化”“微小化”、日常化、個性化成為一種新的文化訴求。
在這個“微時代”的背景下,政治也“微化”“微小化”了,成為一種“微政治”,形成一個“微政治時代”。這里所說的“微政治”,是指政治不再以搞運動式的、行政化的、命令性的方式運行,而是以日常性的、人性化的、親民式的方式進行。政治不再表現為暴風驟雨式的運動,而是以“潤物細無聲”的方式滲透在日常生活中。從政治信息的傳播和接受角度看,也開始走向“微小化”,行政部門不再通過傳統的“大媒體”——報紙、電視、廣播發布政令,而是以官方微信、官方微博的方式傳達政令,解答政務問題。人們接受政治信息的方式也發生了改變,從閱讀報紙、收聽廣播、收看電視,轉向通過新興的“微媒體”——微信、微博、博客、短信來了解時事政治。在通過新興的“微媒體”接受政治信息的同時,人們也通過微信、微博、博客、短信表達自我的政治訴求,以“自媒體”的方式主張和行使自身的話語權利。
因此,在“微時代”,政治是以一種“微小化”、日常化、個性化的方式和每個人緊密聯系著,它更體現在人們日常生活的行為、言行中。可以說,“微時代”的政治與日常生活相伴、和文化結合、和信息相隨,以一種普泛化、日常化、個性化、碎片化的方式滲透在人們的生活中。
娛樂化傾向與政治訴求并存
當“微時代”政治以“無意識”的方式包圍著人們時,文學自然也無法擺脫與政治的聯系。文學與政治的關系是文學史中不可回避的話題,文學與政治的聯姻與疏離也深刻反映著文學的演進與變革。“微時代”政治不再是以外在的方式干擾文學,文學本身就是政治。傳統時代的文學觀說,“文學是人學”;而“微時代”則說,“文學是政治”。正如文學要表現人一樣,文學也要表現政治。美國著名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遜就指出:“一切文學,不管多么虛弱,都必定滲透著我們稱之為的政治無意識,一切文學都可以解作對群體命運的象征性沉思。”
“微時代”的文學與政治的聯系又不同于此前,它有著鮮明的時代特征。這就是文學的娛樂性、休閑性和消遣性。一句話,文學更加娛樂化。這是因為在“微時代”,生活日趨娛樂、休閑和消遣。“玩”成為“微時代”文化的一個特征,“微時代”的文學也無法擺脫其娛樂、休閑和消遣的特點。因此,“微時代”會沿著政治性和娛樂性這兩條路線行進:一方面,滿足讀者“玩”和娛樂性、消遣性的通俗文學、網絡文學會高歌猛進。武打、游戲、玄幻、穿越、言情、盜墓、公案、恐怖等小說還會大行其道,從不同的層面滿足讀者的閱讀、消遣需求;另一方面,“微時代”的娛樂文學也滲透著“政治無意識”。因此,與純游戲性、娛樂性的作品不同,在一些看似游戲性、娛樂性、消遣性的作品中,也會表達一種善或惡、美或丑的道德訴求,這是一種道德傾向,同時也是一種政治訴求。
宏觀時代的“微觀反映”
同時,承擔政治使命、文化使命、文學使命的文學也會一如既往地向前推進。文學之所以和政治聯姻,就如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所說,“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人離不開政治,因為人是有意識的存在物。作為有意識的存在物,人的一言一行也必然傳達出一種意識信號。文學作為人的一種意識活動,也總是要表達一種意識、觀念或想法。可以說,什么也不想表達、什么也不想說明的文學作品是不存在的。不論作者自覺或不自覺,也無論讀者意識到或沒有意識到,文學作品總要表達一種意識、一種觀念。因此,進入“微時代”,文學的使命變得更重要,文學不再是一種“游戲”式的或非功利的,它總是或隱或顯地表達一種意識、一種觀念、一種政治訴求。并且,具有“使命性”和“娛樂性”的兩種文學會不時在電影、電視及新媒體中會合,交替吸引著讀者和觀眾的目光。
“微時代”文學的另一個特征就是文學的“微小化”,形成一種“微文學”。“微文學”的“微”就“微”在人上,反映的是“微人”。“微文學”聚焦于“人”,但不再是大寫的“人”;聚焦于人的情感,但不是那種政治化、概念化的情感;聚焦于人的觀念,但不是脫離瑣細日常生活的觀念;聚焦于時代中的人,而不是聚焦時代。相對于那種大時代、大主題、大人物、大題材的文學來說,“微文學”更關注小人物,更貼近日常生活,表現人的“微生活”“微情感”,描寫“微人物”“微世界”,表達“微思想”“微觀念”,展示“微理想”“微價值”“微主題”。當然,“微文學”不是對時代的完全摒棄,它是以“微”的方式反映時代,它所表現的是“微時代”“微生活”“微情感”,是宏觀時代的“微觀反映”,也是“微觀時代”的宏觀反映。因此,這里所說的“微”,并不是微不足道,“微文學”完全可以通達到政治,透露出一種政治智慧、一種政治內容。
在中國文學史上,花間詞、艷詞、閨怨詞就屬于“微文學”,但這種表現“微生活”“微情感”的“微文學”,古人也將其通達于政治,所謂的“借花卉以發騷人墨客之豪,托閨怨以寫放臣逐子之感”(劉克莊)、“假閨房兒女之言,通之于《離騷》、變雅之義”(朱彝尊)、“寫怨夫思婦之懷,寓孽子孤臣之感”(陳廷焯),強調從閨房兒女之言和花卉草木抒寫“孽子孤臣”和賢人君子濟世情懷。從這一點看,“微文學”完全可以通之于政治。張惠言甚至提出“微言”一詞。主張“興于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可以看出,以“微言~微文學”的方式表達騷雅之意,也是中國古代文學的傳統。
“微時代”文學還有一個特征是文學的“技術化”“技巧化”。“微時代”信息爆滿,各種信息從四面八方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在這種信息多元、娛樂多元的時代,如何能吸引讀者、引發讀者的閱讀興趣是“微時代”文學面臨的一個重要任務。為此,“微時代”的文學就要在“技術化”“技巧化”方面下功夫。文學的“技術化”“技巧化”是多方面的,這其中既有內容方面的技巧,如怎樣實現文學與政治聯姻,通過文學表達政治訴求,而這種政治訴求又符合文學的規律,能為廣大讀者所接受。當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出“莎士比亞化”和“席勒式”,要求文學創作要“更莎士比亞化”,不應該“席勒式地把個人變成時代精神的單純的傳聲筒”。因此,通過文學表達政治訴求就有一個技術和技巧的問題,否則將適得其反。同時,“微時代”的文學也是一種“微閱讀”。“微閱讀”講究新穎、獨特、有趣。“微時代”文學在形式上也應注重新穎、獨特,更注重形式的“技術化”和“技巧化”。這其中既有結構構思的“技術化”“技巧化”,也包括語言表達的“技術化”“技巧化”。只有具備了形式上“技術化”“技巧化”的文學,也才能更容易被讀者接受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