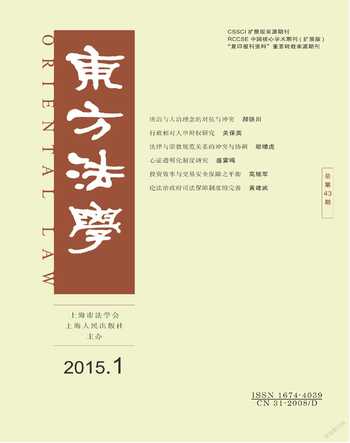論國(guó)際體系、格局變動(dòng)中限制日本主權(quán)國(guó)際協(xié)定的法律地位
管建強(qiáng)
內(nèi)容摘要:冷戰(zhàn)背景下,“舊金山和約”格局的出現(xiàn)加之東歐劇變和蘇聯(lián)解體,雅爾塔體系解體之說(shuō)頗為盛行。日本學(xué)界、政界不斷拋出“舊金山和約”優(yōu)先論來(lái)抗辯《開(kāi)羅宣言》等限制日本主權(quán)的國(guó)際協(xié)定的拘束力。雅爾塔體系下限制日本主權(quán)的國(guó)際協(xié)定正在被日本以各種方式試圖突破。梳理國(guó)際政治體系與政治格局變化的相互關(guān)系,研究雅爾塔體系下限制日本主權(quán)協(xié)定與“舊金山和約”的沖突的效力沖突較之宏觀上強(qiáng)調(diào)雅爾塔體系有效與否更具可操作性。事實(shí)上,冷戰(zhàn)格局的變化,不等于國(guó)際協(xié)議效力的廢棄,也不等于雅爾塔體系的解體。中日邦交所再度確立的《開(kāi)羅宣言》等一系列協(xié)定的拘束力,是鎖定中日政治格局的法律基礎(chǔ)。
關(guān)鍵詞:開(kāi)羅宣言 波茲坦公告 現(xiàn)代國(guó)際法 國(guó)際關(guān)系 雅爾塔體系
引 言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下簡(jiǎn)稱(chēng)“二戰(zhàn)”)后期,確立的旨在遏制德、日軍國(guó)主義復(fù)活的雅爾塔體系(也有稱(chēng)雅爾塔體制)是大國(guó)對(duì)戰(zhàn)后世界所作的安排。雅爾塔體系是以《開(kāi)羅宣言》為核心的重新劃定日本疆界及其被占領(lǐng)地區(qū)的邊界的重要協(xié)議。2010年9月,日本東京政府宣布“購(gòu)買(mǎi)”釣魚(yú)島,企圖以此方式?jīng)_破雅爾塔體系束縛、推翻二戰(zhàn)結(jié)束時(shí)的一系列定論。2013年4月28日,日本政府在東京大肆進(jìn)行了所謂主權(quán)回復(fù)紀(jì)念日活動(dòng)。其目的就是表達(dá)日本已經(jīng)擺脫了雅爾塔體系下的限制日本主權(quán)協(xié)定的約束,成為了一個(gè)正常的國(guó)家。面對(duì)中國(guó)的譴責(zé),日本學(xué)界、政界不斷拋出“舊金山和約”優(yōu)先論 〔1 〕來(lái)抗辯《開(kāi)羅宣言》的拘束力,實(shí)際上就是以“舊金山和約”格局來(lái)抗辯雅爾塔體系在東亞地區(qū)的適用。
一、國(guó)際體系與國(guó)際格局變化的關(guān)系
國(guó)際體系首先是一個(gè)最高層次的宏觀抽象概念,將國(guó)際政治領(lǐng)域內(nèi)所有行為體作為一個(gè)相互聯(lián)系的有機(jī)整體加以考察和理解。其次,國(guó)際體系是一個(gè)規(guī)則系統(tǒng),規(guī)定了系統(tǒng)內(nèi)主要行為體的基本特征,以及國(guó)際政治行為主體的運(yùn)行規(guī)律和基本狀態(tài)。
國(guó)際格局指在一定的國(guó)際體系規(guī)則制約和影響下,在一定時(shí)期和一定范圍內(nèi)的主要國(guó)際行為體之間的力量對(duì)比關(guān)系。〔2 〕
國(guó)際體系與國(guó)際格局之間既有明顯區(qū)別,又存在緊密的聯(lián)系。國(guó)際體系對(duì)于國(guó)際格局的影響是根本性的,國(guó)際體系的性質(zhì)和規(guī)則決定了國(guó)際格局的基本內(nèi)容。國(guó)際格局對(duì)于國(guó)際體系有重要的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會(huì)促進(jìn)或阻礙國(guó)際體系內(nèi)容的變革。兩者作用的方向一致,將極大地推動(dòng)新的國(guó)際體系的發(fā)展,適應(yīng)國(guó)際體系發(fā)展的國(guó)際格局將更好地維持國(guó)際秩序。如果相互背離,將在很長(zhǎng)一段時(shí)間內(nèi)阻礙體系變革的腳步,直到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將通過(guò)激烈的方式推動(dòng)變革。換言之,只有當(dāng)國(guó)際格局對(duì)抗國(guó)際體系發(fā)展到變革、顛覆舊的國(guó)際體系狀態(tài)時(shí),人們才可以說(shuō)體系已經(jīng)解體。因此,蘇聯(lián)解體后,瓦解的是兩極格局,而非雅爾塔體系的解體。
所謂“雅爾塔體系”是指二戰(zhàn)后期,戰(zhàn)勝?lài)?guó)(中、美、英、蘇),特別是美、蘇兩家按照自己的意愿對(duì)未來(lái)世界秩序進(jìn)行規(guī)劃,通過(guò)開(kāi)羅會(huì)議(1943年11月22—11月26日)、德黑蘭會(huì)議(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雅爾塔會(huì)議(1945年2月4—11日)和波茨坦會(huì)議(1945年7月18日—8月2日)等進(jìn)行的多次討論后形成的一系列協(xié)議和諒解,以及由此確立的旨在遏制德、日軍國(guó)主義復(fù)活并以此為邏輯起點(diǎn)的戰(zhàn)后國(guó)際和平秩序。其主要內(nèi)容是要求敵國(guó)無(wú)條件投降(完全接受雅爾塔體系的約束),處置戰(zhàn)敗國(guó)、重新確定戰(zhàn)后歐亞的政治版圖、建立聯(lián)合國(guó)等。基于以上的首腦會(huì)議形成一系列影響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公報(bào)、議定書(shū)、協(xié)定、聲明和備忘錄,特別是以《雅爾塔協(xié)定》為主體的國(guó)際關(guān)系體系,即雅爾塔體系。
1989年的東歐劇變和1991年的蘇聯(lián)解體,以美、蘇爭(zhēng)霸和意識(shí)形態(tài)斗爭(zhēng)為標(biāo)志的兩極格局結(jié)束。有人據(jù)此認(rèn)為雅爾塔體系解體了。“解體論”者認(rèn)為雅爾塔體系主要包含美、蘇兩極,蘇聯(lián)一極不存在了,世界就變成了美國(guó)一家獨(dú)大,世界進(jìn)入了“美國(guó)領(lǐng)導(dǎo)”下的體制。〔3 〕20世紀(jì)末,我國(guó)學(xué)術(shù)界、理論界關(guān)于雅爾塔體系有一個(gè)幾乎得到普遍認(rèn)同的命題:隨著社會(huì)主義蘇聯(lián)的解體,雅爾塔體系也就瓦解、崩潰了。〔4 〕
實(shí)際上,即使國(guó)際體系一如既往地存在,它也會(huì)因國(guó)際格局的變動(dòng)在非核心支柱領(lǐng)域作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例如,二戰(zhàn)后直至蘇聯(lián)解體之前,雅爾塔體系的也是受到一定程度的調(diào)整的。1945年雅爾塔會(huì)議公報(bào)中指出:“消滅德國(guó)的軍國(guó)主義和納粹主義,戰(zhàn)后將德國(guó)的一切武裝力量解除,予以解散。” 〔5 〕然而朝鮮戰(zhàn)爭(zhēng)后,隨著東西方兩邊陣營(yíng)的關(guān)系開(kāi)始緊張,各大國(guó)對(duì)德國(guó)的非軍事化政策有所改變。1990年兩德統(tǒng)一后,美、英、法、蘇四國(guó)與聯(lián)邦德國(guó)政府簽署《德國(guó)最終解決條約》(又稱(chēng)“二加四條約”),聯(lián)邦國(guó)防軍削減三十七萬(wàn)人,前民主德國(guó)的國(guó)家人民軍解散。在這國(guó)際格局的變化中,參與雅爾塔體系調(diào)整的有當(dāng)年雅爾塔體系的制定者。概言之,通常國(guó)際體系是由戰(zhàn)勝?lài)?guó)與戰(zhàn)敗國(guó)之間以一系列影響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公報(bào)、議定書(shū)、協(xié)定等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guó)際法所固定下來(lái)的。同樣,國(guó)際體系的變動(dòng)或國(guó)際格局的重新組合,最終都是需要通過(guò)有拘束力的國(guó)際協(xié)議來(lái)確立實(shí)施的。
雅爾塔體系是大國(guó)對(duì)戰(zhàn)后世界所作的安排,是戰(zhàn)后世界政治地圖、政治體制等的總稱(chēng)。從政治地圖上講,也許最大的變化就是德國(guó)統(tǒng)一了,東歐國(guó)家脫離了蘇聯(lián)陣營(yíng)獲得了更多的獨(dú)立性,僅此而已。但從政治體制上講,正如很多專(zhuān)家論述的那樣,聯(lián)合國(guó)是雅爾塔體系的一部分,〔6 〕是其核心和支柱,〔7 〕蘇聯(lián)解體后,雖然蘇聯(lián)一極超級(jí)大國(guó)不存在,但是繼承蘇聯(lián)主體的俄羅斯依然存在,俄羅斯在國(guó)際法上依然享有繼承蘇聯(lián)所締結(jié)的限制日本主權(quán)的條約上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據(jù)此得出的結(jié)論就應(yīng)該是:雅爾塔體系沒(méi)有瓦解,而是基于民族自決、主權(quán)獨(dú)立等民主化思潮的影響,從屬于雅爾塔體系的格局發(fā)生了重大的調(diào)整。
二、論限制日本主權(quán)的國(guó)際協(xié)定
國(guó)際體系是由戰(zhàn)勝?lài)?guó)之間以一系列影響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公報(bào)、議定書(shū)、協(xié)定等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guó)際法所固定下來(lái)的。同樣,國(guó)際體系的變動(dòng)或國(guó)際格局的重新組合,最終都需要通過(guò)有拘束力的國(guó)際協(xié)議來(lái)確立并實(shí)施。
二戰(zhàn)后期,戰(zhàn)勝?lài)?guó)(中、美、英、蘇),特別是美蘇兩國(guó)按照自己的意愿對(duì)未來(lái)世界秩序進(jìn)行規(guī)劃,通過(guò)開(kāi)羅會(huì)議、德黑蘭會(huì)議、雅爾塔會(huì)議和波茨坦會(huì)議等進(jìn)行的多次討論后形成的以《雅爾塔協(xié)定》為主體的處置戰(zhàn)敗國(guó)、重新確定戰(zhàn)后歐亞的政治版圖、建立聯(lián)合國(guó)的國(guó)際關(guān)系體系是通過(guò)具體的國(guó)際協(xié)議被鎖定的。前有1942年1月1日,美、英、中、蘇等26個(gè)國(guó)家發(fā)動(dòng)的《聯(lián)合國(guó)家宣言》為基礎(chǔ),后有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達(dá)成的《開(kāi)羅宣言》、1945年2月11日蘇、美、英達(dá)成的《雅爾塔協(xié)定》、1945年6月26日簽有50余國(guó)簽署的《聯(lián)合國(guó)憲章》、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蘇發(fā)表的《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以下簡(jiǎn)稱(chēng)《波茨坦公告》)以及《日本投降書(shū)》等國(guó)際文獻(xiàn),這些國(guó)際協(xié)議完成了近代國(guó)際法向現(xiàn)代國(guó)際法的進(jìn)化,推動(dòng)了國(guó)際法歷史性的邁進(jìn)。
迄今,日本右翼勢(shì)力甚至日本政府并不正面回應(yīng)雅爾塔體系的拘束力問(wèn)題,而是通過(guò)“舊金山和約體制”優(yōu)先論、“日本已經(jīng)是一個(gè)正常的國(guó)家”等論調(diào)來(lái)抹黑《開(kāi)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等協(xié)定法律地位。國(guó)內(nèi)一些學(xué)者受此影響也接受了所謂的:(1)《開(kāi)羅宣言》不是國(guó)際條約,不具有法律拘束力;(2)《波茨坦公告》是勝利者強(qiáng)加在戰(zhàn)敗者身上義務(wù),不具有公平性;(3)《開(kāi)羅宣言》以及《波茨坦公告》僅僅是軍事停戰(zhàn)協(xié)議,其效力低于為結(jié)束戰(zhàn)爭(zhēng)法律狀態(tài)的“舊金山和約”。
為此,本文不揣淺陋,從國(guó)際法的角度,針對(duì)具體的爭(zhēng)議點(diǎn),圍繞《開(kāi)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在與“舊金山和約”的沖突中的法律地位展開(kāi)研究。
(一)《開(kāi)羅宣言》法律拘束力不容否定
70多年前,中美英三國(guó)首腦齊聚埃及開(kāi)羅,于1943年12月1日發(fā)表《開(kāi)羅宣言》,明確宣示了三國(guó)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開(kāi)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的或占領(lǐng)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guó)之領(lǐng)土,例如滿洲、臺(tái)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guó)。〔8 〕1945年7月26日,發(fā)表了《波茨坦公告》,該公告再一次重申了“開(kāi)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shí)施”。〔9 〕同年9月2日,日本國(guó)簽署無(wú)條件投降書(shū),在《日本投降書(shū)》中明確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表明《開(kāi)羅宣言》對(duì)日本具有國(guó)際法效力。〔10 〕上述國(guó)際政治、法律文件是雅爾塔體系的重要內(nèi)容并構(gòu)成了建立戰(zhàn)后亞太地區(qū)秩序的國(guó)際性文件框架,明確了日本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侵占別國(guó)領(lǐng)土行為的非法性,確立了中國(guó)對(duì)臺(tái)灣及其包括釣魚(yú)島在內(nèi)的附屬島嶼等的主權(quán),是二戰(zhàn)后維護(hù)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證。
否認(rèn)《開(kāi)羅宣言》法律性質(zhì)的人認(rèn)為《開(kāi)羅宣言》僅僅是同盟國(guó)首腦之間缺乏書(shū)面簽署的約定,而且是一個(gè)“目的說(shuō)明”,因此,《開(kāi)羅宣言》不符合條約的格式要求,更不對(duì)第三國(guó)日本產(chǎn)生法律拘束力。〔11 〕
但是,從國(guó)際法角度而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2條1(a)規(guī)定:“就適用本公約而言:稱(chēng)‘條約’者,謂國(guó)家間所締結(jié)而以國(guó)際法為準(zhǔn)之國(guó)際書(shū)面協(xié)定,不論其載于一項(xiàng)單獨(dú)文書(shū)或兩項(xiàng)以上相互有關(guān)之文書(shū)內(nèi),亦不論其特定名稱(chēng)如何。”第3條規(guī)定:“本公約不適用于國(guó)家與其他國(guó)際法主體間所締結(jié)之國(guó)際協(xié)定或此種其他國(guó)際法主體間之國(guó)際協(xié)定或非書(shū)面國(guó)際協(xié)定,此一事實(shí)并不影響此類(lèi)協(xié)定之法律效力。”顯而易見(jiàn),雖然《維也納條約法公約》調(diào)整的條約僅僅是國(guó)際法主體之間的書(shū)面的協(xié)定,但是這一規(guī)定并不影響國(guó)際法主體之間的口頭協(xié)定的法律效力。換言之,非書(shū)面協(xié)定,如君子協(xié)定受?chē)?guó)際習(xí)慣法調(diào)整。此外,從以上的定義還可獲知,不管條約的名稱(chēng)如何,只要是國(guó)際法主體之間的創(chuàng)立權(quán)利義務(wù)法律關(guān)系的不違背國(guó)際法原則的協(xié)定就具有條約的性質(zhì),就具有法律拘束力。
當(dāng)然,涉及國(guó)家領(lǐng)導(dǎo)人之間發(fā)表的聯(lián)合聲明、公告等文件是否具有法律拘束力,還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判斷其拘束力的重要指標(biāo)就是要看這些聲明、宣言中是否明確了具體的權(quán)利和義務(wù)。如果對(duì)某事項(xiàng)未來(lái)的發(fā)展方向、重要意義作出泛泛而言的展望、強(qiáng)調(diào)等,那么這類(lèi)文獻(xiàn)是不具有法律拘束力的。而《開(kāi)羅宣言》明確地規(guī)定了同盟國(guó)之間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部分有:“我三大盟國(guó)此次進(jìn)行戰(zhàn)爭(zhēng)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guó)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wú)拓展領(lǐng)土之意思。”該宣言表明了三大同盟國(guó)打敗日本國(guó)之后也絕不吞并日本固有領(lǐng)土,這是其一;其二,同盟國(guó)承諾剝奪日本固有領(lǐng)土以外的一些領(lǐng)土,歸還至原屬?lài)?guó);其三,同盟國(guó)不得與日本商洽投降條件,必須統(tǒng)一在日本無(wú)條件投降的基礎(chǔ)上。事實(shí)上,《開(kāi)羅宣言》是促令日本無(wú)條件投降的法寶。卡薩布蘭卡會(huì)議結(jié)束后,羅斯福總統(tǒng)在1943年1月24日的記者招待會(huì)上第一次公開(kāi)使用了“無(wú)條件投降”的詞語(yǔ)。〔12 〕隨后在盟國(guó)各種文件中使用了這一術(shù)語(yǔ)。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發(fā)表《開(kāi)羅宣言》首次公開(kāi)重申對(duì)日的無(wú)條件投降政策,從而堅(jiān)定了各國(guó)的信心,保證了同盟國(guó)總戰(zhàn)略的實(shí)施;1945年2月11日的《雅爾塔公報(bào)》再度重申了對(duì)德的無(wú)條件投降政策。所謂“無(wú)條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是指對(duì)于戰(zhàn)勝?lài)?guó)提出的投降條件,不加以任何條件地投降。〔13 〕“無(wú)條件投降”的理論適用于戰(zhàn)爭(zhēng)行動(dòng)的停止,導(dǎo)致戰(zhàn)敗國(guó)同意同盟國(guó)提出的全部條件。適用這種做法的有:(1)德國(guó),它通過(guò)1945年5月7日的蘭斯投降書(shū)和8日的柏林投降書(shū)適用了這種做法;(2)日本,它通過(guò)1945年9月2日的投降書(shū)適用了這種做法。〔14 〕
“無(wú)條件投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時(shí)才出現(xiàn)的現(xiàn)象,是同盟國(guó)處置法西斯國(guó)家的一項(xiàng)重要政策。為保證同盟國(guó)團(tuán)結(jié)不被敵國(guó)離間,確保同盟國(guó)陣營(yíng)的成員不與任何敵國(guó)進(jìn)行停戰(zhàn)談判,使敵國(guó)全面接受同盟國(guó)提出的投降要求,而拒絕其提出的任何修改條件。因此拒絕敵國(guó)提出的任何條件的“無(wú)條件投降”原則是戰(zhàn)勝法西斯國(guó)家的重要法寶。可見(jiàn),《開(kāi)羅宣言》對(duì)三大同盟國(guó)規(guī)定了明確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內(nèi)容。即宣言的任何國(guó)家均有義務(wù)遵守上述規(guī)定,同時(shí)對(duì)任何違約者享有追究其違約責(zé)任的權(quán)利。簡(jiǎn)而言之,《開(kāi)羅宣言》的法律拘束力分為兩個(gè)階段,第一階段是該宣言公布之日開(kāi)始至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書(shū)簽字之前,這一時(shí)期該宣言所拘束的對(duì)象僅僅是三大國(guó)。
《開(kāi)羅宣言》對(duì)日本國(guó)構(gòu)成拘束力的法律邏輯構(gòu)造來(lái)自以下的模式:首先,條約不能拘束第三者是一項(xiàng)古老的國(guó)際法原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在吸納了該項(xiàng)規(guī)則的基礎(chǔ)上也規(guī)定了例外原則。其第35條規(guī)定:“如條約當(dāng)事國(guó)有意以條約之一項(xiàng)規(guī)定作為確立一項(xiàng)義務(wù)之方法,且該項(xiàng)義務(wù)一經(jīng)第三國(guó)以書(shū)面明示接受,則該第三國(guó)即因此項(xiàng)規(guī)定而負(fù)有義務(wù)。”1945年7月26日,三大同盟國(guó)發(fā)表對(duì)日最后通牒式的《波茨坦公告》。該公告第8條規(guī)定:“《開(kāi)羅宣言》的條件必須實(shí)施,日本主權(quán)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guó)及由我等指定的諸小島。”是年,蘇聯(lián)于8月8日對(duì)日宣戰(zhàn)后加入該公告。1945年9月2日日本簽署了無(wú)條件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書(shū)面投降書(shū)。一經(jīng)日本書(shū)面明示接受《波茨坦公告》,該公告以及《開(kāi)羅宣言》對(duì)日本國(guó)就產(chǎn)生法律拘束力。
從另一個(gè)角度來(lái)看,四大國(guó)向日本提出了包含《開(kāi)羅宣言》的諸條件必須實(shí)施的《波茨坦公告》,其行為本身就可看作法律上的要約,而日本的投降書(shū)則是承諾。國(guó)際法從來(lái)沒(méi)有規(guī)定過(guò)條約必須在一張書(shū)面文件中完成,可見(jiàn),日本也是當(dāng)事國(guó)。至此,《波茨坦公告》包括《開(kāi)羅宣言》與《日本投降書(shū)》形成了國(guó)際法上權(quán)利與義務(wù)的協(xié)議關(guān)系,構(gòu)成了限制日本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法律基礎(chǔ)。《開(kāi)羅宣言》從一開(kāi)始就是不折不扣的國(guó)際條約,只是拘束的主體有所變化,對(duì)日本的拘束力產(chǎn)生于日本投降書(shū)遞交之日起。
(二)剝奪日本固有領(lǐng)土以外的攫取之土地
近代國(guó)際法并不禁止主權(quán)國(guó)家行使無(wú)差別的開(kāi)戰(zhàn)權(quán),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qiáng)對(duì)外殖民擴(kuò)張也一直沒(méi)有停止。近代國(guó)際法的游戲規(guī)則是,軍事勝出的殖民擴(kuò)張國(guó)家就擁有吞并戰(zhàn)敗國(guó)的領(lǐng)土主權(quán)或者是割讓其領(lǐng)土。
針對(duì)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后獲勝的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對(duì)戰(zhàn)敗的帝國(guó)主義國(guó)家所占有的殖民地進(jìn)行瓜分的凡爾賽和會(huì),新興的社會(huì)主義國(guó)家蘇聯(lián)的領(lǐng)袖列寧就提出了“不割地、不賠償”口號(hào)。同時(shí),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慘禍徹底警醒了世界人民,要維護(hù)世界和平、防止慘禍重演,就必須鏟除殖民帝國(guó)主義的土壤,就必須在國(guó)際法上明確武力掠奪他國(guó)領(lǐng)土的非法性和無(wú)效性。為此,三大同盟國(guó)在1943年《開(kāi)羅宣言》公開(kāi)宣布:“我三大盟國(guó)此次進(jìn)行戰(zhàn)爭(zhēng)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懲罰日本之侵略,三國(guó)決不為自己圖利,亦無(wú)拓展領(lǐng)土之意思。三國(guó)之宗旨在剝奪日本……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攫取之土地,亦務(wù)將日本驅(qū)逐出境。” 〔15 〕這表明即使日本戰(zhàn)敗,同盟國(guó)也不會(huì)剝奪日本固有的領(lǐng)土。剝奪的僅限于“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攫取之土地”。
從列寧提出的理論到二戰(zhàn)中同盟國(guó)的實(shí)踐,可以看到,同盟國(guó)從根本上否定了國(guó)家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動(dòng)因,改變了傳統(tǒng)國(guó)際法中關(guān)于征服、滅亡的規(guī)則,為徹底禁止戰(zhàn)爭(zhēng),實(shí)現(xiàn)世界和平創(chuàng)建了必要的新規(guī)范。由此可見(jiàn),這場(chǎng)反法西斯的戰(zhàn)爭(zhēng)是人類(lèi)歷史上真正意義上的正義戰(zhàn)爭(zhēng),它通過(guò)對(duì)近代國(guó)際法的改造,創(chuàng)制了現(xiàn)代國(guó)際法的新規(guī)范,鏟除了帝國(guó)主義殖民擴(kuò)張、吞并他國(guó)領(lǐng)土的誘因。《開(kāi)羅宣言》是人類(lèi)進(jìn)步和國(guó)際法進(jìn)步的重要體現(xiàn)。
在剝奪“日本以武力或貪欲攫取之土地”對(duì)象上,《開(kāi)羅宣言》規(guī)定“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guó)之領(lǐng)土,例如滿洲、臺(tái)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華民國(guó)(all the territories Japan has stolen from the Chinese, such as Manchuria,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shall be restored to the Republic of China)”,“日本亦將被逐出于其以暴力或貪欲所攫取之所有土地(Japan will also be expelled from all other territories which she has taken by violence and greed)”。就意味著,日本通過(guò)武力以《馬關(guān)條約》從中國(guó)攫取的中國(guó)東北、臺(tái)灣及其附屬島嶼當(dāng)然要回歸中國(guó),同時(shí)也是否定日本繼續(xù)攫取琉球領(lǐng)土的法律依據(jù)。總之,這些條款意味著,其他非日本的固有領(lǐng)土均須從日本剝離。
(三)審判戰(zhàn)爭(zhēng)罪犯
如果只是保留戰(zhàn)敗國(guó)的主權(quán)而不懲罰戰(zhàn)敗國(guó),世界和平的秩序仍然無(wú)法建立。懲罰罪犯取代傳統(tǒng)的吞并戰(zhàn)敗國(guó)領(lǐng)土的設(shè)想此后得到了強(qiáng)調(diào)。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guó)在波茨坦會(huì)議期間發(fā)表《波茨坦公告》,蘇聯(lián)于8月8日對(duì)日宣戰(zhàn)后加入該公告。
四大國(guó)將《開(kāi)羅宣言》諸項(xiàng)條件納入《波茨坦公告》明確規(guī)定必須實(shí)現(xiàn)。《開(kāi)羅宣言》與《波茨坦公告》兩者相互聯(lián)系,前者是原則大綱,后者是相對(duì)具體化地要求日本無(wú)條件接受的條件。
《波茨坦公告》重申《開(kāi)羅宣言》提出的條款實(shí)施,日本投降后,其主權(quán)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guó)及由盟國(guó)指定的島嶼;軍隊(duì)完全解除武裝;戰(zhàn)犯交付審判;日本政府必須尊重人權(quán),保障宗教、言論和思想自由;不得保有可供重新武裝作戰(zhàn)的工業(yè)。日本政府應(yīng)立即宣布所有武裝部隊(duì)無(wú)條件投降。尤為重要的是《波茨坦公告》提出了要審判日本戰(zhàn)犯。戰(zhàn)后同盟國(guó)最高司令部頒布設(shè)立了“遠(yuǎn)東國(guó)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zhàn)爭(zhēng)罪犯。
日本方面不斷有人鼓吹,遠(yuǎn)東軍事法庭的審判是事后法違反國(guó)際法、違反正義原則。如果按照傳統(tǒng)國(guó)際法規(guī)范懲罰日本,其結(jié)果不難推斷,日本不得不以割地賠償求得殘存,或者日本直接滅亡。那么,在今天的世界地圖中就沒(méi)有日本的名字。
國(guó)際法的效力依據(jù)來(lái)自國(guó)際法主體的共同的協(xié)調(diào)意志。事實(shí)上,遠(yuǎn)東國(guó)際軍事法庭以戰(zhàn)爭(zhēng)罪、反和平罪和反人道罪起訴和審判戰(zhàn)犯是同盟國(guó)與日本共同的創(chuàng)制。“舊金山和約”第11條寫(xiě)明,日本明確地接受遠(yuǎn)東國(guó)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nèi)或境外之盟國(guó)戰(zhàn)犯法庭之判決。“舊金山和約”是日本國(guó)會(huì)批準(zhǔn)的“和約”,當(dāng)然反映了日本的國(guó)家意志。可見(jiàn),從法律效力的依據(jù)來(lái)看,破壞和平罪是同盟國(guó)與戰(zhàn)敗國(guó)日本共同意志之下創(chuàng)立的。
“法無(wú)明文規(guī)定不為罪”的格言并非對(duì)主權(quán)的限制,而是關(guān)于正義的一般原則。“罪刑法定”的一個(gè)基本要求是國(guó)民能夠根據(jù)刑法規(guī)范預(yù)測(cè)自己行為的后果,從而明確地知道何種行為被刑法所禁止而不當(dāng)為。侵略行為在被告人實(shí)施之前就被禁止。被告人既然應(yīng)當(dāng)知道,違反交戰(zhàn)法規(guī)禁止性規(guī)范者要被處以懲罰,那么也就應(yīng)當(dāng)預(yù)見(jiàn)違反《巴黎非戰(zhàn)公約》禁止性規(guī)范者也將會(huì)受到懲處。懲處被告并非遠(yuǎn)離公正,如果允許其錯(cuò)誤行為逍遙法外才是不公正的。
按照近代(傳統(tǒng))國(guó)際法規(guī)則處理戰(zhàn)敗國(guó),雖然不懲治侵略罪罪行,但是當(dāng)然要吞并戰(zhàn)敗國(guó),鼓吹按照近代國(guó)際法規(guī)則處理的話,日本必然面臨著以喪失主權(quán)國(guó)家為代價(jià)。日本既想要保存國(guó)體,又想要避免應(yīng)有懲罰,那么世界和平和安全、國(guó)際正義就難以持續(xù)存在。戰(zhàn)后建立國(guó)際軍事法庭審判破壞和平罪的實(shí)踐是在國(guó)際法禁止性規(guī)范、違反國(guó)際法應(yīng)當(dāng)承擔(dān)國(guó)家責(zé)任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造性地對(duì)發(fā)動(dòng)侵略罪行的個(gè)人判處了侵略罪,這是對(duì)國(guó)際法的新貢獻(xiàn)。
(四)限制日本戰(zhàn)爭(zhēng)權(quán)
戰(zhàn)后,因?yàn)槿毡拘聭椃ú莅甘亲鳛橥藝?guó)最高司令部的麥克阿瑟提出的,日本人往往視日本憲法為“麥克阿瑟憲法”。事實(shí)上,日本憲法的效力依據(jù)來(lái)自于《日本投降書(shū)》對(duì)《中蘇美英四國(guó)對(duì)日本乞降照會(huì)的復(fù)文》的無(wú)條件承認(rèn)。
首先,中、美、英三國(guó)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在1945年7月26日公布后,日本于同年8月10日發(fā)來(lái)乞降照會(huì)并詢(xún)問(wèn)公告確切涵義。對(duì)此,8月11日中、蘇、美、英四國(guó)以四大國(guó)名義對(duì)日本乞降照會(huì)的復(fù)文中言明:“自投降之時(shí)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統(tǒng)治國(guó)家之權(quán)力,即須聽(tīng)從盟國(guó)最高司令官,該司令官將采取其認(rèn)為適當(dāng)之步驟以實(shí)施投降條款。” 〔16 〕
1945年9月2日,由日本外務(wù)大臣重光葵和參謀總長(zhǎng)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簽訂并向同盟國(guó)九國(guó)受降代表麥克阿瑟等所呈遞的日本投降文書(shū)完全接受了《波茨坦公告》的條款。投降文書(shū)第6項(xiàng)言明:“余等為天皇、日本政府及其后繼者承允忠實(shí)履行波茨坦宣言之條款,發(fā)布為實(shí)施該公告之聯(lián)合國(guó)最高司令官或其他同盟國(guó)指令代表所要求之一切命令及一切措置。” 〔17 〕第8項(xiàng)承諾:“天皇及日本國(guó)政府統(tǒng)治國(guó)家之權(quán)力,應(yīng)置于為實(shí)施投降條款而采取其所認(rèn)為適當(dāng)步驟之同盟國(guó)最高司令官之下。” 〔18 〕
因此,根據(jù)《波茨坦公告》、《中蘇美英四國(guó)對(duì)日本乞降照會(huì)的復(fù)文》以及《日本投降書(shū)》,日本憲法第9條規(guī)定的放棄戰(zhàn)爭(zhēng)權(quán),其效力依據(jù)絕對(duì)不是美國(guó)單方面的,更不是出自麥克阿瑟的,而是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四大國(guó)的授權(quán)。今天日本要修改憲法第9條當(dāng)然應(yīng)當(dāng)征得包括中國(guó)在內(nèi)的四大國(guó)的同意。毋庸置疑,解禁集體自衛(wèi)權(quán)是否符合憲法的問(wèn)題不是日本國(guó)單方面就可以定調(diào)的。
目前國(guó)內(nèi)也有學(xué)者在積極地傳播著一種觀念:日本要成為一個(gè)“普通的”國(guó)家是正常合理的訴求,修改日本憲法中限制日本戰(zhàn)爭(zhēng)權(quán)的“憲法九條”是遲早的事。這種觀點(diǎn)抹殺了戰(zhàn)勝?lài)?guó)對(duì)戰(zhàn)敗國(guó)主權(quán)限制的權(quán)利與義務(wù)關(guān)系。
三、中日邦交協(xié)議是主導(dǎo)中日關(guān)系政治格局的基礎(chǔ)
(一)“舊金山和約”的法律地位
在朝鮮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的背景下,美國(guó)為拉攏日本,于1951年9月8日在美國(guó)舊金山召開(kāi)會(huì)議,使得包括日本在內(nèi)的48個(gè)交戰(zhàn)國(guó)達(dá)成了“舊金山和約”,中國(guó)被排除在外,蘇聯(lián)出席了會(huì)議,但是拒絕簽署該和約。在未經(jīng)中國(guó)同意的情況下,“舊金山和約”將《開(kāi)羅宣言》明確規(guī)定的“在使日本所竊取于中國(guó)之領(lǐng)土,例如滿洲、臺(tái)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guó)”,改為“日本放棄對(duì)臺(tái)灣及澎湖列島的一切權(quán)利、權(quán)利根據(jù)及要求”(“舊金山和約”第2條第2款)。“舊金山和約”的這項(xiàng)規(guī)定,反映出美、日勾結(jié),企圖使臺(tái)灣處于地位“未定”狀態(tài)。此外,未經(jīng)四大國(guó)討論和授權(quán),“舊金山和約”第3條便將北緯29度以南的島嶼交由美軍一方托管,這為美國(guó)此后非法將中國(guó)釣魚(yú)島劃歸琉球管轄范圍提供了機(jī)遇。
相反的觀點(diǎn)認(rèn)為,《開(kāi)羅宣言》、《波茨坦公告》僅僅是“停戰(zhàn)文件”,投降文件并非是戰(zhàn)爭(zhēng)的終結(jié)。它必須要等待和平條約的締結(jié)。〔19 〕由于這是首次以具有明確的國(guó)際法效力的條約來(lái)加以規(guī)定的,故臺(tái)灣自該和約1952年4月28日生效之日起就脫離了日本的主權(quán),所以日本自該日以后,喪失了對(duì)臺(tái)灣的領(lǐng)土的處分權(quán)。縱然1972年中日邦交時(shí)《中日聯(lián)合聲明》“處分”臺(tái)灣,但是因?yàn)榕_(tái)灣已經(jīng)不是日本領(lǐng)土,其處分為無(wú)效。〔20 〕
如果說(shuō)終結(jié)戰(zhàn)爭(zhēng)的和平條約效力高于停戰(zhàn)協(xié)定是一般規(guī)范,那么它的前提是以前后當(dāng)事國(guó)不變?yōu)闂l件的。有關(guān)條約的沖突規(guī)范集中地被匯總在《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59條,其規(guī)定:“任何條約于其全體當(dāng)事國(guó)就同一事項(xiàng)締結(jié)后訂條約,如果前后條約沖突,前一條約效力終止。”中國(guó)和蘇聯(lián)不是前后條約的當(dāng)事國(guó),因此“舊金山和約“優(yōu)先于停戰(zhàn)條約的說(shuō)辭是不能適用于中國(guó)和蘇聯(lián)(俄羅斯)的。
根據(jù)國(guó)際法,“舊金山和約”存在的問(wèn)題很多。首先它違反了“絕不單獨(dú)地與敵國(guó)進(jìn)行停戰(zhàn)、媾和”的《聯(lián)合國(guó)家宣言》。1942年1月1日,為共同抗擊德國(guó)、日本、意大利的法西斯侵略,26個(gè)國(guó)家在華盛頓公布了《聯(lián)合國(guó)家宣言》。該宣言約定對(duì)敵國(guó)進(jìn)行全面的決戰(zhàn),同時(shí)約定,“每一政府各自保證與本宣言簽字國(guó)政府合作,并不與敵國(guó)締結(jié)單獨(dú)停戰(zhàn)協(xié)議或和約”,〔21 〕中、美、蘇、英均是《聯(lián)合國(guó)家宣言》的締結(jié)國(guó)。朝鮮戰(zhàn)爭(zhēng)爆發(fā)后,西方陣營(yíng)為拉攏日本成為西方陣營(yíng)的橋頭堡,于1951年締結(jié)“舊金山和約”,使得日本再次遇到了免遭嚴(yán)厲懲罰的機(jī)會(huì)。《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0條規(guī)定:“遇條約訂明須不違反先訂或后訂條約或不得視為與先訂或后訂條約不合時(shí),該先訂或后訂條約之規(guī)定應(yīng)居優(yōu)先。”可見(jiàn)在四大國(guó)之間《聯(lián)合國(guó)家宣言》的效力優(yōu)先于“舊金山和約”。
同時(shí),“舊金山和約”違反了“條約不拘束第三國(guó)原則”。這項(xiàng)原則是一項(xiàng)古老的、公認(rèn)的原則。《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4條也明確規(guī)定:“條約非經(jīng)第三國(guó)同意,不為該國(guó)創(chuàng)設(shè)義務(wù)或權(quán)利。”因此,日本未經(jīng)中國(guó)同意,尤其是在中國(guó)缺席的情況下處分承諾歸還中國(guó)的領(lǐng)土臺(tái)灣,當(dāng)屬背信地、嚴(yán)重地違反國(guó)際法規(guī)定的條約必須履行的古老規(guī)則。
國(guó)內(nèi)學(xué)術(shù)界主流觀點(diǎn)認(rèn)為,“舊金山和約”是非法的、無(wú)效的。正如1951年9月18日,周恩來(lái)嚴(yán)正聲明:“舊金山對(duì)日和約由于沒(méi)有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參加準(zhǔn)備、擬制和簽訂,中央人民政府認(rèn)為是非法的,無(wú)效的,因而是絕對(duì)不能承認(rèn)的。” 〔22 〕
也有學(xué)者認(rèn)為,“舊金山和約”違背了《聯(lián)合國(guó)家宣言》規(guī)定的同盟國(guó)不能單獨(dú)地與敵國(guó)締結(jié)和約的規(guī)定,學(xué)界可以認(rèn)定其違法,但是國(guó)際法并不禁止國(guó)家就同一事項(xiàng)在前后條約中訂立相互矛盾的條款,因此,不能就此判定“舊金山和約”為無(wú)效。
實(shí)際上,基于朝鮮戰(zhàn)爭(zhēng)的原因,美國(guó)具有扶植和壓制日本的雙重性。因此,在“舊金山和約”中存在符合四大國(guó)利益的條款。如確認(rèn)雅爾塔體系勝利成果的第11條中,日本國(guó)重申了“接受規(guī)定遠(yuǎn)東國(guó)際軍事法庭與其他在日本境內(nèi)或境外之盟國(guó)戰(zhàn)罪法庭之判決……”另一方面,在“舊金山和約”中也有明顯超越其權(quán)限的無(wú)效條款。例如第2條e款所謂的“日本放棄對(duì)南威島及西沙群島之一切權(quán)利、權(quán)利根據(jù)與要求。”對(duì)此,1951年8月15日,周恩來(lái)在發(fā)表的“關(guān)于美英對(duì)日和約草案及舊金山會(huì)議的聲明”中就指出:“草案又故意規(guī)定日本放棄對(duì)南威島和西沙群島的一切權(quán)利而亦不提歸還主權(quán)問(wèn)題。實(shí)際上,西沙群島和南威島正如整個(gè)南沙群島及中沙群島、東沙群島一樣,一向?yàn)橹袊?guó)領(lǐng)土,在日本帝國(guó)主義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時(shí)雖曾一度淪陷,但日本投降后已為當(dāng)時(shí)中國(guó)政府全部接收……” 〔23 〕尤為嚴(yán)重的是,根據(jù)國(guó)際法,軍事占領(lǐng)并不導(dǎo)致領(lǐng)土所有權(quán)的轉(zhuǎn)移,而日本侵華期間對(duì)西沙群島和南威島的軍事占領(lǐng)并不會(huì)導(dǎo)致日本對(duì)該島嶼產(chǎn)生所有權(quán),沒(méi)有所有權(quán)何來(lái)“放棄”之說(shuō)?可見(jiàn),該條款實(shí)質(zhì)上是超越了日本國(guó)主權(quán)權(quán)限,根據(jù)《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6條之規(guī)定,締約國(guó)超出締約權(quán)限所締結(jié)之條約是無(wú)效的條約款。
筆者以為籠統(tǒng)地將“舊金山和約”全盤(pán)否定或全盤(pán)肯定均為形而上學(xué)的。根據(jù)《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35條規(guī)定,條約當(dāng)事國(guó)有意以條約之一項(xiàng)規(guī)定為第三國(guó)創(chuàng)設(shè)義務(wù),非經(jīng)第三國(guó)以書(shū)面明示接受,不對(duì)該第三國(guó)產(chǎn)生義務(wù)。第36條規(guī)定,如條約當(dāng)事國(guó)有意以條約之一項(xiàng)規(guī)定給第三國(guó)賦予一項(xiàng)權(quán)利,若該第三國(guó)倘無(wú)相反之表示,應(yīng)推定其表示同意。因此,中國(guó)對(duì)于“舊金山和約”應(yīng)采取的立場(chǎng)是,凡是“舊金山和約”中違背《開(kāi)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約定,非法處分中國(guó)領(lǐng)土主權(quán)的條款規(guī)定是無(wú)效條款。凡是賦予第三國(guó)權(quán)利的(例如舊金山和約第11條),中國(guó)政府當(dāng)然有權(quán)援用之。這種將條約條款分離開(kāi)來(lái)進(jìn)行認(rèn)定的方式也是符合《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44條規(guī)定的。
(二)所謂的“日華和約”的法律地位
1952年4月8日,日本與臺(tái)灣當(dāng)局簽署了所謂的“日華和約”。從國(guó)際法的角度看,這個(gè)“和約”不是兩個(gè)主權(quán)國(guó)家之間的協(xié)議,臺(tái)灣當(dāng)局不是代表全中國(guó)人民的合法政府,因而是非法的、無(wú)效的。該“和約”第2條寫(xiě)道:“茲承認(rèn)依照公歷1951年9月8日在美利堅(jiān)合眾國(guó)舊金山市簽訂之對(duì)日和平條約第2條,日本業(yè)已放棄對(duì)于臺(tái)灣及澎湖列島以及南沙群島及西沙群島的一切權(quán)利、權(quán)利名義與要求”,等于認(rèn)可了臺(tái)灣“無(wú)主地位”。當(dāng)時(shí)的臺(tái)灣當(dāng)局對(duì)“和約”所涉及諸多損害中國(guó)權(quán)益的條款內(nèi)容沒(méi)有提出異議,這也是日本為什么膽敢強(qiáng)硬地堅(jiān)持對(duì)釣魚(yú)島擁有主權(quán)的根本所在。〔24 〕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率領(lǐng)政府代表團(tuán)訪華。9月29日,周恩來(lái)總理和外交部長(zhǎng)姬鵬飛代表中國(guó)政府,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相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簽署發(fā)表了《中日聯(lián)合聲明》。〔25 〕《中日聯(lián)合聲明》表達(dá)了“復(fù)交三原則”。“復(fù)交三原則”的第一個(gè)原則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政府是中國(guó)唯一的合法政府,這一原則體現(xiàn)在《中日聯(lián)合聲明》中的第2項(xiàng),在中日兩國(guó)之間已經(jīng)不成為爭(zhēng)議。第二個(gè)原則即臺(tái)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領(lǐng)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臺(tái)灣問(wèn)題純屬中國(guó)內(nèi)政。對(duì)此,《中日聯(lián)合聲明》以第3項(xiàng)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政府重申:臺(tái)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領(lǐng)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guó)政府的這一立場(chǎng),并堅(jiān)持遵守《波茨坦公告》第8條的立場(chǎng)(《波茨坦公告》第8條:開(kāi)羅宣言諸條款必須履行)。”第三個(gè)原則是所謂“日華和約”是非法的、無(wú)效的,必須廢除。這一原則雖然沒(méi)有在《中日聯(lián)合聲明》明確記載,但是,該聲明的序言以及有關(guān)條款的內(nèi)涵已經(jīng)顯而易見(jiàn)地表明了中日兩國(guó)政府達(dá)成了“日華和約”是無(wú)效的共識(shí)。
1971年10月25日,聯(lián)合國(guó)大會(huì)通過(guò)了《恢復(fù)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在聯(lián)合國(guó)組織中的合法權(quán)利問(wèn)題》的2758號(hào)決議。〔26 〕所謂恢復(fù)(Restoration),意味具有溯及效力,它顯示了聯(lián)合國(guó)承認(rèn)自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成立之日起就當(dāng)然擁有合法的代表權(quán)。因此,臺(tái)灣當(dāng)局在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政府建立后,擅自以中國(guó)主權(quán)的身份所訂立的“日華和約”是無(wú)效的。
此后,1972年9月29日中日兩國(guó)政府發(fā)表的《中日聯(lián)合聲明》第3項(xiàng)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政府重申:臺(tái)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guó)領(lǐng)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guó)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guó)政府的這一立場(chǎng),并堅(jiān)持遵循波茨擔(dān)公告第8條的立場(chǎng)。”而《波茨擔(dān)公告》第8條則規(guī)定:“開(kāi)羅宣言之條件必須實(shí)施,而日本之主權(quán)必將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guó)及吾人所指定其他小島之內(nèi)。”1978年8月16日,中國(guó)全國(guó)人民代表大會(huì)常務(wù)委員會(huì)批準(zhǔn)了兩國(guó)外長(zhǎng)草簽的《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恢復(fù)中日邦交的級(jí)別得到提高。該和平友好條約確認(rèn)了《中日聯(lián)合聲明》所確立的各項(xiàng)原則。根據(jù)《中日聯(lián)合聲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條約》規(guī)定可見(jiàn),中日邦交協(xié)議已然成為主導(dǎo)中日關(guān)系政治格局的基礎(chǔ)。
結(jié) 語(yǔ)
蘇聯(lián)解體,兩極格局結(jié)束,但這并不意味著雅爾塔體系隨之解體。宏觀上,從體系的力量中心來(lái)看,幾大力量的地位和角色未變;特別是體系的主要矛盾依舊。因?yàn)榫S系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勝利成果的國(guó)際組織聯(lián)合國(guó)依然在發(fā)揮作用,聯(lián)合國(guó)是雅爾塔體系的重要支柱。從另一方面而言,雅爾塔體系創(chuàng)建后局部的國(guó)際格局有了重大的變化。鑒于國(guó)際體系是由戰(zhàn)勝?lài)?guó)之間以一系列影響戰(zhàn)后世界秩序的公報(bào)、議定書(shū)、協(xié)定等具有法律拘束力的國(guó)際法所固定下來(lái)的。同樣,國(guó)際體系的變動(dòng)或國(guó)際格局的重新組合,最終都是需要通過(guò)有拘束力的國(guó)際協(xié)議來(lái)確立并實(shí)施的。因此,研究《開(kāi)羅宣言》的歷史地位、法律效力、直面它與“舊金山和約”之間的效力沖突較之宏觀上強(qiáng)調(diào)雅爾塔體系具有更強(qiáng)的說(shuō)服力和可操作性。
“舊金山和約”體制或政治格局中的有些抵觸雅爾塔體系的、超越締約國(guó)權(quán)限的,應(yīng)當(dāng)被視為無(wú)效。《開(kāi)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日本投降書(shū)》等國(guó)際政治、法律文件是雅爾塔體系中重新劃定日本疆界及其被占領(lǐng)地區(qū)的邊界的重要協(xié)議,構(gòu)成了建立戰(zhàn)后亞太地區(qū)秩序的國(guó)際性文件框架,明確了日本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侵占別國(guó)領(lǐng)土行為的非法性,確立了中國(guó)對(duì)臺(tái)灣及其附屬島嶼等的主權(quán),是二戰(zhàn)后維護(hù)世界和平秩序的重要保證。無(wú)論國(guó)際體系或國(guó)際格局的如何變化,中日邦交協(xié)議已然成為主導(dǎo)中日關(guān)系政治格局的基礎(chǔ),其中重申的《開(kāi)羅宣言》也是釣魚(yú)島歸屬中國(guó)的重要法律依據(jù),日本對(duì)此負(fù)有條約義務(wù)。特別是近10多年來(lái),日本右翼勢(shì)力不斷抬頭,企圖以“舊金山和約”體制否定《開(kāi)羅宣言》、《波茨坦公告》為基礎(chǔ)的戰(zhàn)后亞太國(guó)際秩序,為日本重新成為所謂“正常國(guó)家”鳴鑼開(kāi)道;而美國(guó)也有意圖背離《開(kāi)羅宣言》的基本精神,重新扶持日本右翼勢(shì)力,推行美國(guó)在亞洲的所謂“再平衡”戰(zhàn)略。因此,有必要深入解讀《開(kāi)羅宣言》的法律內(nèi)涵以及蘊(yùn)含其中的歷史正當(dāng)性、進(jìn)步性,解釋《開(kāi)羅宣言》在當(dāng)代國(guó)際社會(huì)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