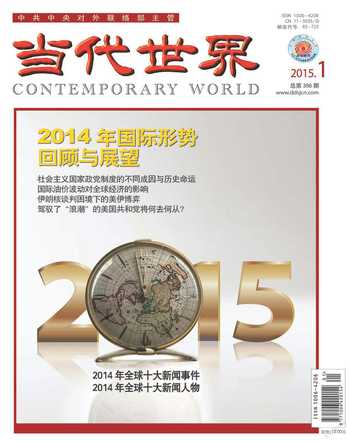解決阿富汗問題:地區國家與地區多邊機制的作用
張力

自冷戰結束以來,地區多邊機制在解決本地區的危機和沖突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阿富汗的情況并不例外。自美國發動阿富汗反恐戰爭以來,國際社會已舉行多次阿富汗問題會議,就阿富汗的穩定與重建、地區安全以及協調各方努力達成諸多共識。目前,鑒于軍事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前景黯淡和國際聯軍撤離在即,地區多邊合作在國際社會的政策選項中受到重視。本文探討地區國家、地區多邊機制在當前和未來阿富汗問題上的作用及面臨的挑戰。
地區層面的參與動力和影響
隨著阿富汗重建進程的啟動,阿富汗的鄰國、地區國家和地區多邊機制的作用得以突顯。與阿富汗接壤的鄰國包括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巴基斯坦和中國,主要地緣周邊國家包括印度、俄羅斯、土耳其及中亞地區其他國家。鄰國及周邊國家與阿富汗存在著緊密的地緣、宗教、民族與歷史淵源關聯。早在2002年12月,阿富汗便與六個鄰國共同簽署《喀布爾友好鄰邦宣言》,各鄰邦承諾充分尊重阿富汗的主權與領土完整,支持阿和平與重建努力。此后,阿富汗與各鄰國之間的合作不斷擴大到貿易、投資、邊界管理和打擊毒品走私等領域。在近年來解決阿富汗問題的一系列國際高峰會議上,如何發揮地區鄰國及周邊國家的作用、促進阿富汗的穩定與重建一直是引起各方關切的重要議題。
與阿富汗問題相關的地區機制(準機制)包括上海合作組織、“伊斯坦布爾進程”(也稱“亞洲中心”國家倡議)、亞洲相互協作與信任措施會議(“亞信會議”)、南亞區域合作聯盟(“南盟”)、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集安組織”)、經濟合作組織和伊斯蘭會議組織。
上合組織對維持阿富汗及地區穩定的重要性近年來受到普遍關注。2005年11月,上合組織成立“阿富汗問題聯絡小組”,為參與阿富汗問題的解決搭建了工作平臺。上合組織于2009年3月在莫斯科舉行首次阿富汗問題會議,阿總統卡爾扎伊應邀與會。上合組織意識到阿富汗問題與地區安全的密切關聯,2010年6月塔什干峰會《共同宣言》提出:“作為維護安全的決定性因素,實現阿富汗和平穩定有助于整個地區社會經濟持續發展。”[1]在2012年6月上合組織北京峰會上,阿富汗被接納為觀察員國。顯而易見,阿富汗成為上合組織觀察員國具有重大意義,表明上合組織日益重視阿富汗問題,并為協助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更直接的政治渠道。2014年9月,上合組織杜尚別元首理事會批準《給予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地位程序》、《關于申請國加入上海合作組織義務的備忘錄范本》修訂案兩份重要文件,從法律上為機制擴容創造了條件。但阿富汗目前尚未正式提交申請,該國能否在不久將來成為上合組織的正式成員仍需要觀察。
“伊斯坦布爾進程”是推動解決阿富汗問題的另一重要地區平臺。2010年1月26日,阿富汗問題地區峰會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爾舉行,稱為“伊斯坦布爾進程”。“進程”將加強地區安全合作以推動解決阿富汗問題作為主旨,支持阿富汗實現國內和解和重新融合,支持聯合國在阿富汗問題上發揮協調作用,呼吁各國在援助阿富汗的同時尊重其主權和領土完整,相互之間不干涉內政、睦鄰友好與和平共處,并提出打擊恐怖主義和毒品走私,防止武器非法跨境流通,建設和發展地區貿易、交通和能源走廊等倡議。
中國是“伊斯坦布爾進程”的支持者和參與方。2014年10月底,在繼伊斯坦布爾、喀布爾和阿拉木圖之后,北京承辦了“進程”第四次外長會議,這是中國首次舉辦有關阿富汗問題的重大國際性會議。會議涉及與阿富汗問題相關的眾多議題,強調地區國家與國際社會加強共識與合作,推動阿富汗實現持久和平、可持續安全與經濟發展。隨后發表的《北京宣言》表明各方就阿富汗問題達成了廣泛的地區共識。此外,本次會議在幫助推進阿國內實現包容性政治和解、提高阿富汗安全能力建設、擴大阿富汗參與地區貿易和經濟聯通等方面做出了具體承諾。[2]
“亞信會議”是亞洲國家在安全領域加強合作、增強互信的地區多邊論壇,有潛力在阿富汗問題上發揮積極影響。于2014年5月在上海舉行的“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上,阿總統卡爾扎伊表示,希望“亞信會議”能促進阿富汗的和平與穩定。卡爾扎伊還對會議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倡議作出積極回應,相信該計劃將為阿富汗和中國深化與亞歐各國間的合作、繁榮經濟開辟新的廣闊空間。[3]體現“亞信會議”成員國共識的《上海宣言》強調:恐怖主義、暴力極端主義和毒品是對阿富汗及本地區內外的安全與穩定構成的嚴重威脅;推動阿富汗、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之間的密切合作以應對恐怖主義挑戰,包括摧毀恐怖分子庇護所、切斷恐怖主義資金來源和技術支持、幫助阿打擊非法制販毒品和推廣替代種植等。[4]
此外,南盟、經濟合作組織、伊斯蘭會議組織和集安組織等也在一定程度上嘗試對阿富汗問題產生影響。
地區國家的制約因素
盡管地區國家、地區多邊機制普遍支持阿富汗實現穩定,不斷加強與阿富汗的接觸,并嘗試在解決阿富汗問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但這些國家和多邊機制也面臨著不容忽視的制約和局限,各方是否已真正做好應對準備仍然存在不確定性。主要問題包括地區國家之間的利益差別和潛在沖突、深度參與的實際能力受限、與美國等域外大國的政策協調障礙、現有地區機制的功能缺失等。
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歷史糾結和利益沖突備受關注,被普遍認為是影響阿富汗穩定的主要地區障礙。印巴兩國都將阿富汗視為各自安全政策的重要關注點,相互的競爭是一種“零和博弈”。印度擔心阿富汗再次受巴基斯坦的左右,尤其是奉行類似塔利班時期敵視印度的政策,并一直指責巴基斯坦干涉阿國內政治和支持包括塔利班在內的武裝教派勢力,并力排印度在阿富汗的存在;而巴基斯坦則認為,阿富汗是巴抗衡印度的戰略縱深,如果聽任印度擴大在阿影響和阿富汗親印,無異將使自己陷入東西兩翼受敵的險境。
巴基斯坦是影響阿富汗局勢的重要國家,也是阿富汗穩定的主要利益攸關方。自“9·11”事件以來,巴基斯坦在阿富汗及南亞地區反恐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時也付出了高昂代價。由于地緣政治和歷史糾葛,現階段的巴阿雙邊關系存在某些制約。但阿富汗的穩定離不開巴基斯坦的全面合作卻是不爭的事實。另一方面,印度也是阿富汗和平穩定的重要利益攸關方。自2001年阿富汗重建啟動以來,印度與喀布爾一直保持密切合作,并向阿提供了20億美元的援助。在后塔利班時期,印度的這一姿態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巴基斯坦的影響。印度高度關切美國從阿撤軍,擔心局勢失控和塔利班卷土重來,更擔憂危機外溢將直接危害自身安全和利益。北約撤離無疑將促使印度進一步強化與阿富汗的關系。目前印度已著手培訓阿國家安全部隊,并替阿向俄羅斯付款購買軍事裝備。這些舉措降低了阿富汗在軍事援助上對美國和北約的依賴。
但印阿關系的提升也帶來了其他方面的問題,該地區原有的地緣政治平衡或將被改變。尤其隨著美巴“反恐”盟友關系的緊張和美國從阿撤軍,這一矛盾將更為突出。明顯的反映是近年來印度在阿富汗的存在日益受到嚴峻威脅。2008年7月和2009年10月,印度駐阿使館遭到武裝分子的襲擊,造成嚴重人員傷亡。2013年8月和2014年5月,印度駐賈拉巴巴德和赫拉特的兩個領事館再遭恐怖襲擊。盡管阿國內極端武裝組織聲稱對此負責,但印度仍懷疑巴軍方情報部門在背后的作用。[6]美國雖然贊揚印度對阿重建作出積極貢獻,但對印度擴大影響也不時表露出不安。據維基解密電文,美軍前駐阿最高指揮官麥克里斯特爾就曾警告稱,印度在阿富汗顯示實力可能刺激巴基斯坦,導致伊斯蘭堡在阿富汗或印度實施反制措施,從而加劇地區緊張。[7]奧巴馬政府也將如何平衡印巴在阿富汗的影響視為撤軍后善后措施的要務之一。盡管如此,也有跡象顯示,如果阿富汗持續不穩,巴基斯坦應對其國內安全挑戰的能力將嚴重削弱,巴基斯坦對這種利害關系的認知也不斷提高,有可能改變應對阿富汗局勢的慣有思維和政策,從而轉變角色增大對阿和平進程的促進作用。
伊朗與阿富汗存在一種微妙關系。一方面,德黑蘭與喀布爾之間一直保持著政治接觸,伊朗收容了大量阿富汗難民,并在阿西部地區承接了一些重要重建項目。但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著眼,伊朗支持阿富汗實現最終和平并非唯一的政策選項。伊朗雖然不希望塔利班勢力在阿國內卷土重來,但由于與美國關系緊張,也不反對利用塔利班的武裝活動繼續給美國制造麻煩。美分析人士認為:“德黑蘭在過去十年中從未中斷向塔利班某些分支組織提供援助,其目的并非是推翻喀布爾當局或幫助塔利班卷土重來,而是刻意讓美國感到頭疼,并利用這一戰術化解美國或以色列對伊核設施實施軍事打擊的潛在威脅。”[8]盡管美國從阿撤軍和美伊關系逐步解凍有可能減少伊朗對阿境內武裝組織的支持,但伊朗可能會繼續利用阿富汗問題以緩解來自美國的戰略壓力。
此外,作為重要地區國家,中亞鄰國和俄羅斯也因利益差別難以在阿富汗及周邊安全問題上保持協調。例如,將北方運輸線(在阿富汗反恐戰爭期間,由土庫曼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替代巴基斯坦為阿富汗提供后勤保障通道)作為未來地區貿易和運輸通道發展模式的設想遭到極大爭議。俄羅斯為阻止美國擴大地緣戰略影響,極力推動加強集安組織和組建快速反應部隊。但烏茲別克斯坦則對俄羅斯的動議保持警惕,反對快速軍力部署的提議,擔心其成為外部干預其內政的工具,烏甚至在2012年6月宣布退出集安組織。有觀察家注意到,烏茲別克斯坦甚至對任何將非阿富汗直接鄰邦的國家納入其中的地區機制都懷有戒心。[9]此外,阿富汗的中亞鄰國自身面臨日益增大的極端主義威脅,對阿富汗問題的主要安全關注點多局限于防范危機外溢損害自身。并且中亞國家的經濟現狀也使它們難以向阿提供更多的援助。
“安全真空”與
地區機制介入的局限
地區國家和地區組織是否有意愿和能力填補因國際聯軍撤離阿富汗留下的“安全真空”更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2009年,美國及其北約盟國的領導人曾向中國、印度試探派遣軍隊參加阿境內國際聯軍行動的可能性,但中、印均明確排除了派兵可能。近年來,阿富汗本土安全力量雖不斷增強,但戰斗力仍受到普遍質疑。隨著北約向阿國家安全部隊全面移交安全責任,阿政府軍的傷亡率近期已迅速上升。2014年后美國將依據《美阿雙邊安全協議》(BSA)繼續留駐部分軍力,但其任務主要限于培訓、援助與反恐特種行動,最終撤離僅是時間問題。這一局勢引發了有關地區國家如何在阿境內直接發揮安全作用的討論,甚至也有組建地區多邊安全部隊(MN-RSF)以接替即將撤離的國際聯軍的建議。
然而,事實上,地區國家以多邊方式從軍事上介入的可行性極小。在周邊國家中,印度對直接介入阿國內戰事缺少興趣,政策上極為謹慎。印度擴大對阿富汗的介入將引發巴基斯坦的激烈反應,不利于整個地區的穩定。因此,盡管印度對阿提供援助、培訓和部分裝備,但拒絕阿富汗政府索取重武器的要求。巴基斯坦、伊朗則受地區政治因素的局限,若在阿境內部署軍隊勢必引起阿境內外各方敏感。2001年底波恩會議討論聯合國授權組建多國聯軍時便未考慮巴基斯坦和伊朗參與。這一理由目前似乎依然存在。喀布爾當局也高度警惕巴基斯坦和伊朗干預其國內事務,不太可能接受兩國在其境內部署軍隊。中亞各國則受自身的局限,擔心直接介入將加劇本土的極端主義威脅,并對前蘇聯時期在阿遭受軍事挫折記憶猶新。并且,塔吉克人、烏茲別克人、土庫曼人是中亞國家與阿富汗的跨境民族,這些國家向阿派兵將面對來自阿主體民族普什圖人的阻力。[10]俄羅斯盡管表示將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邊界重新布防以降低因北約撤軍帶來的安全風險,但不可能參與在阿境內的任何軍事行動,這從俄目前對當年阿富汗戰爭的反思和對外國軍隊2014年繼續在阿部署的激烈反對立場可窺一斑。[11]
在北約撤軍后如何應對阿富汗的安全穩定問題上,現有地區多邊機制存在某些明顯的缺陷和局限。以上合組織為例。上合組織日益重視阿富汗問題固然是件好事,參與解決阿富汗問題也可提升機制的國際聲望,但從現狀看,上合組織處理阿富汗問題的實際能力與新近提出深化與阿富汗接觸的承諾之間還有較大距離。有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和俄羅斯對上合組織的政策各有倚重,俄羅斯的興趣主要是增強該機制的安全功能和建設共享的軍事合作平臺,但中國更看重其經濟功能和促進地區貿易自由化。[12]也有學者認為,上合組織缺乏解決阿富汗問題所需的能力與國際影響力,因此不會充當主導力量。[13]事實上,與作為整體的協調作用相比,上合組織多數成員國仍傾向于通過雙邊關系與阿富汗接觸,對多邊參與的熱度有限。從總體上看,上合組織與阿富汗的實質性接觸尚有待加強,其作為整體應對阿富汗及地區安全危機的功能和效果也有待進一步驗證。
除上合組織外,其他地區多邊機制在影響阿富汗問題上也存在顯著的局限。“伊斯坦布爾進程”為推動阿富汗的穩定與重建設立了若干機構,發表多次聯合聲明并有明確義務承諾,但至今并未取得令人矚目的具體成效。而且,地區國家多不愿向阿富汗提供軍事方面的支持。正如有分析指出,即使“進程”可能取得某些具體進展,但相關國家會避開向阿富汗提供它現階段最需要的軍事援助。[14]南盟則受印巴對立的掣肘,其建設性地影響阿富汗問題的能力有限。
結???語
綜上所述,隨著美國及其北約盟國2014年底從阿富汗撤出戰斗部隊,地區國家、地區多邊機制發揮更大作用已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盡管存在多種制約因素甚至可能出現“安全陷阱”,但基于利益和責任,建設性地擴大介入應是必要的政策選擇。作為地區國家和崛起中大國,中國是阿富汗問題地區合作的支持者和推動方。除積極參與全球和地區層面的各種努力并提出重要主張外,中國近年來發起有巴基斯坦、印度、俄羅斯與阿富汗參加的多次阿富汗問題三邊對話,推動阿富汗與巴基斯坦雙邊對話,并與巴、印、俄等利益攸關國家分別舉行雙邊對話。尤其是中國作為東道國在2014年10月底承辦“伊斯坦布爾進程”第四次部長級會議,為推動地區國家致力于阿富汗的和平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受到國際社會的高度贊賞。誠然,中國具備某些影響阿富汗局勢走向的條件和能力,國際社會各方也出于不同考慮期待中國發揮更大作用。但也須看到,中國在奉行積極接觸政策、應對地區安全挑戰的同時,應充分權衡利弊得失和核準自己的政策目標。從現狀和前景著眼,中國應繼續推動地區多邊機制為解決阿富汗問題發揮更大作用,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同時應有應對局勢演變可能帶來的安全挑戰的準備,保障在整個地區的戰略利益。
(作者系四川大學南亞研究所教授)
(責任編輯:張凱)
[1]?《上合組織形成完善的擴員機制》,載《南方都市報》,http://news.sina.com.cn/s/2010-06-12/050417647477s.shtml(上網時間:2010年6月12日)
[2]?《阿富汗問題伊斯坦布爾進程北京宣言》,http://world.huanqiu.com/article/2014-11/5187369.html(上網時間:2014年10月31日)
[3]?《卡爾扎伊:期望亞信會議促進阿富汗和平與穩定》,http://gb.cri.cn/42071/2014/05/19/7311s4546865.htm(上網時間:2014年5月19日)
[4]?《亞信會議第四次峰會上海宣言》,http://baike.baidu.com/view/13212745.htm?fr=aladdin(上網時間:2014年5月21日)
[5]?“India?blames?Pakistan?for?Kabul?embassy?attack,”?http://gulfnews.com/news/world/india/india-blames-pakistan-for-kabul-embassy-attack-1.118052(上網時間:?2008年7月13日)
[6]??Sue?Pleming,?“U.S.?seeks?to?balance?India's?Afghanistan?stake,”?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0/05/31/idINIndia-48927220100531(上網時間:2010年5月31日)
[7]?同[6]。
[8]??Simbal?Khan,?“Afghanistan:?post-2014?strategy?and?the?regional?framework,”?http://www.eastasiaforum.org/2012/05/11/afghanistan-post-2014-strategy-and-the-regional-framework/(上網時間:2012年5月11日)
[9]?Arwin?Rahi,?“Why?a?Regional?Security?Force?Will?Not?Work?in?Afghanistan,”?The?Diplomat,?http://thediplomat.com/2014/04/why-a-regional-security-force-will-not-work-in-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4年4月20日)
[10]?Amie?Ferris-Rotman,?“Russia?May?Deploy?Troops?To?Afghan?Border?After?NATO?Withdrawal,”?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3/05/17/russia-deploy-troops-afghan-border_n_3290864.html(上網時間:2013年5月17日)
[11]?Jagannath?P.?Panda,?“Narrow?interests?limit?SCO's?influence,”?Global?Times,?June?13,?2011,?http://www.china.org.cn/opinion/2011-06/13/content_22771809.htm(上網時間:2011年6月13日)
[12]?《阿富汗問題與上合組織的作為》,http://www.xzbu.com/1/view-3135027.htm(上網時間:2012年6月25日)
[13]?Shannon?Tiezzi,?“Can?China?Save?Afghanistan??The?Diplomat,?October?31,?2014,?http://thediplomat.com/2014/10/can-china-save-afghanistan/(上網時間:2014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