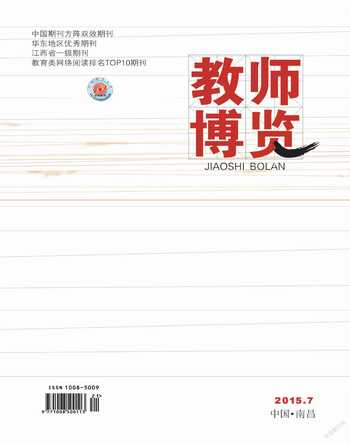“據詩文作畫”的特點和創(chuàng)作規(guī)律
朱軼
[摘 ? 要] 自古以來,詩與畫之間就有著互相取資的傳統(tǒng)。中職美術專業(yè)學生“據詩文作畫”是一項基本的技能。首先,“據詩文作畫”遵循“由文本到畫作”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其次,作畫內容基于對詩文的解讀;畫作品位基于對詩文意境的品讀;畫作高度基于對詩文人文內涵的體悟。再次,作畫不是對詩文的簡單復制,而是對詩文進行的再創(chuàng)作。
[關鍵詞] 據詩文作畫;創(chuàng)作規(guī)律;內容解讀;意境的品讀;人文內涵的體悟;再創(chuàng)作
詩與畫是藝壇上一對孿生姊妹,她們之間有著互相取資的傳統(tǒng)。宋代文學家蘇軾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提出“詩畫同一律”,在《書摩詰藍田煙雨圖》中盛贊王維“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境界。此后,有更多學者論及詩畫藝術之相通之特點。宋人蔡絳在《西清詩話》中說:“丹青吟詠,妙處相資。昔人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蓋畫手能狀,詩人能言之。”另一宋人張舜民在《畫墁集》中說:“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清代鄒一桂亦云:“善詩者詩中有畫,善畫者畫中有詩。”這些先賢都道出了中國詩文與畫作相融相通的關系。
現在通行的高中語文教材里選取了許多中國的經典作品,有詩有文,古代如陶淵明的《歸園田居》、司馬遷的《史記·荊軻刺秦》、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近現代的如戴望舒的《雨巷》、徐志摩的《再別康橋》、郁達夫的《故都的秋》、朱自清的《荷塘月色》……有長于狀物摩形之作,亦有敘事跌宕之文。雖然世殊時異,但經典的內涵如山間之清泉,汩汩涓涓,常出常新。
本校開展的語文和美術專業(yè)相結合的課題“中職學校美術專業(yè)語文‘讀、繪、制、賞’教學范式研究”在“據詩文作畫”方面有著獨特而領先的嘗試。這個省級課題是在我校原有課題“據詩文作畫”基礎上的一次提升:“詩文”依然是“作畫”的來源和基礎,但“作畫”的目標已由原先的一幅畫上升到了一組畫,同時結合我校動漫專業(yè)的優(yōu)勢,最終目的是將其制作成動漫作品。
作為課題研究的重要部分,本文將從語文學習的角度,重點對美術專業(yè)學生“據詩文作畫”特點和創(chuàng)作規(guī)律進行一番探索。
一、“據詩文作畫”的基本原則
我校課題的選材范圍明確為人教版高中語文必修和選修教材,但教材里的文章并不是篇篇都適合進行“據詩文作畫”。通過篩選,較適宜進行”據詩文作畫”的篇目可以大致分成兩類:一類是寫景抒情的詩文,一類是寫人記事的詩文。但不論是哪類詩文,除了極少數描摹景物的詩文里可以不出現人,或景物里出現的人物只是作為陪襯,不做重點描繪,不需進行角色形象設計以外,其他”據詩文作畫”的創(chuàng)作過程基本都遵循“由文本到畫作(動畫)”創(chuàng)作的基本原則,即”閱讀文本—分析文本—角色造型設定—場景設定—分鏡頭—創(chuàng)作原畫(制成動畫)”。
二、“據詩文作畫”的特點和創(chuàng)作規(guī)律
1.畫作內容——基于對詩文內容的解讀
“據詩文作畫”第一步就是解讀原作文字,而解讀的層次直接影響美術創(chuàng)作的效果。
讀懂詩文的第一步,是讀懂內容,即詩文寫于何時何地,寫的何人何事,描摹的何種景象。往往讀懂了詩文內容就可以創(chuàng)造出精美的美術作品,特別是那些長于狀物摩形之作和敘事跌宕之文,更是美術佳作的源泉。
比如,根據郁達夫的《故都的秋》進行美術創(chuàng)作。面對郁達夫的文字描述,大概任何人眼前都會浮現一副關于秋景的畫面。因為文中描述的許多場景簡直就是一幅幅帶有立體美感的畫面,如“從槐樹葉底,朝東細數著一絲一絲漏下來的日光”一段:碧藍遼闊的天空作了畫的背景;地面上,五顏六色的牽牛花薈萃成流光泛彩的野花圃;天與地之間,間或出現一兩只白色或瓦灰色的馴鴿,點綴在一大片的空白中間,顯得疏密得體,濃淡相宜。對于美術專業(yè)的學生,只要稍加訓練就可以把文中的內容直接轉化成畫作。
還有司馬遷的《史記·鴻門宴》。故事的線索非常清晰:曹無傷告密—項伯夜訪—劉項約婚—劉邦請罪—項王留飲—范增舉玦—項莊舞劍—樊噲闖營—樊噲力斥—沛公逃席—項王受璧—誅殺曹無傷。學生閱讀完文本,理清故事線索,確定好人物角色造型設定,再根據情節(jié)發(fā)展進行分鏡頭場景設定,就可以進行連環(huán)畫的繪制了。
2.畫作品味——基于對詩文意境的品讀
除了表現和還原場景、事件,中國的所有藝術形式,又都講究意境。作詩,需有“真味”,明代藏書家朱承爵在《存余堂詩話》中說:“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畫作,亦需有意境才能氣韻超拔,生命恒久。所以,當畫者對詩文的意境有自己獨特的感悟時,就能進一步在畫作意境的營造上進入更高的境界。
如根據南唐后主李煜的名作《虞美人》進行美術創(chuàng)作。《虞美人》是李煜的代表作,也是他的絕命詞。這首詞作者不加藻飾,不用典故,純以白描手法直接抒情,通過意境的營造感染讀者。詞作中他竭力將美景與悲情、往昔與當今、景物與人事的對比融為一體,尤其是通過自然的永恒和人事的滄桑的強烈對比,把蘊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傾瀉出來,凝成最后的千古絕唱——“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這些意境怎么表達?在轉化成畫作時就該好好琢磨。首先,畫面的整體布置安排可以借鑒詞人在詞作中運用的對比的方法。其次,畫面中景物的整體色調應與詞作意境相符,適宜選用灰暗、沉靜的顏色作為主色。再次,在畫面的具體構思上,選取哪個場景作為主體:是當年的繁華景象,還是現實落魄的圖景?是否出現主人公形象?是正面刻畫主人公悲苦、惆悵的表情,還是干脆留下主人公的背影,讓觀眾自由想象?……可以選取最有感觸的角度來確定。總之,畫作創(chuàng)作的繁與簡、虛與實、動與靜、整齊與松散等對比關系,風格及技法的確定,都有賴于創(chuàng)作者對所參照的詩文意境的體悟。
3.畫作高度——基于對詩文人文內涵的體悟
對詩文的品味,最重要的一點是對詩文的人文內涵的理解。那些光耀千古的經典詩文作品,無不凝結了作者深刻的人文思考和體驗。所以,許多有識之士特別強調語文教育要講人文性,認為教育應該是“人文的教育”。作為詩文的讀者和畫作的創(chuàng)造者,“人文”就是我們所應選取的角度和應達到的高度。換言之,你站在何種人文的角度去理解這篇詩文,也就決定了你用什么樣的方式去創(chuàng)作畫作。
比如魯迅的《孔乙己》,魯迅先生作為偉大的文學家、思想家,窮其一生塑造了孔乙己、祥林嫂等眾多經典人物形象,如果我們也跟咸亨酒店的“短衣幫”們一樣,僅僅去嘲笑“孔乙己、祥林嫂”們,甚至還用現代的眼光審視,也恨不得再踏上一只腳罵一句“誰叫你自己不努力不奮斗,活該!”那我們自身也就是更加深刻地印證了魯迅先生揭示的“國民劣根性”,我們和我們的學生也就成了另一群麻木的“看客”。這豈不是語文教育的巨大缺失?
該怎么讀?筆者覺得,我們自己,同時也包括我們的學生,應該站在人文的高度,帶著悲憫的心,帶著同情和善意去解讀。當我們從人文立場出發(fā),用人文史觀、視角去看待這些人物和事件的時候,當我們要把他們轉化成畫作的時候,畫面必然會沖破文字表面的敘述場景,會有更深的人性表達和人文內涵閃現其中,讓畫作達到相當的高度。
三、“據詩文作畫”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
“據詩文作畫”并不是簡單地將文學作品“翻譯”成繪畫語言,“據詩文作畫”是一種再創(chuàng)作。
再創(chuàng)作的內涵豐富,比如狀物摩形類詩文轉化后的“神似”與“形似”的問題,僅僅做到“形似”并不困難,而要達到“神似”則一定經過了畫者的再創(chuàng)作。比如像表現李白的《夢游天姥吟留別》等一些神話題材的“仙氣”和“意境”時就需“留白”的藝術,表現在構圖上就是不要平、滿,沒有空處,而是要“空”,要“險”,可表現遠山朦朦朧朧,似斷似續(xù),煙霧氤氳,云氣繚繞的景象。
再比如對敘事跌宕類詩文進行繪畫創(chuàng)作時,在塑造人物形象、掌握重點突出高潮、組織故事的開始和結局等地方常常需要作畫者進行再創(chuàng)作。如《記梁任公的一次演講》,原作主要刻畫了梁任公的形象,文中只寫了一方面,但在畫面上卻要將演講者和聽眾兩方面都具體呈現。聽眾有多少人,是些什么樣的人,聽眾整體反應怎樣,哪幾位聽眾的神情需要具體刻畫,哪些聽眾要模糊處理……這些都要作畫者很好地推敲。
詩人用詩心感受世界,文人用文筆描寫感情,畫者用畫筆涂繪意境。“詩畫同源”給了我們創(chuàng)作的可能和空間,我們用實踐對經典重新注解。“丹青”“吟詠”相濟相生,妙趣無限!
責任編輯 ? 萬永勇
[作者簡介] 朱 軼(1979—),女,湖南長沙人,長沙市美術學校,中教一級,研究方向為
語文教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