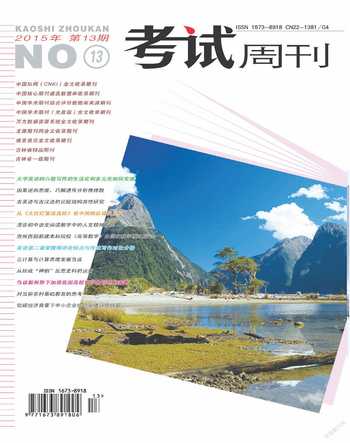試論日本人的無常觀
廖曉菲
摘 要: 無常觀是影響日本許多文學(xué)作品走向的觀念之一,《方丈記》和《徒然草》更是其重要體現(xiàn),這兩部作品比較全面地揭示了日本人的無常觀。日本學(xué)界,歷來對(duì)這兩部作品多有研究。本文以這兩部作品為中心,對(duì)無常進(jìn)行積極和消極兩方面的介紹,側(cè)重對(duì)積極的無常觀提出看法。
關(guān)鍵詞: 無常觀 方丈記 徒然草
“無常”屬于佛教用語(yǔ),在傳入日本以后逐漸本土化,使得無常觀成為日本人的一種心理特征,更是日本大量的文學(xué)作品中的心理內(nèi)涵。日本中世隨筆文學(xué)的雙璧——《方丈記》與《徒然草》分別為日本僧人鴨長(zhǎng)明和兼好法師所作,可以說無常觀是這兩部作品的主基調(diào)。這兩部作品中的無常觀被后世日本人不斷引用和解析,比如西尾實(shí)在解析《徒然草》時(shí)提出了“詠嘆無常觀”和“自覺無常觀”;今成元昭分析《方丈記》是以“場(chǎng)所”為中心提出了“空間無常觀”等①。事物不是片面的,同樣“無常觀”也是多面的,本文通過對(duì)兩部作品的解析,試論消極無常和積極無常,著重論述在積極無常觀方面所體現(xiàn)出的美學(xué)思想。
一、何謂“無常觀”
“無常”常見于佛教典籍,其中最有名的是《大般涅槃經(jīng)》中所說的“諸行無常”,它由“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己”、“寂滅為樂”四部分構(gòu)成,說明了世間無一時(shí)一刻不在變動(dòng),以“生”與“滅”的法則深入透析這個(gè)世界的無常,又在這生生滅滅中看到人生的“苦”,釋迦頓悟,釋然這世界的“苦”便是“寂滅為樂”。故而,在佛教看來“無常”是萬物的法則,也是萬物生靈陷入“苦”的根源。這一宗教思想傳入日本后,隨著日本的歷史現(xiàn)實(shí)的發(fā)展有了日本式的改變。這一變化大致上分為兩種情況:生成式無常和消滅式無常。前者是對(duì)無常的積極看待,后者則是一種消極看待。比如在“落花”一事上,花開花落是無常法則,無人能夠改變,但是從落花枝頭的生息演變,來看待“無常”,就是“生成式無常”,而從一地飄零的落花看“無常”,就是“消滅式無常”。二者本源都是對(duì)無常法則的認(rèn)可,但是有了不一樣的側(cè)面。
二、鴨長(zhǎng)明與《方丈記》中的無常觀
鴨長(zhǎng)明(公元1155—1216年)出生于京都,是京都賀茂御祖神社(下鴨神社)的神官之子,小時(shí)候被過繼到祖母家,由祖母撫養(yǎng)長(zhǎng)大。25歲時(shí),父親和祖母相繼去世。鴨長(zhǎng)明在30—40歲期間,專心研究和歌與音樂曲調(diào)。由于在和歌方面才華出眾,他受到后鳥羽先帝的賞識(shí),被任命為和歌所的“寄人”(朝廷的一種官銜)。后鳥羽先帝還推薦鴨長(zhǎng)明出任下鴨神社攝社的神官一職,但無奈遭到同族的反對(duì)。個(gè)人家庭、仕途等的不如意,以及所處社會(huì)的動(dòng)蕩不安,等等,使得鴨長(zhǎng)明在50歲時(shí)遁世出家,隱居在方丈庵中,并寫下了回憶其人生際遇的隨筆《方丈記》。
《方丈記》大致分為三部分:開篇的序言,是文章的思想主調(diào),集中體現(xiàn)了鴨長(zhǎng)明的無常觀:
逝川流水不絕,而水非原模樣。滯隅水浮且消且結(jié),那曾有久佇之例。世上的人和居也如此。敷玉灑金般的都城里,并棟比甍、貴賤人等的住居,雖幾經(jīng)世代而延續(xù),但尋究其間真實(shí),昔日的本家罕見,不是去年被燒今年新造,就是大宅衰微成了小宅。住的人也相同。盡管地方?jīng)]變,人也甚多,但舊日見過的人,二三十人中只有二三人。朝死夕生,復(fù)而不已,恰似水泡。不清楚,新生的死去的人,來自何方去了哪里?亦不清楚,這夢(mèng)幻的宿世,為誰(shuí)惱心,又因何要眉開眼笑?那主人那宅院互爭(zhēng)無常的樣子,說起來無異于喇叭花上的露珠。時(shí)而露珠落去花留著,留是留著,但一見朝陽(yáng)即枯。時(shí)而花萎露珠未消,消是未消,但不待黃昏時(shí)②。
不難看出其中滿溢的無常感嘆,生死輪回只在朝夕,恍然間已是物是人非,若水波中的泡沫沒碰著就碎了。露水一向在日本的和歌中就是無常的代名詞,這挨不過朝陽(yáng)的露水都不及蜉蝣幸運(yùn)。人生無常,花與露都脆弱,如夢(mèng)似幻,人世間只是驚鴻一瞥。鴨長(zhǎng)明對(duì)于無常是人世不二法則的體會(huì),是十分深刻的,開篇遣詞造句優(yōu)美,可這美好的文字里透漏出的是他在歷經(jīng)人世的種種波折之后感悟到的無常的“苦”,文字雖輕,但其中的愁苦意味顯得更濃厚。
第二部分是正文的前篇,記載了鴨長(zhǎng)明親身經(jīng)歷的平安末期的“五大災(zāi)禍”,即“安元大火”、“治承颶風(fēng)”、“遷都福原”、“養(yǎng)和饑饉”及“元?dú)v大地震”。
“人的營(yíng)生,皆在愚蠢之中。為了在那般危險(xiǎn)的京城中建房,費(fèi)財(cái)勞心,是何等無聊的事啊”③。
“昨日相互爭(zhēng)艷的豪華人家的宅邸,與日荒廢下去。拆了家屋材木扎成筏由淀河漂運(yùn)而去,莊基地眼睜睜成了田地”④。
“一年春夏干旱,一年秋冬大風(fēng)洪水襲來,不祥之事接踵而來,五谷顆粒無收,只是白白春耕夏種,卻沒有秋收冬藏的喜悅”⑤。
正是在這些災(zāi)禍中的所見所聞,更讓鴨長(zhǎng)明深刻地體會(huì)到了諸行無常,人在面對(duì)天災(zāi)人禍時(shí)那么渺小、那么無力、那么無可奈何。無論如何苦心經(jīng)營(yíng),到滅了時(shí)竟然是不帶一絲一毫的拖拉。“生”與“滅”的巨大落差讓鴨長(zhǎng)明掉進(jìn)了無常的“苦”中,他思考如何從這些轉(zhuǎn)瞬即逝的人世間解脫出來:“得一何樣場(chǎng)所,采取什么舉措,暫且安身,須臾之間也好,能讓心安憩嗎?”于是,他選擇遁入空門、隱居起來,學(xué)習(xí)釋迦,希望在大自然中頓悟到解脫的方法。
在第三部分,鴨長(zhǎng)明筆鋒一轉(zhuǎn),將這方丈之地的隱居生活一一描寫,先是自敘身世,接著書寫隱遁大原山,后又遷移日野山筑庵。四時(shí)景美,時(shí)有小童做伴,似乎深得隱逸之樂。可是鴨長(zhǎng)明終究不是天生的隱者,閑適的生活并不代表他找到了解脫無常之苦的方法。一方丈小屋當(dāng)然要時(shí)常擔(dān)心風(fēng)雨,還要提防獨(dú)居招致的盜賊,這便是“得一何樣場(chǎng)所”,即便是隱居,擔(dān)憂不減,人心始終是躁動(dòng)的。四時(shí)景色宜人,可是在四季更迭中最難忽略的就是“變遷”,就是所謂的“無常”。
“春看藤波起伏,紫云般照映西方。夏聽杜鵑聲,如語(yǔ)契約去死后的永遠(yuǎn)之旅。秋日蟬聲盈耳,似聽空蟬悲世。冬時(shí)雪動(dòng)人,積雪消雪可比人世罪障”⑥。
很難有人看的是純粹的景,因?yàn)橛玫氖亲约旱摹把劬Α保嗛L(zhǎng)明同樣沒有免俗,他看的春藤、夏鳥、秋蟬、冬雪。春藤若紫云卷向西方,西方是佛教的凈土,是彼世;夏日的杜鵑啼血締結(jié)往生的契約;秋蟬更是悲嘆人世,因我即將告別;冬雪美則美,也幸得消融我在人世的罪孽。即便是隱居,即便是在空門參悟,鴨長(zhǎng)明感受到的仍舊是那揮不散、逃不出的無常之苦。所以說,鴨長(zhǎng)明在《方丈記》中所體現(xiàn)的無常觀是哀痛的、是為流逝、是為得不到、是為不得長(zhǎng)存。雖然免不得自身命運(yùn)的凄楚,可這種“消滅式無常觀”確實(shí)也是當(dāng)時(shí)日本社會(huì)心理、文學(xué)筆調(diào)的一大體現(xiàn),加上日本人擅長(zhǎng)在“雪月花”上大做文章,確實(shí)也擔(dān)得“凄美”。這感染著日本人生命觀中都多少帶有無奈與哀傷。
三、兼好法師和《徒然草》的無常觀
兼好法師原名吉田兼好,生平不詳,其先人,曾世代為“神祇官”,掌管宮中“卜筮”。兼好的祖父兼名、父親兼顯、兄兼雄皆身為官吏服務(wù)于朝廷。兼好本人出家之前也是在朝為官,官至左兵衛(wèi)佐。他深諳朝廷、武家“有職故實(shí)”(禮儀、典章、制度),頗為時(shí)人所重。二條天皇去世后,不久便辭官出家,成為自由的隱逸者。辭官時(shí)約30歲,隱居中致力于文學(xué)研究和詩(shī)歌創(chuàng)作,后出家,《徒然草》也就是在這個(gè)時(shí)期創(chuàng)作出來的。他一生志不在功名,游離在政治斗爭(zhēng)之外。
《徒然草》全書243段,分為上下兩卷,文字為漢日混合,內(nèi)容混雜,主要是自己的思想和一些雜感。如兼好法師自己在序段所言:“百無聊賴,終日于硯前枯坐,心中諸事紛繁,遂信手而書,其中或有常理難度、不可名狀事,目為狂言怪談可也。”⑦可見《徒然草》確實(shí)是隨心所作,在看似無心中往往能夠體現(xiàn)出最真實(shí)的感受。
《徒然草》中的無常觀也不是一個(gè)主基調(diào)的,其中既有積極的“生成式無常觀”又有消極的“消滅式無常觀”,但不是以上下兩卷為分界,有所夾雜,但大致上是以第32段為界限。兼好法師的消極無常表現(xiàn)最多的是第25段:
飛鳥川激流變化不定,恰如人世之無常。時(shí)移世易,悲歡離合,昔年華屋美棟而今俱成無人荒野。即使府宅依舊,也已物是人非,桃李無言,與誰(shuí)共話往昔?尚有未知主人之遺跡,更似浮云,虛無消散⑧。
這段隨筆中不難看出作者的感嘆,帶著日本人特有的淡然的語(yǔ)氣。滄海也能變成桑田,何況華屋在風(fēng)吹日曬中變成荒原。桃李爭(zhēng)相開放,又匆匆謝去,卻是終究無法向世人訴說花下的故事,現(xiàn)年盛開的花不是去年的花了,要訴說也得等得一個(gè)新的故事了。逃不過的,不過是人生諸行無常。再說《徒然草》的第三十段,人死之后,墓地置辦在遠(yuǎn)離村子的山里,家里的血親也就在忌日等一些需要祭拜的日子才來掃掃墓。別的旁系親戚大抵不愿意這么做,許是因?yàn)椴患R虼耍贡仙隽饲嗵Γ⒙涞臉淙~漸漸掩埋了墳冢,那么,太陽(yáng)西斜時(shí)的山嵐、夜半的清月,只有這些成了墓地下已逝之人的話友。這種無法跨越的悲傷與無奈生出人的無常觀,生前、死后,哪個(gè)不是圍困在無常里呢?兼好法師對(duì)于無常的苦也是體會(huì)深刻的,但既然時(shí)局渾濁、自己隱居遁世這樣的感嘆也是必然的,可以說是他“生成式無常觀”的思想基礎(chǔ)之一。
再來看兼好法師的“生成式無常觀”:
推究緣故,蓋因世事變易無常,完美事物從未存在。事始而難終,志不遂而希望不絕。人心不定,物皆幻化,凡事均不過暫存。可嘆此理庸常難明。吉日作惡則必兇,惡日行善則必吉。吉兇皆由人而生,而非由日而定⑨。(第91段)
人生便如雪佛,自下逐漸消融。可嘆于此期間,蠅營(yíng)狗茍圖得利者,何其多也⑩。(第166段)
世間之事,“變”既然為正理,那么就順應(yīng)這種變化,事在人為,也許無法擺脫命運(yùn)但是不要認(rèn)命,不要在命運(yùn)面前顯示出自己的畏懼,要尊敬做力所能及的改變。這就是兼好法師在無常里參透出來的生存之道,可能算不上解脫的方法,但是這確實(shí)是他站在另一個(gè)角度看到的無常,看到的人生。他對(duì)無常不僅僅是意識(shí)到,更是從本質(zhì)的角度對(duì)無常給予了肯定。
四、無常的生命美學(xué)
世事無常,人生無常雖說是定理,但是它并不意味著生命色彩的消失。兼好法師在《徒然草》第155段中表達(dá)了一種更積極的人生態(tài)度:“生住異滅之轉(zhuǎn)變,乃切實(shí)大事,如洪流漲溢迅猛,滔滔奔涌,片刻不停。無論真俗,欲隨心立業(yè),于時(shí)機(jī)概不必論。莫徘徊觀望,莫裹足不前。”{11}
他鼓勵(lì)人們珍惜生命,只爭(zhēng)朝夕。日式的無常觀更帶有生命色彩,它看似一層憂傷籠罩,但在人們的不斷參悟中沉淀、蛻變變成五彩斑斕的生命外衣。《敦盛》有一段詞句,是日本戰(zhàn)國(guó)梟雄——織田信長(zhǎng)最愛吟詠,引以起舞的一段:“人間五十年,萬事如夢(mèng)幻。一度生存者,豈有長(zhǎng)不滅。”{12}他這一位有著懷抱天下的雄心壯志的天下人,怎么會(huì)常詠無常呢?歸根到底他是明白的,人生確實(shí)無常,但不在這須臾片刻的人生里盡情“開疆?dāng)U土”,如何甘休?小林秀雄在《平家物語(yǔ)》一文中有道:“從平家物語(yǔ)的作者們并無厭世厭人的詩(shī)魂來看,當(dāng)時(shí)的無常思想,不過是時(shí)代的虛無構(gòu)想。”{13}可見,平家物語(yǔ)雖然在琵琶聲中顯得哀婉,但是確實(shí)有“哀而不傷”的感覺,因?yàn)闊o常是人世定理,那六波羅政權(quán)如何如日中天,終究是會(huì)西斜的,不過是世事按照發(fā)展規(guī)律不斷前行罷了。
小林秀雄所寫的《無常之事》,開篇寫某段旅途中見眼前之景,是能與《徒然草》相媲美的文段。小林秀雄表明,認(rèn)為宣長(zhǎng)最執(zhí)著的想法便是:斷然于釋、巋然不動(dòng),唯此物美。由此看出,無常確確實(shí)實(shí)是定理。這些看來都是“日式無常”,長(zhǎng)存之物必然是不存在的,就連思想也是,可是這不妨礙它的存在和撞擊生成那一瞬間的高度。這便是無常的美學(xué)。
五、結(jié)語(yǔ)
本文通過對(duì)無常的佛教本源解釋,引出它在經(jīng)過日本本土化以后大致分為“生成式無常觀”和“消滅式無常觀”,這兩種無常觀屬于日本人的社會(huì)心理。接著又分別列舉了《方丈記》和《徒然草》這兩部作品,各有不同的主基調(diào)。鴨長(zhǎng)明在無常的“苦”里無法自拔,他意識(shí)到了無常這一定理,但是他的生活經(jīng)歷使得他在有生之年無法完全參透無常。這也是當(dāng)時(shí)許多日本人的心理及大多數(shù)文學(xué)作品中體現(xiàn)的主題。兼好法師,也在“消滅式無常觀”中徘徊,可是他的心性、他的人生經(jīng)歷使得他能從另一個(gè)角度看待“無常”,走向“無常”的深處、探尋它的本質(zhì)。
生命本來就是不完整的,因?yàn)樯岬谩⒁驗(yàn)榈檬В@種殘缺和凋零感,時(shí)刻都刺激著日本人敏感而纖細(xì)的思維。島國(guó)的地理環(huán)境讓日本人不得不習(xí)慣生死無常,但也許正是因?yàn)檫@樣的環(huán)境,佛教的無常得以傳播,卻不是純粹佛教義理上的無常。
注釋:
①http://www.academia.edu/4141342
②③④⑤⑥[日]鴨長(zhǎng)明,吉田兼好,著.方丈記 徒然劃[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06:3,5,7,10,19.
⑦⑧⑨⑩{11}[日]吉田兼好,鴨長(zhǎng)明,著.王新禧,譯.徒然草·方丈記[M].武漢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11,11:2,27,75,133,127.
{12}大國(guó)通史 日本通史,P277.
{13}小林秀雄集,P255.
參考文獻(xiàn):
[1][日]鴨長(zhǎng)明,吉田兼好,著·方丈記 徒然草[M].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06.
[2][日]小林秀雄.新訂小林秀雄全集第八巻無常といふ事·モオツァルト.新潮社.昭和53年.
[3]沙歡,董佳佳,陳君.試論《徒然草》的生命美學(xué)[J].作家,2010(6):126-127.
[4]洪瑜瑛.《方丈記》與《徒然草》——無常觀的對(duì)比[A].福建省外國(guó)語(yǔ)文學(xué)會(huì),2009年年會(huì)論文集[C],2009.
[5][日]吉田兼好,鴨長(zhǎng)明,著.王新禧,譯.徒然草 方丈記[M].武漢:長(zhǎng)江文藝出版社,2011.11.
(本文在撰寫過程中得到寧波大學(xué)日語(yǔ)系李廣志老師的指導(dǎo),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