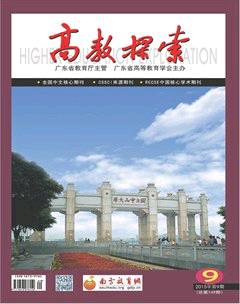基于心理契約理論的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度研究
吳思+樊博



摘要: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是大學(xué)生活躍思想、展現(xiàn)自我、培養(yǎng)綜合能力的重要平臺(tái),社團(tuán)參與度影響到社團(tuán)作用的發(fā)揮程度。本文引入心理契約理論,在回顧國(guó)內(nèi)外相關(guān)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構(gòu)建了大學(xué)生心理契約履行與社團(tuán)參與度關(guān)系模型,以189位大學(xué)社團(tuán)成員為調(diào)研對(duì)象,以問(wèn)卷調(diào)查的方式獲取研究數(shù)據(jù),通過(guò)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的PLS建模的方法驗(yàn)證了多重假設(shè)關(guān)系,研究得出以下結(jié)論:社團(tuán)心理契約中的關(guān)系型契約相對(duì)于交易型契約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的影響更加顯著;同時(shí)組織認(rèn)同感在關(guān)系型契約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的影響中發(fā)揮了重要的中介作用。
關(guān)鍵詞: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度;心理契約理論
一、引言
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是由高校學(xué)生依據(jù)興趣愛(ài)好自愿組成的,按照章程自主開(kāi)展活動(dòng)的學(xué)生組織,是大學(xué)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校園文化建設(shè)的重要載體[1];有效開(kāi)展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活動(dòng),在培養(yǎng)學(xué)生綜合素質(zhì)、促進(jìn)學(xué)生全面發(fā)展、活躍校園文化氛圍、豐富學(xué)生課余生活、加強(qiáng)校園文化建設(shè)等諸多方面發(fā)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2]。在社團(tuán)活動(dòng)中,學(xué)生是參與的主體,只有當(dāng)社團(tuán)成員意識(shí)到學(xué)生社團(tuán)的價(jià)值,積極投入?yún)⑴c到社團(tuán)活動(dòng),大學(xué)生社團(tuán)的積極作用才有可能充分發(fā)揮,但社團(tuán)參與度并不理想。有數(shù)據(jù)顯示,大學(xué)生普遍認(rèn)為自己參加的社團(tuán)活動(dòng)較少,未到一般水平[3];另一份研究表明,社團(tuán)成員交往的程度和密度較低,僅為15.7%[4]。大學(xué)生帶著很高的熱情加入社團(tuán),而加入之后,由于社團(tuán)的約束力不足或社團(tuán)建設(shè)未能滿足成員期望,弱化了他們社團(tuán)參與的積極性與持續(xù)性。針對(duì)這一問(wèn)題,研究者將視角聚焦在內(nèi)部管理制度層面、社團(tuán)外部支持與物質(zhì)保障層面,希望以此加強(qiáng)社團(tuán)建設(shè),促進(jìn)成員積極參與。然而,本文認(rèn)為,社團(tuán)參與度高低更取決于成員內(nèi)心對(duì)于社團(tuán)以及自我的期待,即社團(tuán)組織與成員之間的心理契約。大學(xué)生社團(tuán)組織屬于非正式群體,約束力相對(duì)較弱,心理契約成為維系社團(tuán)與成員間關(guān)系的紐帶,更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有著重要影響。本文通過(guò)實(shí)證分析方法,探究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心理契約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的影響方式及其程度,并提出提高社團(tuán)參與度的建議措施。
二、相關(guān)理論研究
(一)心理契約的概念
心理契約一詞首先由施恩在20世紀(jì)60年代提出。80年代之后,由于全球化導(dǎo)致的企業(yè)競(jìng)爭(zhēng)加劇,心理契約的研究進(jìn)入高潮。大量的心理契約研究集中在企業(yè)領(lǐng)域,在推動(dòng)企業(yè)發(fā)展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各類組織尤其是非營(yíng)利性組織已經(jīng)開(kāi)始積極關(guān)注這一概念。心理契約的內(nèi)涵主要有兩大觀點(diǎn),即廣義的心理契約與狹義的心理契約概念,兩者的不同點(diǎn)在于期望主體的選擇。支持廣義心理契約的觀點(diǎn)主要有:Levinson認(rèn)為“未書(shū)面化的契約”,是組織與員工之間相互期望的總和[5];Schein把心理契約定義為每一組織成員與其組織之間每時(shí)每刻都存在的一組不成文的期望[6];Kotter提出,“心理契約”是個(gè)人與其組織之間的一份內(nèi)隱的協(xié)議,他將雙方關(guān)系中的一方希望付出的以及從另一方得到的回報(bào)具體化[7]。人們將雙向期望的觀點(diǎn)稱之為心理契約廣義定義。狹義心理契約以美國(guó)學(xué)者Rousseau、Robinson、Morrison等人為代表,強(qiáng)調(diào)心理契約是雇員個(gè)體對(duì)雙方交換關(guān)系中彼此義務(wù)的主觀理解[8],被稱之為“Rousseau學(xué)派”。
大學(xué)生社團(tuán)作為非正式群體,機(jī)構(gòu)相對(duì)松散,雙向的心理契約在這類組織中很難界定,因而本文認(rèn)為應(yīng)從社團(tuán)成員的視角評(píng)判心理契約的履行狀況,以心理契約的狹義內(nèi)涵作為理論支撐,定義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心理契約為社團(tuán)成員對(duì)雙方關(guān)系中彼此義務(wù)進(jìn)行的主觀理解與期待。
(二)心理契約的維度
心理契約的維度也存在著分歧,主要有二維結(jié)構(gòu)和三維結(jié)構(gòu)兩種觀點(diǎn)。以Rousseau和Parks為代表的學(xué)者認(rèn)為:雖然心理契約存在很大的差異性和個(gè)體性,但大致可分為兩類——交易型心理契約和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其中交易型契約指組織提供的晉升、績(jī)效獎(jiǎng)勵(lì)、培訓(xùn)和職業(yè)發(fā)展的情況,是以物質(zhì)經(jīng)濟(jì)交換為基礎(chǔ)的契約關(guān)系的履行狀況;而關(guān)系型契約則與之相對(duì),表示組織提供的長(zhǎng)期工作保障狀況,是雇員以長(zhǎng)期工作、忠誠(chéng)等為代價(jià)換取的社會(huì)情感交換為基礎(chǔ)的契約關(guān)系的履行[9]。以Rousseau&Tijorimala[10]、Lee& Tinsley[11]為代表的學(xué)者,通過(guò)實(shí)證研究發(fā)現(xiàn)心理契約由三個(gè)維度構(gòu)成:交易維度、關(guān)系維度和團(tuán)隊(duì)成員維度。
在大學(xué)生社團(tuán)中,組織與成員之間為非雇傭關(guān)系,組織不需要提供物質(zhì)獎(jiǎng)勵(lì)和長(zhǎng)期的工作保障,但仍存在以提供活動(dòng)、晉升、加分、培訓(xùn)等短期可實(shí)現(xiàn)的以一定功利性目的為基礎(chǔ)的交易型契約,以及以社團(tuán)成員平等、信任、忠誠(chéng)換取的以社會(huì)情感交換為基礎(chǔ)的關(guān)系型契約。社團(tuán)中也存在著團(tuán)隊(duì)成員關(guān)系,但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心理契約著重探討組織與成員之間的關(guān)系,基于此,本文根據(jù)“交易—關(guān)系”二維結(jié)構(gòu),對(duì)社團(tuán)內(nèi)容進(jìn)行了維度劃分,具體如下(見(jiàn)表1)。
(三)社團(tuán)參與度
學(xué)生參與度理論發(fā)源于上個(gè)世紀(jì)30年代。與傳統(tǒng)教育理論將學(xué)生作為知識(shí)和技能的被動(dòng)接收者不同,此理論將學(xué)生作為主體,關(guān)注其在教育活動(dòng)中的參與程度,以此使學(xué)生的能力發(fā)展達(dá)到最大化。其中,Pace指出學(xué)生在教育活動(dòng)中投入的時(shí)間和努力越多,則學(xué)生從學(xué)習(xí)或其他方面的大學(xué)體驗(yàn)中收獲越多。[12]Austin通過(guò)提出學(xué)生攝入理論進(jìn)一步促進(jìn)了參與度理論的發(fā)展,他認(rèn)為,一個(gè)高度涉入的學(xué)生是指在學(xué)習(xí)、校園活動(dòng)、參與學(xué)生組織及與師生交流互動(dòng)中投入時(shí)間和精力較多的學(xué)生,而這類學(xué)生往往可以達(dá)到最好的學(xué)習(xí)效果。[13]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是大學(xué)生自我發(fā)展與自我教育的平臺(tái),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度是學(xué)生參與度理論的一部分,學(xué)生在社團(tuán)中的積極參與能夠發(fā)揮社團(tuán)的積極作用,促進(jìn)學(xué)生自我發(fā)展。因而,本文結(jié)合學(xué)生參與度理論并分析大學(xué)生社團(tuán)組織與相關(guān)活動(dòng)的文獻(xiàn)研究,梳理得出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度的概念為大學(xué)生參加社團(tuán)活動(dòng)的頻度,以及參與社團(tuán)的深度與質(zhì)量的集合。其中,社團(tuán)參與頻度指成員在社團(tuán)活動(dòng)中投入的時(shí)間和精力;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則指社團(tuán)成員參與社團(tuán)日常運(yùn)作及其所舉辦各類社團(tuán)活動(dòng)的優(yōu)劣程度[14],Katz曾經(jīng)提出,有效運(yùn)作的組織需要組織成員做出下列三種行為:(1)留任在組織中(離職傾向);(2)可靠地完成角色要求的職責(zé)(角色內(nèi)績(jī)效);(3)做出角色要求之外的創(chuàng)新的和動(dòng)的行為。[15]因此,社團(tuán)成員參與的深度與質(zhì)量也可依此進(jìn)行劃分:(1)消極完成社團(tuán)任務(wù);(2)可靠地完成組織要求的任務(wù);(3)做出角色要求之外的行動(dòng)(公民組織行為)。
綜上所述,國(guó)內(nèi)針對(duì)學(xué)生社團(tuán)建設(shè)的研究往往集中于內(nèi)部管理制度層面、社團(tuán)外部支持與物質(zhì)保障層面,忽視了社團(tuán)參與主體這一研究方向。本文認(rèn)為,制度約束與物質(zhì)支持都有利于社團(tuán)建設(shè),但社團(tuán)存在的意義和發(fā)展的根源應(yīng)為社團(tuán)成員的積極參與與努力付出,因而本文選擇社團(tuán)參與度為研究的重點(diǎn)。同時(shí),關(guān)于社團(tuán)參與度影響因素的研究,本文創(chuàng)新性地引入心理契約理論,認(rèn)為在大學(xué)生社團(tuán)這類非正式群體中,組織與成員之間沒(méi)有明確的雇傭關(guān)系,心理契約作為社團(tuán)成員內(nèi)心對(duì)于組織和自身的期望與實(shí)現(xiàn),成為維系成員與組織關(guān)系的紐帶,更影響著社團(tuán)參與度的高低。這也為社團(tuán)參與度研究提供了更加堅(jiān)實(shí)的理論支撐。
三、研究假設(shè)與模型構(gòu)建
社會(huì)交換理論認(rèn)為,人類的一切行為都受到某種能夠帶來(lái)獎(jiǎng)勵(lì)和報(bào)酬的交換活動(dòng)的支配,人類一切社會(huì)活動(dòng)都可以歸結(jié)為一種交換。因此,當(dāng)成員感受到心理契約履行較好時(shí)(無(wú)論交易型心理契約還是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作為一種交換,其都更傾向于參與組織行為,并對(duì)組織付出。同時(shí),關(guān)于心理契約的文獻(xiàn)綜述也表明,心理契約履行與員工態(tài)度工作行為有關(guān),包括工作績(jī)效、組織公民行為、組織信任、員工流動(dòng)率等。組織心理契約得到恰當(dāng)履行,成員擁有更高的工作信任、留職意向和組織支持感。大學(xué)生社團(tuán)作為非營(yíng)利性的學(xué)生組織,與一般企業(yè)組織不同,組織與成員之間沒(méi)有明確的雇傭關(guān)系,且缺乏有效的規(guī)章制度。因而,心理契約在大學(xué)生社團(tuán)中的作用將更加關(guān)鍵,良好的心理契約履行,將提高大學(xué)生的積極性與參與度。
綜上所述作出如下假設(shè):
H1:交易型心理契約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有正向作用;
H2: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與社團(tuán)參與度有正向作用。
根據(jù)陳淑嬌[16]對(duì)于寧波高校大學(xué)生參與的調(diào)查,有45%的大學(xué)生參加社團(tuán)為了提高自己的個(gè)人能力,另有5%抱著加分評(píng)優(yōu)的目的加入的。由此可見(jiàn),大學(xué)生參與社團(tuán)具有一定功利性,且重視社團(tuán)交易型契約履行的程度。為了獲得更好的收益,此類學(xué)生會(huì)增加參與的頻率,然而,由于他們對(duì)所在組織缺乏認(rèn)同感,認(rèn)為自己和組織之間完全是交易的關(guān)系,他們只會(huì)把目前的工作當(dāng)成向更好工作邁進(jìn)的墊腳石,所以一般來(lái)說(shuō),他們只會(huì)做那些工作職責(zé)明確規(guī)定的工作,沒(méi)有動(dòng)力去做超出角色范圍的工作,因而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的關(guān)注較低。
尹潔林,徐樅巍[17]在研究中認(rèn)為擁有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的員工都對(duì)自己所服務(wù)的組織有著強(qiáng)烈的歸屬感、信任和忠誠(chéng)度,他們更加注重用一些行動(dòng)回報(bào)組織給予他們的支持和尊重,而這些行動(dòng)包括那些并不在工作職責(zé)要求范圍內(nèi)卻對(duì)組織的運(yùn)作有益的行為。依此看來(lái),關(guān)系型契約使成員更易深度參與組織活動(dòng)。
綜上所述,作出如下假設(shè):
H3:交易型契約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頻度的影響大于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
H4:關(guān)系型契約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的影響大于社團(tuán)參與頻度。
在交易型契約中成員關(guān)注的是短期雇傭關(guān)系下的即時(shí)回報(bào),即成員參與組織具有較強(qiáng)的功利性目的,又可稱為工具性信念。所謂工具性信念指的是相信某些行為會(huì)帶來(lái)特定的結(jié)果,因此做出這些行為是為了達(dá)到一定的目的。[18]工具性信念在社團(tuán)中是成員行為選擇的重要驅(qū)動(dòng)器。目前,在現(xiàn)有的社團(tuán)管理中,若社團(tuán)交易型契約履行良好,如可以提供加分、評(píng)優(yōu)、晉升等激勵(lì),往往會(huì)刺激社團(tuán)參與者的工具性信念,促使其提高社團(tuán)參與度。同時(shí),由于社團(tuán)考評(píng)更傾向于參與頻度,而參與的深度與質(zhì)量由于難以衡量而容易被忽略,因而具有較強(qiáng)工具性信念的社團(tuán)成員為得到其期待的結(jié)果會(huì)更加注重社團(tuán)參與的頻度,而對(duì)參與的質(zhì)量有所忽略。綜上所述,得出以下假設(shè)。
H5:交易型契約以工具性信念為中介變量對(duì)社團(tuán)參與進(jìn)行影響。
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是員工和組織之間的一種基于社會(huì)情感交換的關(guān)系,表達(dá)了員工對(duì)于組織所給予的支持和尊重的認(rèn)可、理解和感激,因此擁有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的員工對(duì)于組織有著深厚的情感和強(qiáng)烈的認(rèn)同,愿意全身心地投入到組織中去,即社團(tuán)成員的組織認(rèn)同感較強(qiáng)。許多實(shí)證研究也表明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與組織認(rèn)同成正相關(guān)。而組織認(rèn)同體現(xiàn)在組織成員在行為和觀念等方面與所在組織保持一致性的程度[19],反映組織成員對(duì)組織既有理性的契約感與責(zé)任感,也有非理性的歸屬感與依賴感。在大學(xué)生社團(tuán)組織中,理性的契約感與責(zé)任感會(huì)提高社團(tuán)成員的參與度,而非理性的歸屬感與依賴感則會(huì)進(jìn)一步提高社團(tuán)成員的參與質(zhì)量。
H6:關(guān)系型契約以組織認(rèn)同作為中介變量對(duì)社團(tuán)參與進(jìn)行影響。
基于上述提出的研究假設(shè),本文構(gòu)建了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心理契約履行與社團(tuán)參與度關(guān)系模型,如圖1所示,其中交易型、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為自變量,工具性信念與組織認(rèn)同為中介變量,社團(tuán)參與頻度與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為因變量。
圖1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心理契約履行與社團(tuán)參與度關(guān)系模型
四、實(shí)證分析
(一)樣本與問(wèn)卷
本文以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成員為研究對(duì)象,通過(guò)問(wèn)卷調(diào)研的方式對(duì)北京、河北、重慶、武漢、上海5省份中的5所高校的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成員進(jìn)行了問(wèn)卷發(fā)放,共發(fā)放問(wèn)卷220份,其中回收205份,有效問(wèn)卷189份,最終修訂的問(wèn)卷有26道題。為確保因子分析的有效性,需獲得至少5倍于題目數(shù)的有效樣本[20],即至少130份。而本研究成功獲取189份有效樣本,達(dá)到了數(shù)據(jù)分析所需的最低樣本數(shù),可進(jìn)行下一步的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檢驗(yàn)。在189個(gè)有效樣本中,其中男生占55%,女生占45%;年級(jí)分布中,大一33%,大二37%,大三19%,大四11%。
本文通過(guò)問(wèn)卷調(diào)查的方法對(duì)理論模型進(jìn)行驗(yàn)證,問(wèn)卷主要采用李克特5級(jí)量表法進(jìn)行測(cè)量(最高分為5分,最低分為1分,分?jǐn)?shù)高為贊同程度越高)。根據(jù)研究假設(shè),問(wèn)卷設(shè)計(jì)共分為七部分,即社團(tuán)交易型心理契約履行、社團(tuán)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履行、工具性信念、組織認(rèn)同、社團(tuán)參與頻度、參與質(zhì)量和基本信息。第一、二部分中,由于目前并沒(méi)有關(guān)于社團(tuán)心理契約履行的成熟量表,本問(wèn)卷根據(jù)Robinson,Kraatz and Rous-Robinson[21]等人對(duì)心理契約中“組織責(zé)任”的探索性分析,并結(jié)合社團(tuán)自身特點(diǎn)進(jìn)行改編;對(duì)于工具性信念的度量,本文結(jié)合其概念,對(duì)20位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成員進(jìn)行調(diào)研,合并提煉出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成員四個(gè)最為主要的工具性信念;組織認(rèn)同的測(cè)量采用Mael和Ashforth[22]開(kāi)發(fā)的一維組織認(rèn)同量表,測(cè)量個(gè)體對(duì)組織的一種認(rèn)同狀態(tài)。該量表信度和效度水平較高,并且操作性很強(qiáng),國(guó)內(nèi)外很多研究都證實(shí)了這一量表的有效性。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度,前部分關(guān)于參與頻度及精力的提問(wèn),后半部分則關(guān)于社團(tuán)參與的質(zhì)量與深度。其中,借鑒了Williams和Anderson[23]有關(guān)員工行為中角色內(nèi)行為,以及角色外行為(組織公民行為)部分的成熟量表。最后為基本信息內(nèi)容。
(二)模型的測(cè)量
本文的統(tǒng)計(jì)分析方法以PLS(Partial Least Squares)為主。PLS對(duì)于樣本容量、殘差分布的要求最低,同時(shí)可有效地解決許多普通多元回歸分析無(wú)法解決的問(wèn)題,諸如克服變量多重共線性在系統(tǒng)建模中的不良作用等,本文模型中含有中介變量,適合使用PLS進(jìn)行建模。另外,本文使用SPSS對(duì)所得數(shù)據(jù)進(jìn)行預(yù)處理,獲得問(wèn)卷的信度與效度。具體軟件選用SmartPLS 3.0,以及SPSS 20.0。
本文通過(guò)SPSS對(duì)問(wèn)卷整體的信度和效度進(jìn)行了測(cè)量。其中,Cronbachs Alpha為0.919>0.9,表明問(wèn)卷的信度高,內(nèi)部一致性強(qiáng),可進(jìn)行因子分析;同時(shí),Kaiser-Meyer-Olkin度量為0.89,主成分提取平方和載入為1.039>1,表明問(wèn)卷的整體效度較高。
為了檢驗(yàn)測(cè)量模型的有效性,本文通過(guò)SmartPLS對(duì)各潛變量的聚合效度和區(qū)分效度進(jìn)行了檢測(cè)。聚合效度是指不同測(cè)量方式是否有效測(cè)量對(duì)應(yīng)的構(gòu)念。在本文中,如表2所示,各潛變量的組合信度(CR)均大于0.7,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大于推薦值0.5,同時(shí)各觀測(cè)變量的外部載荷值(Factor Loading)大于0.7,這說(shuō)明各潛在變量的觀測(cè)變量具有較高的內(nèi)部一致性,可以有效測(cè)量對(duì)應(yīng)的構(gòu)念。
區(qū)分效度是指觀測(cè)變量是否有效測(cè)量相應(yīng)的構(gòu)念,且區(qū)分于其他構(gòu)念的測(cè)量指標(biāo)。根據(jù)Fornell和Larcker[24]提出的方法,區(qū)分效度通過(guò)觀察各個(gè)因子的AVE平方根是否大于其他因子的相關(guān)系數(shù)加以判斷。結(jié)果如表3所示,其中對(duì)角線上的數(shù)值為各因子的AVE平方根,均大于其他因子的相關(guān)系數(shù),證明區(qū)分效度良好。
(三)結(jié)構(gòu)模型評(píng)價(jià)
結(jié)構(gòu)模型路徑系數(shù)估計(jì)結(jié)果,反映的是潛變量之間的直接影響關(guān)系,本文中的路徑系數(shù)見(jiàn)表4。
模型中路徑系數(shù)及各系數(shù)顯著性表明,工具性信念作為大學(xué)生社團(tuán)交易型契約履行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影響的中介變量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頻度與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的路徑系數(shù)為0.003和0.039,且p>0.05,表明顯著性不明顯。由此可見(jiàn),工具性信念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度的中介作用較弱,假設(shè)5不成立。因而,本文去掉中介變量——工具性信念,并對(duì)原模型進(jìn)行調(diào)整,結(jié)果如下(見(jiàn)圖2)。
在經(jīng)過(guò)調(diào)整的模型中(見(jiàn)表5),可以看出,大學(xué)生社團(tuán)交易型契約的履行直接影響參與頻度與參與質(zhì)量,影響系數(shù)分別為0.243、0.168,且P值<0.05,表明影響顯著,假設(shè)1成立。同時(shí)對(duì)于參與頻度的影響系數(shù)大于對(duì)參與質(zhì)量的影響系數(shù),表明交易型契約的履行對(duì)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頻度的影響更加顯著,假設(shè)3成立。對(duì)于大學(xué)生社團(tuán)關(guān)系型契約的履行,其影響組織認(rèn)同的路徑系數(shù)為0.711,且影響顯著;同時(shí)組織認(rèn)同感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頻度和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的影響系數(shù)分別為0.355、0.495,P值<0.05。這一方面表明社團(tuán)關(guān)系型契約的履行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頻度和參與質(zhì)量的呈正相關(guān)的影響,且組織認(rèn)同感的中介作用顯著,假設(shè)2與假設(shè)6成立。
同時(shí),在關(guān)系型契約通過(guò)組織認(rèn)同感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的影響系數(shù)大于社團(tuán)參與頻度,假設(shè)4成立。由此可見(jiàn),在經(jīng)過(guò)調(diào)整的模型中,除假設(shè)5不成立之外,其余假設(shè)全部成立。
除了路徑系數(shù)及其顯著程度,R2可用來(lái)評(píng)價(jià)結(jié)構(gòu)模型的預(yù)測(cè)能力。Chin將內(nèi)部路徑模型中內(nèi)生變量的R2值對(duì)應(yīng)0.67、0.33、0.19三個(gè)數(shù)值劃分為強(qiáng)、中、弱三個(gè)等級(jí)。由表6可見(jiàn),本模型的R2除社團(tuán)參與頻度預(yù)測(cè)度一般外,其余均超過(guò)中等,可見(jiàn)模型的預(yù)測(cè)能力較好[25]。同時(shí),根據(jù)Tenenhaus(2004)提出的PLS全局匹配擬合優(yōu)度:GoF=AVE———·R2——,計(jì)算得到本研究模型的GoF為0.518,大于0.36的高影響邊界值,故全局匹配度高。
(四)實(shí)證研究結(jié)果分析
通過(guò)上述研究,得出如下結(jié)果:(1)心理契約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影響顯著,其中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度的影響更加顯著,尤其是社團(tuán)參與的深度與質(zhì)量。根據(jù)調(diào)查,大部分社團(tuán)成員認(rèn)為如果社團(tuán)具有公平公正、相互尊重的氛圍,且社團(tuán)內(nèi)部溝通頻繁,凝聚力強(qiáng),那么他們會(huì)更愿意融入社團(tuán)并進(jìn)行社團(tuán)建設(shè)。可見(jiàn),履行較好的關(guān)系型契約,可促使社團(tuán)成為大學(xué)生擴(kuò)展交際、溝通交流的平臺(tái),同時(shí)也有利于大學(xué)生發(fā)展健康的心智。然而,與關(guān)系型契約相比交易型契約作用相對(duì)較低,社團(tuán)中良好的活動(dòng)、晉升、加分等對(duì)于社團(tuán)成員的吸引較弱,其原因可能與學(xué)生社團(tuán)提供的活動(dòng)形式與內(nèi)容千篇一律,同時(shí)缺乏有效的制度與激勵(lì)有關(guān),很難引起學(xué)生的興趣。(2)組織認(rèn)同的中介作用顯著。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通過(guò)組織認(rèn)同感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起正向影響,且對(duì)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影響更為顯著。事實(shí)表明,高校社團(tuán)作為大學(xué)生自發(fā)組織的非營(yíng)利性組織,缺乏明確的規(guī)章制度作為約束,管理相對(duì)松散。因而,心理契約成為社團(tuán)與成員之間的無(wú)形約束,良好的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有利于加強(qiáng)社團(tuán)凝聚力,形成社團(tuán)文化,進(jìn)而形成社團(tuán)成員的組織認(rèn)同。同時(shí)這種心理層面的約束相對(duì)較弱,尤其是基于關(guān)系型契約產(chǎn)生的理性契約感與責(zé)任感更加需要感性的認(rèn)同感與依賴感作為紐帶加強(qiáng)社團(tuán)內(nèi)部的凝聚力,促進(jìn)社團(tuán)成員的參與度。組織認(rèn)同感在其中起到較強(qiáng)的中介作用。(3)工具性信念的中介作用微弱。在本文提出的6個(gè)假設(shè)中,唯有工具性信念的中介作用假設(shè)不成立。究其原因本文認(rèn)為有以下兩點(diǎn),其一是高校社團(tuán)中激勵(lì)與晉升機(jī)制缺乏,多數(shù)學(xué)生參加社團(tuán)得不到上述獎(jiǎng)勵(lì),因而工具性信念很弱;其二大學(xué)生加入社團(tuán)的目的多種多樣,例如擴(kuò)展交際、發(fā)展興趣等,都可影響社團(tuán)參與度,分散了工具性信念的中介作用。這一觀點(diǎn)也反駁了國(guó)內(nèi)一些文章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高功利性的論述。
五、結(jié)論
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是培養(yǎng)學(xué)生綜合素質(zhì)、促進(jìn)學(xué)生全面發(fā)展、活躍校園文化氛圍的重要載體,社團(tuán)參與度是關(guān)系到社團(tuán)存在與發(fā)展的重要內(nèi)容,因而探究出影響社團(tuán)參與度提高的核心因素,并提出相應(yīng)對(duì)策具有重要的意義。本文在回顧國(guó)內(nèi)外文獻(xiàn)的基礎(chǔ)上,創(chuàng)新性地將心理契約引入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并構(gòu)建了適合于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心理契約履行與社團(tuán)參與度之間的模型,通過(guò)選擇5所高校189名社團(tuán)參與者作為研究樣本,以問(wèn)卷調(diào)查的方式獲取數(shù)據(jù)進(jìn)行統(tǒng)計(jì)分析,運(yùn)用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的方法驗(yàn)證了模型中的假設(shè),證實(shí)了完善社團(tuán)心理契約履行(尤其是關(guān)系型契約)對(duì)提高社團(tuán)參與度具有正相關(guān)影響。因此,為促進(jìn)大學(xué)生積極參與社團(tuán)活動(dòng),充分發(fā)揮社團(tuán)提升學(xué)生能力的作用,應(yīng)首先將重心放在完善關(guān)系型契約的履行,提高組織認(rèn)同度上。學(xué)生社團(tuán)要重視營(yíng)造組織內(nèi)部的和諧氛圍,搭建溝通交流平臺(tái),促進(jìn)成員間信任;要維護(hù)公平平等的組織環(huán)境,尊重每一位成員,提高成員忠誠(chéng)度;最后要明晰組織目標(biāo)愿景,形成組織文化,加強(qiáng)組織認(rèn)同。當(dāng)然,交易型契約對(duì)社團(tuán)參與度的影響也較為顯著,尤其是參與頻度方面。社團(tuán)發(fā)展的最初宗旨應(yīng)是為大學(xué)生提供豐富多彩的活動(dòng),為此也應(yīng)提高活動(dòng)的質(zhì)量,豐富社團(tuán)活動(dòng)內(nèi)容;同時(shí)適當(dāng)?shù)募?lì)晉升機(jī)制也有利于調(diào)動(dòng)學(xué)生的積極性,增加參與頻度。心理契約的完善,是從心理層面優(yōu)化了社團(tuán)成員對(duì)于組織與自身責(zé)任與義務(wù)的期待和實(shí)現(xiàn),社團(tuán)成員將會(huì)更加自愿積極地參與到社團(tuán)活動(dòng)中來(lái),社團(tuán)建設(shè)也會(huì)從源頭得到加強(qiáng)。
由于受到時(shí)間和空間的限制,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性,尚需進(jìn)一步探討。例如,實(shí)證的樣本仍需擴(kuò)展和延伸,增加被調(diào)查學(xué)校和社團(tuán)的數(shù)量與種類,提高研究的外部效度;此外,結(jié)構(gòu)方程模型以交易型心理契約以及關(guān)系型心理契約整體為自變量,結(jié)構(gòu)相對(duì)簡(jiǎn)單,未能探討出心理契約具體內(nèi)容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度的影響;最后,本研究以社團(tuán)成員作為分析單位不夠全面,如同時(shí)以不同社團(tuán)作為分析單位,并應(yīng)用層次回歸分析的方法(HLM),則可獲得不同層次中社團(tuán)心理契約對(duì)于社團(tuán)參與度的深入分析。
參考文獻(xiàn):
[1]王志堅(jiān).高校學(xué)生社團(tuán)與和諧校園文化建設(shè)[J].教育探索,2008(6).
[2]李鳳威等.遼寧省高校大學(xué)生社團(tuán)活動(dòng)的現(xiàn)狀與對(duì)策[J].現(xiàn)代教育管理,2012(3):102-105.
[3]胡三曼,劉明前.基于社團(tuán)參與視角的大學(xué)生職業(yè)決策自我效能研究[J].內(nèi)蒙古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教育科學(xué)版),2011(11).
[4]李鳳蘭.社會(huì)轉(zhuǎn)型期大學(xué)生參與社團(tuán)狀況的調(diào)查及對(duì)策研究[J].中國(guó)電力教育,2008(10).
[5]Levinson H,Price C R,Manden K J,Solley CM. Man,Management and Mental Health[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6]Schein E.H.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M].Englewood Cliffs,New Jersy: Prentice-Hall,1980.
[7]Kotter J. P.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73(15).
[8]Rousseau DM. Psychological and Implied Contracts in Organizational[J]·Employee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Journal,1989(2): 121-139.
[9]Robinson SL,Kraatz M S,Rousseau DM. Changing Obliga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 longitudinal Stud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 (1):137-152.
[10]Rousseau D M,Tijioriwala. Perceived Legitimacy & Unilateral Contract Change[C]//It Takes a Good Reason to Change a Psychological Contract. San Diago: Symposium at the SIOP Meetings,1996.
[11]Lee C,Tinsley CH. Psychological Normative Contracts of Work GroupMember in the U.S. and HongKong[R].Working Paper,1999.
[12]Pace,C. R. Measuring the Quality of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s: An Account of the Development and Use of the College Student Experiences Questionnaire[M].Los Angeles: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Institute,1984.
[13]Astin,A. W. Student Involvement -A Developmental Theory for Higher Education[J].Journal of College Student Development,1999(40) : 518-529.
[14]胡三嫚.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質(zhì)量的實(shí)證研究[J].高教探索,2012(1).
[15]Turnley WH,F(xiàn)eldman D C. Re-examining the Effects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Violations: Unmet Expectations and Job Dissatisfaction as Mediators[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0(21): 25-42.
[16]陳淑嬌.大學(xué)生社團(tuán)參與的調(diào)查與研究[J].浙江青年專修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9(1).
[17]尹潔林,徐樅巍.心理契約與員工行為的關(guān)系研究[J].北京航空航天大學(xué)學(xué)報(bào)(社會(huì)科學(xué)版),2009(9).
[18]Haworth CL,Levy PE. The Importance of Instrumentality Beliefs in the Prediction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s[J]. Journal of Vocational Behavior,2001(59).
[19]Ashforth,B.E.,&Mael,F(xiàn).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the Organiza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1989(14):20–39.
[20] Stevens J.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M]. Taylor & Francis US,2009.
[21]Robinson SL,Kraatz M S,Rousseau DM. Changing Obligations and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A Longitudinal Study[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 (1):137-152.
[22]Mael,F(xiàn)&Ashforth,B E. Alumni and Their Alma Mater: a Partial Test of Reformulated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Identification[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2(13):103-123.
[23]Williams.L.J.,&Anderson,S.E.Job Satisfaction and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as Predictors of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and In-Role Behaviors[J]. Journal of Management,1991(17):601-617.
[24]Fornell C,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1981: 39-50.
[25]CHIN WW.The Partial Least Squares Approach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J].Modern Methods or Business Research,1998:295-3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