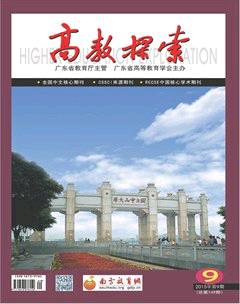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動因、過程與啟示
梁爾銘
摘要:民初高等教育學制存在的種種缺點,引發了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在教育界各方面的努力下,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終告成功,造就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學制的基本框架。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注意與國際教育潮流接軌,在高等教育領域實施雙元體制,提倡開放型高等師范教育,對當今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有著重要參考價值。同時,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過程暴露的種種問題,也值得當今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吸取教訓。
關鍵詞:壬戌學制;高等教育;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學制會議
作為學制系統中的最高等級,高等教育學制有著非同一般的地位。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學制的建立,并非由中國傳統高等教育學制逐步演變而來,而是在西學東漸的背景下向外國學習的結果。由于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學制也處在一個持續變動的過程當中。從清末的壬寅癸卯學制,到民初的壬子癸丑學制,最后是1922年制定的壬戌學制奠定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學制的基礎。考察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動因、過程及其啟示,可作為當前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參考和借鑒。
一、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動因
民國成立以后,學制改革一直是教育界的重要議題。鑒于清末頒行的壬寅癸卯學制片面模仿日本學制所帶來的弊端,民初北京政府教育部在制定壬子癸丑學制時本“擬遍采歐美各國之長,衡以本國情形,成一最完全之學制”,但“當時由歐美回國之人,專習教育者絕少,不能窺見歐美立法精神,譯出文件,大半不適用”,致使大家認為“歐美制終不適用于國情”,最后“仍是采取日本制,而就本國實際經驗,參酌定之”。[1]如果說清末尚處于君主制時代而與日本君主立憲制略有相似的話,已經進入共和體制的中華民國制定新學制時還以國情為由模仿日本學制顯然不合邏輯。
按照壬子癸丑學制的規定,高等學校分為普通教育類的大學、實業教育類的專門學校和師范教育類的高等師范學校三種類型。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閎材,應國家需要”[2]為宗旨,本科招收預科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學習年限為預科三年、本科為三或四年。在大學之上還設有大學院,供大學本科畢業合格者深造之用,其學制年限不定。專門學校的宗旨是“教授高等學術,養成專門人才”[3],預科入學資格與大學預科相同,本科招收預科畢業或經試驗有同等學力者,學習年限為預科一年、本科三年(醫科為四年)、研究科一年以上。高等師范學校以“造就中學校、師范學校教員”[4]為目的,預科招收師范學校或中學校畢業者,本科招收預科畢業者,學習年限為預科一年、本科三年、研究科一或二年。高等師范學校還另設專修科兩或三年、選科兩年以上三年以下,入學資格與預科相同。
這種形式的高等教育學制安排,存在著諸多弊端。從縱向看,大學、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均設有預科,模糊了高等教育的任務。壬子癸丑學制規定“中學畢業生不能直接進專門學校或大學本科”,“必須先入預科一年乃至三年,做種種補習的工夫,才能進入專門”,“而預科的功課又往往與中學課程相重復,在制度上缺少聯絡,在時間上也不經濟”,“此外大學預科三年殊嫌太長”。[5]預科在高等教育學制中的存在,不但增加了高等教育的年限,還使高等教育難以專心于專業教育和科學研究。從橫向看,高等普通教育、高等實業教育和高等師范教育之間地位不平等。雖然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在專業設置及課程安排方面與大學有許多相近和相似之處,但專門學校本科畢業不過相當于大學二年級肄業,研究科畢業也只相當于大學三年級到四年級水平,而高等師范學校本科畢業不過相當于大學一年級肄業,研究科畢業也只相當于大學二年級或三年級水平,專修科和選科更只相當于大學預科畢業,且二者均沒有升入大學院的途徑。兩相比較,高等實業教育和高等師范教育的地位明顯低于高等普通教育。
對于壬子癸丑學制中暴露的問題,教育界曾有過改革的提議。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是當時全國最為重要的教育組織之一,成立伊始便注意到壬子癸丑學制的缺陷。1915年4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在天津召開第一次年會。會上,各省區教育會代表紛紛要求對壬子癸丑學制進行修改,其中湖南省教育會的《改革學制系統案》被提交大會討論。《改革學制系統案》針對高等教育學制提出了三條相關建議:首先,“取消高等師范學校,而設師范研究科于大學”;其次,“除去專門學校發展之障礙,遂改專門學校入學資格及畢業時之年齡相等于大學校”;最后,“廢止大學校預科”。[6]如果按照此案所擬方法改革高等教育學制,則“現制幾乎全體推翻矣”[7],因此沒有得到大多數與會代表的贊同。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最后只是一面通告各省區教育會就學制問題進行調查,一面將該案附呈教育部備查。
在教育界的推動下,教育行政機關也注意到了壬子癸丑學制的弊端,并在細節方面進行了修正。1917年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召開了一次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與會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推崇德國學制,認為“德之高等專門學校實即增設之分科大學,特不欲破大學四科之舊例,故別立一名而已”[8]。在蔡元培的建議下,國立高等學校校務討論會通過了一項提案,這項提案得到了教育部的認可,隨即在同年9月以《修正大學令》頒布。《修正大學令》規定“大學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設二科以上者得稱為大學”,“其但設一科者稱為某科大學”[9],實質上是鼓勵專門學校升格為大學,取消專門學校與大學之間的區別。同時,《修正大學令》還規定“大學本科之修業年限四年,預科二年”[10],縮短了預科的修業年限而延長了本科的修業年限,使大學預科和本科的學習年限都趨向合理。
雖然只是對高等教育學制的局部修正且沒有涉及高等師范學校,但《修正大學令》的公布還是為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制造了輿論氛圍。對壬子癸丑學制改革的呼聲,正是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動因。
二、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過程中的爭論
1921年10月,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七次年會在廣州召開。學制問題本來應該在第六次年會上討論,只因當時正值各省區派代表赴歐美考察教育而不得不推遲到本次年會。經過一年時間的醞釀,各省區教育會已經為此次年會的主要議題學制改革做好了充分準備。廣東省教育會甚至迫不及待地進行了新學制的試驗,社會上也對新學制的到來充滿了期待。此次年會共提出了八項與學制改革有關的提案,與第六次年會的六項提案一同合并審查。由于廣東省教育會的提案最為完善且經過試驗,各省區教育會代表決定在“以廣東提案為根據”[11]的同時參酌各省提案,最后通過了《學制系統草案》(以下簡稱《廣州年會議決案》),并向社會公布征求意見。
按照《廣州年會議決案》的精神,高等教育學制仍然分為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三個組成部分。大學“不設預科”,“其入學資格以高級中學畢業者或有同等學力者為限”,畢業期限定為四年至六年,大學畢業后“得入研究院”,“不定年限”。[12]同時,“大學得附設專科,不定年限”[13]。高等專門學校也“不設預科,其入學資格與大學同”,畢業期限定為三年至四年,“其四年者待遇與大學四年畢業者同”。[14]高等師范學校“四年畢業,其入學資格與大學同”,畢業后也“得入大學研究院”。[15]另外,“大學得設師范科,高等師范得仍獨立”[16]。與壬子癸丑學制相比,《廣州年會議決案》在高等教育學制方面最主要的變化是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的趨同傾向。大學、高等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不但一致取消了預科,其學習年限也基本相同,且學生畢業后都可以進入研究院。
各類高等學校的趨同確實是大勢所趨,教育界對此項意見表示贊成的居多。但對繼續保留三足鼎立的封閉性高等教育學制設計,教育界中則有不同聲音出現。之前曾推動專門學校升格為單科大學的蔡元培表現激進,力主直接廢除高等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在蔡元培看來,1917年的《修正大學令》已經規定“凡現有高專,均為改進專科大學之準備”,高等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的存在“似皆為遷就現存之學校而存其名”。[17]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師范學院留學回來的陶行知也認為“高等師范入學的資格、畢業的程度,既然與大學相同,似宜以單科大學稱呼它”[18]。同時,他還質疑“四年的高等專門學校與四年的單科大學,究竟有什么分別”[19]。諸如此類的意見還有不少,充分反映了當時教育界對廣州年會議決案中高等教育段的不同訴求。
除教育界意見外,教育行政部門對高等教育學制的改革也有所行動。1922年7月,教育部宣布“現在學制,間有未合,以致進行諸多窒礙”,決定召開學制會議“以資征集意見,為學制改進之標準”。[20]學制會議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所議決的學制系統很有可能直接實行,因此教育界對其非常重視。當時向學制會議提交的提案,除了以時任教育總長高恩洪名義提交的《學校系統改革案》(以下稱《教育總長交議案》),還有各代表提交的相關提案五份。與代表們的提案相比,《教育總長交議案》對高等教育段的考慮更為全面,因此會議討論高等教育學制時主要以《教育總長交議案》為藍本。
雖然開幕之前“廢止‘高專的空氣彌漫京師”[21],但保留高等師范學校和專門學校的意見卻在學制會議開幕后占據了上風。作為藍本的《教育總長交議案》由傾向于保留高等師范學校和專門學校的代理教育次長鄧翠英主持制定,無形中就為保留兩者埋下了伏筆。經過激烈的爭論,學制會議以《教育總長交議案》為基礎通過了《學校系統改革案》(以下稱《學制會議議決案》)。按照《學制會議議決案》的設計,大學分為大學校和師范大學校兩種,其中大學校合設數科或單設一科均可,單設一科者“稱某科大學校”[22]。“大學校修業年限四年至六年”,“師范大學校修業年限四年”[23],都招收高級中學畢業生。而“專門學校修業四年或五年”,“高等師范學校修業四年”,均為“初級中學四年畢業者入之”,[24]僅比高級中學的程度高兩年到三年,事實上降低了程度。高等專門以上學校還“得附設專修科”,“不定年限”。[25]大學院則為“大學畢業者及具有同等程度者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無定”。[26]如果愿意提高程度改招高級中學畢業生,專門學校“得改為單科大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得改為師范大學校”。[27]盡管《學制會議議決案》名義上還規定“專門學校與單科大學校,高等師范學校與師范大學校,均得并設于一校”[28],但實際上專門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已經因程度問題而與大學變成兩個不同層次的教育階段。這種高等教育學制設計既與《廣州年會議決案》中專門學校、高等師范學校和大學并列的設計有著明顯的不同,也與現實中專門學校和高等師范學校逐漸提高至大學程度的情況有所差異。
《學制會議議決案》通過后,如何對待該案成為棘手事情。新任教育總長湯爾和“擬將議決案送往濟南征求全國教育會同意,以昭特別鄭重之意”[29],這為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最后定案時發生的糾紛埋下了伏筆。
三、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定案
學制會議結束后不久,全國教育會聯合會也在濟南召開了第八次年會。教育部代表在開會前曾將《學制會議議決案》和《教育總長交議案》各一百份交給大會主席許名世,但許名世卻一時糊涂沒有將兩案的關系交代明白,致使代表們以為《教育總長交議案》是交給此次年會的提案。《教育總長交議案》上開首即表示,“查現行學校系統,系民國元年臨時教育會議議決,經本部采擇公布”,“施行已來,已歷十載”,“茲已時勢變遷,不無應行修改之處”,[30]完全不提之前的《廣州年會議決案》。這段引子導致了各省區教育會代表的強烈不滿,浙江省教育會代表許倬云甚至表示:“教育部既不睬我們,我們也只有不睬他。”[31]最后幾經調停,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八次年會才確定審查底案“精神上大部分用廣州案,而詞句上多采用學制會議案”[32],并推舉在調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胡適擬訂了一份《擬修正學制系統草案》,還組建了甲組審查會負責審查此案。
《擬修正學制系統草案》在高等教育段的最大特色就是取消了高等師范學校的獨立存在,并且不設降低程度的專門學校。草案擬訂者胡適主張“高等師范只依舊制存在,不列入系統圖,刪去了學制會議降低一年的高等師范”[33]。同時,胡適覺得“學制會議對于師范大學的規定,最為不通”,于是在草案中設計“師范大學為單科大學之一種,收受高級中學畢業生,修業四年”[34],以便與其它大學保持一致。另外,胡適還認為:“學制會議降低了專門學校一年,收受初級中學畢業生,這是和廣州案的精神大背的,故這里仍依廣州案,提高二年。”[35]
《擬修正學制系統草案》擬定后,審查員們進行了逐條審查,并為此展開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黃炎培力主“保存高等師范,收初中畢業生,三年畢業者,修業五年,四年畢業者,修業四年”[36],為此與草案擬訂者胡適數次辯駁。一番爭論之后,甲組審查會終于對高等教育段的學制達成了較為一致的意見。雖然“高等師范不列入新學制一條,也頗有異議,但結果仍依底案,不列入學制”,又新增規定“大學校與師范大學設二年期之師范專修科”。[37]討論完畢后,甲組審查會推舉袁希濤、胡適和許倬云為起草員,根據討論結果起草修正案。修正案提交大會進行三讀討論時,高等教育段的學制設計引發了大爭論。初讀開始之前,即有浙江省教育會代表胡炳旒表示異議,認為“就本草案條文看,是無形中廢止專門和師范,減少求學者之機會”,“因為專門和師范增加年限,依現在情形觀之,社會之需要,經濟之困難,均屬難于進行”[38]。二讀開始以后,專門學校的存廢問題又引起了與會代表對高等教育段學制的激烈討論,但結果除經亨頤提議的刪去舊制高等師范學校“或改為大學之教育科”一條和經亨頤、許倬云提議的增加“職業學校畢業生亦得入專門學校”一條被采納外,其余皆按原案進行。[39]三讀時各省區教育會代表無異議通過,將此案定名為《學校系統案》,并推舉袁希濤為代表將詳細經過情形報告教育部。
11月11日,時任中華民國大總統黎元洪將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八次年會議決的《學校系統案》以《學校系統改革案》名義發表,標志著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定案的完成。《學校系統改革案》以大學校為高等教育段的主干,專門學校輔之,其中大學校“設數科或一科均可”,“其單設一科者稱某科大學校,如醫科大學校、法科大學校、師范大學校之類”。[40]大學校招收高級中學畢業生,修業年限為四年到六年。專門學校則同時招收高級中學和職業學校畢業生,修業年限為三年以上,“年限與大學校同者待遇亦同”[41]。另外,“大學校及專門學校得附設專修科,修業年限不等”[42]。為了補充初級中學教員的不足,也“得設二年之師范專修科附設于大學校教育科或師范大學校”,“亦得設于師范學校或高級中學,收受師范學校及高級中學畢業生”。[43]在大學校之上還設有大學院,“為大學畢業及具有同等程度者研究之所,年限無定”[44]。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定案,使歷時數年的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終于告一段落。
四、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啟示
(一)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應注意與國際教育潮流接軌
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十分注意博采眾長,不再信奉原先出于政治因素而仿效的日本模式,轉而選擇與當時世界高等教育潮流接軌,確實是一場力圖追趕教育現代化趨勢的改革。這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廢止了預科的存在,大力提高職業教育和師范教育的地位,使之與普通教育在高等教育領域得以齊頭并進,都與當時世界高等教育發展的潮流相符。特別預科的廢止,更是符合了當時世界各國高等教育學制“提高中學程度”、“不設大學預科”[45]的發展態勢。正因注意與國際教育潮流的接軌,才使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奠定了中國現代高等教育學制的基礎,并成為近代以來中國高等教育中影響最大的學制框架。20世紀50年代,我國再度因政治的緣故而模仿蘇聯的高等教育學制,由此帶來的后果就是高等教育學制體系被重新架構,走向了一條與世界高等教育發展主流異途的道路。直到改革開放以后,我國高等教育學制才重新開始與國際教育潮流接軌。近年來,國際高等教育發展的趨勢對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影響越來越大。借鑒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的經驗,當今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應注意與國際教育潮流接軌,才能保證高等教育發展的先進性。
(二)高等教育學制中應同時容納科研型大學和應用型大學
大學校和專門學校的平行設置,是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在設計上的特色。除了多科性大學校和醫科大學校、法政大學校、師范大學校等分科大學校外,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中還設有與之對應的各種專門學校。大學校以培養研究型人才為目的,是主要施行普通教育的研究型大學。而專門學校以培養技能型人才為目的,事實上是中等職業學校的延伸,屬于職業教育領域的應用型大學。按照1922年新學制的規定,大學校與專門學校地位基本相等。更為重要的是,專門學校除了招收高級中學畢業生外還招收職業學校的畢業生,打通了中等職業教育與高等教育之間的通道。最近教育界對于本科高校轉型十分關注,在高等教育領域實行研究型大學與應用型大學并存的雙元化體制已成共識。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領域正在加快構建以就業為導向的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立學分積累和轉換制度,打通從中職、專科、本科到研究生的上升通道,引導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由于我國現行高等教育學制對此尚無匹配措施,相關高校向應用型大學轉型無據可依,中等職業教育畢業生進入高等教育渠道也極窄。參考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中的相關設計,在學制系統中同時容納科研型大學和應用型大學,保持職業教育領域升學渠道的暢通,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
(三)高等師范教育學制設計應由封閉型走向開放型
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除了將高等師范學校升格為師范大學校外,還規定多科性大學也可以設立師范科,為高等師范教育設計了一個開放靈活的培養體系。該體系打破了以往封閉的師范教育模式,將高等師范教育的范圍從單科性的師范大學校擴充到多科性大學中去。它既為有志于從事教育行業的普通大學生提供了師范技能訓練的途徑,又大大提高了師范大學生的學科知識水平,使中國高等師范教育模式走向了多元化。新中國建立后,按照蘇聯模式重新建構了一套封閉型的高等師范教育體系,使中國高等師范教育的開放性趨向被迫中斷。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封閉型高等師范教育體系越來越難滿足教育界對教師綜合素質的要求,因此國家層面對建立開放型高等師范教育體系的關注在新世紀前后開始出現。1999年6月,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出“鼓勵綜合性高等學校和非師范類高等學校參與培養、培訓中小學教師的工作,探索在有條件的綜合性高等學校中試辦師范學院”[46]。2012年9月,教育部、國家發改委和財政部又聯合發文鼓勵綜合大學發揮學科綜合優勢“參與教師教育”。盡管當時情形與今天高等師范教育的現實不盡相同,但建立開放型高等師范教育體系正是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追求的目標之一,在此背景下借鑒其指導思想仍然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
(四)高等教育學制改革應有相應措施保證各類高等教育發展的均衡性
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在制度設計上無疑是成功的,但在具體實踐上卻產生了某些問題。職業教育類的專門學校在設計上本來是高等教育中與普通教育類的大學校并駕齊驅的力量,但實際情況卻非如此。1922年學制改革以前全國有公立大學9所、私立大學7所[47],到1926年全國已有公立大學27所、私立大學15所[48];而1920年全國有公立專門學校58所、私立專門學校17所[49],到1926年全國只有公立專門學校41所(含高師1所)、私立專門學校9所[50]。大學數量急劇增加而專門學校數量不斷減少的重要原因,便是“由于十一年(1922年)頒布新學制,原有專校多改辦大學故也”[51]。特別是依舊制設立的8所高等師范學校本“應于相當時期內提高程度”[52]獨立升格為師范大學校,但最后只有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師范學校向著獨立的師范大學發展,其余6所高等師范學校幾經周折全部改建或合并成多科性大學。各類高等教育之間發展比例失衡局面的出現,要歸咎于“新學制對于大學設立之規定極寬”[53],致使各高等學校往往不顧自身實際條件而借調整之機進行升格。目前我國高等教育也遇到了不同類型高等教育之間發展比例不協調的問題,包括師范院校在內的眾多高等專門院校紛紛升格為大學,且大多數出現了向綜合性大學發展的趨勢。吸取1922年高等教育學制改革實施過程中的教訓,我們應切實制定相關措施以保證各類高等教育的均衡發展。
參考文獻:
[1] 蔣維喬.清末民初教育史料(節錄)[G]//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匯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1073.
[2] 教育部.大學令[J].政府公報,1912(178).
[3] 教育部.專門學校令[J].政府公報,1912(176).
[4] 教育部.師范教育令[J].教育部編纂處月刊,1912(1-3).
[5] 商務印書館.新學制學校課程說明書(第1編總論)[M].上海:商務印書館,1923:1-3.
[6][7] 湖南省教育會.改革學校系統案[G]//舒新城.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2冊).上海:中華書局,1933:68,66.
[8] 蔡元培.大學改制之事實及理由[J].新青年,1917(3-6):1.
[9][10] 教育部.大學令[J].教育公報,1917(4-15).
[11][12][13][14][15][16] 全國教育會聯合會.第七次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會務紀要[M].廣州:全國教育會聯合會,1921:39,45,45,45,46,46.
[17] 蔡元培.全國教育會聯合會所議決之學制系統草案評[J].新教育,1922(4-2):126.
[18] 陶行知.新學制與師范教育[J].新教育,1922(4-3):379.
[19] 陶行知.中國建設新學制的歷史[J].新教育,1922(4-2):256.
[2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教育部公布學制會議章程[G]//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57.
[21] 陶行知.教育部學制會議經過情形[J].教育匯刊,1923(5).
[22][23][24][25][26][27][28] 教育部召集之學制會議及其議決案[J].教育雜志,1922(10):2.
[29] 抱一.學制會議之經過[N].申報,1922-10-04(6).
[30]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部交議案[G]//.中華民國檔案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84.
[31] 第八屆教育聯合會開幕紀[N].申報,1922-10-14(7).
[32][33][34][35][36][37] 胡適.胡適日記全編(3)(1919-1922)[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843,843,844,844,838,844.
[38] 第八屆教育聯合會紀事(二)討論學制草案[N].申報,1922-10-22(10).
[39] 第八屆教育聯合會紀事(三)學校系統案三讀通過[N].申報,1922-10-23(7).
[40][41][42][43][44][52] 大總統令[J].政府公報,1922(2393).
[45] 金曾澄.廣東提出學制系統草案之經過及其成立[J].新教育,1922(4-2):180.
[46] 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Z].中發[1999]9號文件,1999-06-13.
[47][49][51][53] 教育部教育年鑒編纂委員會.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丙編教育概況)[M].上海:開明書店,1934:23,145,23,17.
[48][50] 教育部公布全國公立私立專門以上學校一覽表(1926年7月)[G]//中華民國檔案史檔案資料匯編(第三輯·教育).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199-203,199-203.
(責任編輯鐘嘉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