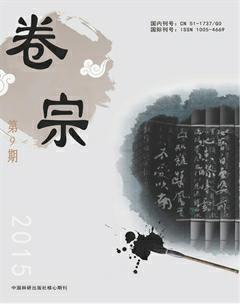從上博簡《孔子詩論》再思《木瓜》篇主旨
王韻
摘 要:上博簡《孔子詩論》的面世,為研究《詩經(jīng)》提供了新的重要出土材料。其中第18-19號簡,是孔子對于《詩經(jīng)·衛(wèi)風(fēng)·木瓜》的評析。據(jù)《孔子詩論》,《木瓜》篇的主旨是表現(xiàn)一類人心中埋藏的愿望沒有得到表達(dá)時的怨憤情緒。孔子對《木瓜》詩義的解釋,大大顛覆了人們對《木瓜》一詩的傳統(tǒng)認(rèn)識,讓我們再次深入思考《木瓜》詩的主旨。
關(guān)鍵詞:《孔子詩論》;《木瓜》;主旨
1994年出現(xiàn)在人們視野中的戰(zhàn)國楚竹書為學(xué)術(shù)界提供了新的研究材料。這批竹簡為戰(zhàn)國晚期的楚墓隨葬品,經(jīng)檢測確定為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212年焚書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戰(zhàn)國古籍,內(nèi)容涉及廣泛。其中包括了戰(zhàn)國佚書《孔子詩論》。
1 對《詩經(jīng)·衛(wèi)風(fēng)·木瓜》篇內(nèi)涵的傳統(tǒng)認(rèn)識
從古到今學(xué)者們對《木瓜》篇的解說頗多。傳統(tǒng)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大致分為三類。一是依照毛詩序之說,賦此詩以政治內(nèi)涵:“《木瓜》,美齊桓公也。衛(wèi)國有狄人之?dāng)。鎏幱阡睿R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wèi)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以后論者多從之。二是宋代大儒朱熹,始疑“美齊桓公”之說不妥,《詩集傳》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如《靜女》之類。”三是姚際恒的看法,他在朱熹的基礎(chǔ)上更進(jìn)一步,《詩經(jīng)通論》說“且詩中皆綢繆和好之音,絕無諷背德意。《集傳》反之,謂‘男女相贈答之詞,然以為朋友相贈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目前學(xué)術(shù)界普遍將此詩釋為男女相好而相互贈答,并且反映出了先秦時期贈玉的民俗文化信息。
2 上博簡《孔子詩論》對《木瓜》篇的評論
上博簡《孔子詩論》的面世,大大顛覆了人們對《木瓜》一詩的傳統(tǒng)認(rèn)識。《孔子詩論》中對《木瓜》的評析出現(xiàn)在第18-19號簡上。18號簡內(nèi)容為:“因《木瓜》之保(報)以俞(喻)其悁者也。《折(杕)杜》則情憙其至也。”19號簡內(nèi)容為:“……(溺)志,既曰‘天也,猶又(有)悁言。《木瓜》又(有)藏愿而未得達(dá)也。因……”李學(xué)勤認(rèn)為,19號簡末端與18號簡的首段可以連綴成文,故19號簡應(yīng)該排在18號簡之前。 兩支簡評《木瓜》之文,翻譯過來就是“《詩》的《木瓜》篇的主旨是表現(xiàn)一類人心中埋藏的愿望沒有得到表達(dá)時的情緒。可以根據(jù)《木瓜》篇的‘報看出他內(nèi)心的憤懣。”這種對詩旨意的解釋令人意外。傳統(tǒng)說法無論是“美齊桓公”,還是“男女相贈”,抑或是“朋友相贈”,都是一種美好的感情,是雙方“永以為好也”的良好祝愿。但是《孔子詩論》的說法顯然已經(jīng)變美為刺,詩中的諷刺意味大有深意。王夫之曾云《木瓜》深意:“《木瓜》得以為厚乎?以《木瓜》為厚,則人道之薄亟矣!厚施而薄償之,有余懷焉;薄施而厚償之,有余矜焉。故以瓊琚木瓜,而木瓜之薄見矣;以木瓜絜瓊琚,而瓊琚之厚足以矜矣。見薄于彼,見厚于此,早已挾匪報之心而責(zé)其后。故天下之工于用薄者,未有不姑用其厚者也。而又從而矜之,曰‘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報之量則已逾矣。……惡仍之而無嫌,聊以塞夫人之口,則瓊琚之用,持天下而反操其左契,險矣!”依王夫之所言,《木瓜》篇“報之以瓊琚”,并非友好之報也,而是謀取如債權(quán)人一般的優(yōu)越地位,表面上看起來是以厚報薄,似為敦厚之舉,實(shí)則工于心計(jì)以塞他人之口,目的只在自己穩(wěn)操勝券,在形勢上壓倒、控制對方,這種人可謂陰險之至了。這樣一解釋,此詩的味道就完全變了。王夫之自然沒有見過《孔子詩論》,然而他的這番說辭不可不謂之洞見。如今《孔子詩論》重現(xiàn)于世,王夫之之論旨竟可與之相合。簡文中明確指出《木瓜》中有“藏愿”,即是“工于心計(jì)之人貶低別人抬高自己的心愿”,晁福林《上博簡<詩論>研究》中指出,這種人“嘴上高唱‘匪報也,永以為好也,心中實(shí)隱藏著厚報于己的圖謀。他的‘報厚 是假,以售其奸則是其真。”“他們以‘厚報為幌子,一方面貶低了別人(“投我以木瓜”的薄施者),另一方面又借以樹立了自己的高大形象,把自己扮成忠厚君子。
3 《木瓜》中的苞苴之禮
《孔從子·記義》中有一段孔子論說《詩經(jīng)》之文,歷來被學(xué)者們引用。其中就有孔子評《木瓜》之語:“吾于《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包且,即苞苴,是用茅葦編成的用于包裝物品的包裹。從這里我們也能夠窺探出先秦時期的禮儀風(fēng)俗。中國自古為禮儀之邦,禮品本是溝通雙方友好往來的一種方式。《木瓜》中表達(dá)的似乎的確是這樣一種雙方互贈物品、以求結(jié)好的美好意愿。但是參考到上博簡中孔子對《木瓜》的批評態(tài)度,孔子這句“吾于《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的評語恐怕需要認(rèn)真審視。苞苴之禮,亦見于先秦時其他典籍。《荀子·大略》載:“湯旱而禱曰:‘政不節(jié)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宮室榮與?婦謁盛與?何以不雨至斯之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莊子·列御寇》中有云:“小夫之智,不離苞苴竿牘”,意思是匹夫之智僅限于送禮致信這樣的事。可見,苞苴之禮的盛行并非小事、美事,相反還是十分惡劣的事,是直接影響政治風(fēng)氣的重大事件,先秦諸子對它多有批判。苞苴之禮,大致相當(dāng)于今天所說的行賄受賄。來而不往非禮也,但是任由最初的禮儀風(fēng)俗演變發(fā)展為行賄受賄、營私牟利的收買行為,其中的味道就變了。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禮,大人弗為”,說的正是這個意思。孔子從《木瓜》中看出了“苞苴之禮”,顯然是持批判態(tài)度的,是帶有強(qiáng)烈政治針對性的。
4 對《木瓜》主旨的再思考
由上可以看出,從對《木瓜》主旨的傳統(tǒng)認(rèn)識到上博簡《孔子詩論》的面世,人們對《木瓜》篇主旨的解讀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從不同的角度解讀似乎都有道理。之所以能夠產(chǎn)生眾多解讀,這關(guān)系到文學(xué)作品的創(chuàng)作和接受問題。正如一千個讀者就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不同時代的不同人解讀《木瓜》,就會有不同的認(rèn)識。我們知道,《詩經(jīng)》,尤其是《國風(fēng)》,多是民歌,隨口唱來,猶如天籟。《詩經(jīng)》的編纂成書,也經(jīng)過了民間“采詩”、士大夫“獻(xiàn)詩”和孔子“刪詩”。這些原始的民歌經(jīng)文人整理潤色,在思想內(nèi)容上必然也會有所闡釋發(fā)揮,反映著編纂人的思想意識。《木瓜》一詩,重章疊沓,讀起來朗朗上口,詩意淺白,感情樸素真摯,應(yīng)是民歌無疑。但是在歷史流傳并經(jīng)典化的過程中,產(chǎn)生了完全不同于原始創(chuàng)作時期的意義,被賦予了強(qiáng)烈的政治色彩,在主旨內(nèi)涵上被改造,這應(yīng)該說并非是創(chuàng)作的原意,而是讀者的接受問題。與我們所有后人一樣,面對《木瓜》,孔子同樣是一個讀者。孔子對《詩經(jīng)》的態(tài)度,最重教化功能,詩可以“興”、“觀”、“群”、“怨”。在《論語》中,就有孔子對《詩經(jīng)》中“繪事后素”和“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之句的解釋。孔子的解釋斷章取義,完全拋開了原詩的本義,自由發(fā)揮,將其涵義的解讀服務(wù)于詩歌的政治教化功能。現(xiàn)今面世的上博簡《孔子詩論》中對《木瓜》篇的批評,再一次印證了孔子的這種解詩方式。可以說,從一首樸素自然的原始民歌演變?yōu)槿寮医?jīng)典,《木瓜》給我們透露出的信息是多角度、多方面的。原始的詩歌創(chuàng)作完成以后,在流傳過程中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它會經(jīng)歷讀者的再創(chuàng)作,甚至是多次創(chuàng)作,即讀者會賦予詩歌自己的理解和新的涵義。《木瓜》一詩既保留著原始民歌的色彩,又有孔子賦予的政治批判意義,同時還體現(xiàn)出了先秦時期贈玉的文化習(xí)俗。故而在解讀詩義時不應(yīng)以一概全,只見一面,而是要看到多種解釋的合理性。
參考文獻(xiàn)
[1]朱熹.詩集傳[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2]韓高年.詩經(jīng)分類辨體[M].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3]晁福林.上博簡《詩論》研究.商務(wù)印書館,2013.
[4]張利軍.從上博簡《詩論》評析《木瓜》看周代貴族社交禮俗演變[J].古籍整理研究學(xué)刊,2010年7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