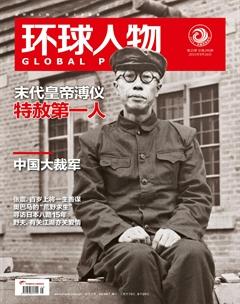難民潮前的慷慨與吝嗇
陶短房
9月2日,年僅3歲的敘利亞小難民艾蘭·庫爾迪在偷渡途中溺死,遺體俯臥在土耳其海灘上的照片頃刻間傳遍世界,并引發被稱為“足以改變各國對地中海難民態度”的連鎖反應。
事件發生前,歐洲各國對難民態度復雜。由于接連發生難民死亡事件,歐盟飽受指責,但地中海沿岸國家又無力接納更多難民。因此,歐盟委員會今年5月推出強制性的“難民配額”,希望較富裕的西歐、北歐國家多接納難民。但只有德國等少數國家表示謹慎歡迎,英、法等國持抵觸態度,東歐國家更堅決反對。
但“9·2”事件改變了一切。9月5日起,涌入德國的敘利亞難民3天內超過3萬。9月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拿出“大禮單”:2016年額外撥出6億歐元用于安置難民,在已宣布的30萬套難民安置房基礎上增建15萬套。德國輿論稱, “默克爾媽媽”的慷慨將導致今年80萬難民涌入德國,“整個德國將為此改變”。原本態度保守的法國和英國也出現微妙變化。公開宣稱“絕不認同配額”的法國總理瓦爾斯改口稱“對難民的不幸忍不住熱淚盈眶”,內政部長卡贊紐夫宣布將在兩年內額外接納2.4萬難民。英國首相卡梅倫則表示,“愿意根據情感和能力的綜合考量自愿接納一些難民”。其他政要也紛紛作出姿態,教皇方濟各呼吁各教會接納難民,芬蘭總理西皮萊宣稱讓出官邸供難民安置用,大西洋另一端的加拿大也坐不住了,魁北克省移民部長韋爾宣布將接納的難民數量增加3倍。唯有美國態度耐人尋味,一方面鼓勵歐盟接納更多難民,另一方面再三強調“美國不會這樣做”。
在難民問題上,各國的慷慨和吝嗇都有緣故。
德國經濟狀況較好,但人口老齡化嚴重,執政黨一直主張引進難民,解決勞動力缺口。作為實用主義政治家,默克爾一貫善于根據民意調整政策。“9·2”事件發生前,德國反對接納難民的聲浪不小,她曾當眾拒絕一位巴勒斯坦難民小女孩的懇求。但這次,公眾普遍同情難民,既希望連任又希望擺脫“冷漠無情”形象的默克爾,如何選擇不言而喻。
英法情況則不同:法國執政的社會黨向來主張寬容對待難民,但奧朗德上臺后,面對國內反難民的輿論,不得不主張控制。此次事件讓難民獲得大量同情分,社會黨政府就借機“回擺”;英國則正相反,執政的保守黨素來對接納難民不感冒,但迫于“政治正確”的壓力,不得不“意思意思”。加拿大本來就是難民接收大戶,但此前公眾對難民擠占福利不滿,迫使政府推出所謂G5原則,要求境外難民至少得到5位加拿大公民或永久居民擔保。小庫爾迪住在加拿大的姑姑就是因為湊不齊5個擔保者,庫爾迪一家才冒險“下海”并釀成悲劇。換言之,加拿大對悲劇負有間接責任。因此,事發后各政黨紛紛表態顯示“政治正確”。
而美國則相反:“9·2”事件的“催淚效應”并不顯著,社會對難民沖擊波普遍不滿,總統選戰期間一些候選人為迎合民意,競相拋出在邊界修筑“長城”、阻止難民入境的競選噱頭。在這種背景下,當然不會有人去倡導接納更多難民。
“難童催淚彈”的效應注定是短暫的,接納大量難民帶來的社會問題、宗教磨合卻是長期的。一旦催淚效應不再,現實糾紛頻發,情況又會如何?其實,現在歐洲就已經出現不同聲音,英國反對接納更多難民的民調又掉頭向上,法國也出現了公開表示要“選擇性接納難民”的市鎮長官。在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澤霍夫呼吁默克爾“慎重考慮”,東部各州更接連發生針對難民庇護所的襲擊事件。默克爾已經表示,此次的慷慨不過是“救急的權宜之計”。
可想而知,一旦人們忘記了那張催人淚下的照片,輿情、選情都可能逆轉,那些在“催淚彈”下秀出的慷慨,恐怕又會發生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