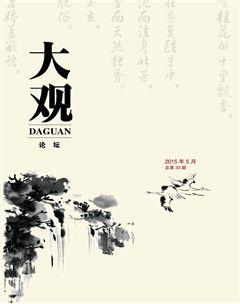溫可錚的歌唱藝術道路
摘要:聲樂藝術是集音樂、文學、戲劇于一身的表演藝術。它既要求歌唱者掌握聲樂演唱技巧,又要求歌唱者具備深厚的文化修養。溫可錚豐富的閱歷和深厚的藝術修養鑄就他成熟高雅的藝術觀。
關鍵詞:溫可錚;聲樂;書畫
一、童年時光與青年求學之路
溫可錚1929年2月17日出生于北平(今北京)一個書香門第。父親溫志賢當年是北京城里的著名律師,他的父親喜愛文學,又是書畫收藏家,對音樂有特殊的愛好,同時也喜歡京劇﹑昆曲﹑京韻大鼓。溫可錚受父親的影響,6歲就正式拜京劇明令楊小樓的女婿劉硯亭為師,學老生,每天早上就練功吊嗓子,7歲時溫可錚隨父親的一班京劇朋友玩票登臺出演《法門寺》,并一人反串三個人的角色,連唱帶表演。
溫可錚天資聰穎,又深受其家庭的影響,逐漸對音樂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和感情。他從小就跟著唱片學唱歌,9歲時被選拔進華北兒童合唱團唱童聲男高音,10歲時以一曲意大利名曲《愛情的喜悅》獲“天才兒童獎”第一名金獎。從此他迷上了歌唱,小學三年級的作文《我的志愿》里寫道:我的志愿是當歌唱家。
1940年溫可錚考入富有音樂傳統的北平育英中學,且經常參加歌詠團的活動。1946年中學畢業后,他立志以音樂為終生事業,雖然歌唱得不錯,可他的父親并不同意溫可錚搞聲樂。他父親覺得男孩子唱歌沒有出息,而更愿意溫可錚學數學、學理工或者做工程師、律師、醫生。但是如果在家玩業余的那他父親喜歡,就是認為不能學。——因為那個時代搞藝術的人地位地下,說不好聽的那就叫作戲子。溫可錚性格倔犟,認定了從事藝術的道路。他立志一定要學成個聲樂教授和別的教授一樣在學校里教書,要不當教授就不回家。1946年17歲的溫可錚考入了南京國立音樂院,師從俄籍教授蘇石林(1894—1978)學習聲樂。蘇石林是國際著名的聲樂大師,他對溫可錚的聲樂藝術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溫可錚跟隨蘇石林學習聲樂長達十年之(1946—1956)。“蘇石林教授雖是俄籍,但他的歌唱卻遵循意大利19世紀著名的弗蘭西斯科﹒蘭貝爾蒂聲樂學派。我在教授親自指導下學習整整十年。”[1]在溫可錚眼里蘇石林教授是一位音樂界公認的聲樂教育家,更是一位了不起的聲樂藝術大師。“或許因為師生都是男低音,也或許因為溫可錚是師從蘇石林時日最久的學生,更因為溫可錚的穎悟和刻苦,他是蘇石林最器重最疼愛的一個學生,師生情誼十分深厚。”[2]1956年—1958年保加利亞聲樂教育家契爾今教授在北京上海任教時,溫可錚又從其學習了兩年。
二、堅韌走出文革迫害,再創藝術輝煌
在這混亂的年代溫可錚受到造反當權派的無端指責,受到非人的虐待。造反派們搶走了他多年潛心積累下來的聲樂筆記,同時對他進行毒打。在學校里挨打成了他的家常便飯,天天挨打使他不知道明天怎么過,身邊一會這個教授死了,一會那個教授自殺了……溫可錚把他的安眠藥攢成了一瓶對愛人王俅說,他活不了了。王逑對溫可錚說,你要死我陪你死但死之前得把話說清楚,你小學一年級寫作文說將來長大要成為偉大的歌唱家。因為父親不同意你還寫了血書,你的理想實現了沒有?
妻子王逑用溫可錚對歌唱的熱愛救活了溫可錚,而溫可錚則用響亮的歌聲,證明了他一生的藝術理想與輝煌成就。溫可錚重新振作了起來,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抓緊時間練習發音和咬字。溫可錚的歌聲里有喜怒哀樂,因為那里融合著他自己的感情。而在文革結束后的音樂會上他的歌聲更多的則是感動。
十年“文化大革命”之后溫可錚的歌聲又回到了祖國的各地舞臺。他以更成熟的風采,大展抱負,將他的歌唱藝術漸漸推向頂峰。他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演出并擔任獨唱,在各地多次舉辦音樂會,到各大音樂院校及藝術團體舉辦聲樂藝術講座及聲樂匯報演出,走出國門舉辦音樂會,舉辦聲樂大師班,進行藝術交流。
三、深厚的藝術修養--溫可錚與書畫
有些歌唱家多有好的聲音,但是就是不耐聽,經不起品。究其原因是他們忽視了與歌唱關系密切的文化品位和個人文化修養而僅僅局限在響亮的聲音里。其實當文化積累養成的高雅品位能夠融入歌聲里的時候,歌的品質就能得到升華。溫可錚就是一位擁有豐厚文化修養的歌唱家。他喜歡書畫,小時候就在表叔的指導下練過。他的表叔叫秦中文,是民國時期有名氣的畫家,曾擔任北平藝專的國畫系主任,他常常帶著畫界的朋友到溫可錚家做客,閑談神聊無不散發著濃濃的文人風雅。他指導年幼的溫可錚畫畫,耳聞目染,溫可錚從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書畫藝術熏陶。溫可錚的夫人王逑老師出身于江南常熟名門望族,清代吳門畫派著名“四王”中的王石谷是王逑老師的前十一代先人,書香門第的家世源遠流長。王逑老師的父親也精于書畫鑒賞,家中也有不少珍品,自己也善于畫梅。東床豈不受泰山的影響?溫可錚自然從中獲益匪淺。
溫可錚說過:“歌唱和音樂本身就是有聲的詩詞書畫,而詩詞書畫則是無聲的歌唱和音樂。他們的藝術境界是密不可分的”。[3]溫可錚先后創作了一批書畫作品,在上海音樂學院,新加坡和紐約聯合國大廈舉辦過書畫展,還出版成冊,這在歌唱家中是少有的。“他的《靈石清供》有幾分宋人的筆意,《墨荷清汽》則有白石的清淡,仿石濤的《山居空寂》不夠枯,《怪石雨竹》竹太弱,《仿古仕女》隱隱約約有幾分吳道子的風格,而《百代畫圣吳道子》卻讓人想起范曾。”[3]
掌握一定的歌唱技術并不難,難的是在聲音里表現的韻味和精神,把聲音唱響亮并不難,難得是聲音里表現出來的情感和氣質。這種精神和情感是依托在聲音技術之上但卻是來自技術之外的藝術修養和人的品質。藝術是相通的,溫可錚廣博的文化視野,潛移默化的滲透于他的歌唱。他能把《懷念曲》,《我住長江頭》,《花非花》這些旋律線條簡潔的歌曲唱出連綿不斷的,類似書畫中重筆濃墨的凝重線條長而內力穩重,含而不發,緊緊扣住人的心弦是與他深厚的文化修養分不開的。
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溫可錚對生活的要求卻顯的很隨意,吃飯不挑食,睡覺不挑床,衣著隨意只要得體,舒服就行。溫可錚經常開懷大笑,笑得暢快淋漓,他也時常被感動,感動的淚水盈眶。他是個感情豐富而且善于表露的人,他說過一個人的品位不是表現在表面的,生活可以簡單樸素些,但藝術要精益求精,人的精神世界要豐富多彩。可見,豐富的閱歷和深厚的藝術修養鑄就溫可錚成熟高雅的藝術觀。
【參考文獻】
[1]溫可錚.吉利與貝爾·康托[J].音樂愛好,1990(01):5
[2]程乃珊.白俄聲樂教授哦蘇石林和他的中國學生溫可錚[J].檔案春秋,2007(10):52
[3]俞子正.生命的詠嘆[M].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2007:58
作者簡介:張兵,河南開封人,碩士研究生,鄭州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研究方向:音樂學(聲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