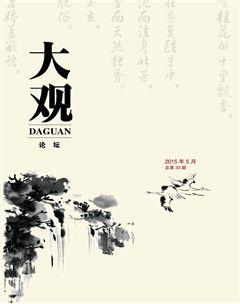試論文人介入對京劇流派的影響
王雪瑩
通常來講,流派是指具有相同藝術風格的藝術家群。然而我國的京劇流派則多指京劇表演風格上形成流派。京劇演員在表演上形成獨特的藝術風格并有追隨者模仿學習發生在清末民初,但“京劇流派”的概念是陳培仲先生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提出的。
“京劇藝術領域內所講的流派,往往是指流派創始人在他們所演出的一系列的劇目中,在他們的唱腔和表演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的創作個性和獨特的風格。……都以其獨有的音調和色彩,給觀眾以不同的審美享受,而得到觀眾的承認、同行的贊許和后學的模仿,其中特別是由于后學者的師承、學習和模仿,使得流派創始人的藝術,得以推廣開來、流傳下去,從而形成流派藝術。”[1]結合陳培仲先生的觀點以及歷來研究成果,對于京劇流派我們可以總結出兩個特點:1、京劇流派具體指在京劇表演上,且是個人表演的風格化擴散到群體;2、這種藝術風格備受大眾喜愛推崇的同時,也得到師承、流播。
京劇流派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京劇最早的三大流派——徽派、漢派、京派,與其說是結合程長庚、余三勝、張二奎三位演員的藝術表演風格區別確立的,毋寧說是按照地域籠統劃分。事實上,到了譚鑫培時期才逐漸確立了以個人表演風格為主的流派——譚派。而對于譚派的傳承影響最大的文人則非陳彥衡莫屬。
陳彥衡曾為譚鑫培做琴師,琴藝高超,享有“胡琴圣手”、“第一琴師”等美譽。然而陳彥衡做琴師實屬客串性質,他更為擅長的是案頭工作。不過這“案頭”也與尋常不同,因陳彥衡從不曾編寫劇本,也不參與劇本修改工作。
陳彥衡對譚腔研究至深,雖然當時“無腔不學譚”,但是卻沒人能比陳彥衡對譚腔更加了若指掌,包括譚鑫培本人也未必能將自己的技藝條分縷析述說清楚。再加上譚鑫培從不收徒,所以后輩余叔巖、言菊朋等名家雖說師出譚派,其實一唱一和、一板一眼多是從陳彥衡處學來。
陳彥衡將譚鑫培演出的諸多劇目記錄下來,并用“工尺譜”整本大段地記錄譚腔。工尺譜是中國民間傳統的記譜方法之一,但是用工尺譜記錄京劇,陳氏卻是首創。陳彥衡記錄的曲譜,工尺細密,板眼符號予以詳細注解,細致入微地標明譚鑫培的唱法。尤為可貴的是,陳彥衡沒有門戶之見,同樣也記錄了其他名角唱腔。
1918年譚鑫培故去,陳彥衡著《說譚》一書聊以紀念。《說譚》并非譚鑫培個人傳記,而是研究皮黃聲韻和譚鑫培唱念技巧與表演精神的著述。此書是對譚派的唱腔風格進行系統的整理,為今后的專業研究留下珍貴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文字資料。稍有遺憾的是,《說譚》在總結分析譚鑫培個人唱腔時,褒揚之詞溢于言表,但并沒有提出一個標準作為譚派準則,因此不能將其看作譚派技法規范。
當然,瑕不掩瑜,對于陳彥衡與他的《說譚》我們應報以肯定態度。雖然陳彥衡不是譚派教習師,《說譚》也非派中“修煉秘笈”,但在通過表演風格確立流派的初始階段,這種記錄劇目與曲譜的行為卻起了積極的推廣作用。因其可以避免傳統戲曲教習時由于不可抗拒的個人局限性造成的越傳越少,越傳越走樣的弊端。此外,有些流派創始人因自身不足在某些唱腔、身段技巧上難免會有因缺就美的無奈之舉。而如果有了白紙黑字的“宗派規范”則也可以很好的避免后人把個人缺失當作特色傳承,避免那些為求模仿逼真就得讓自己擁有某種缺陷的盲目繼承。
譚鑫培之后,雖然京劇各種流派雨后春筍般各放異彩,但卻沒再出現任何關于流派的理論著述。到了四大名旦時代,梅派、程派、荀派、尚派競相爭艷,這一時期的文人們曾前赴后繼地為演員策劃劇目、編寫劇本。輔佐梅蘭芳的齊如山可謂著作等身,也曾撰寫出《國劇身段譜》這樣極具指導性規范性綱領性的專著,但其作品中卻沒有關于梅派唱腔、身段特點的詳細文字記錄。
然而我們也不能忽視齊如山以及養育輔佐程硯秋的羅癭公等文人前輩為流派發展做出的巨大貢獻。齊如山和羅癭公分別為梅蘭芳和程硯秋編寫過劇本,是當時介入京劇的文人代表。這一時期京劇各方面漸趨成熟,文人們編寫劇本時更加注重市場需求,而非借以抒情遣懷或澆滅胸中塊壘。什么樣的戲能得觀眾青睞?表演什么能賣座?這些已成為影響文人編寫劇本的重要因素。值得注意的是,這時的文人雖關注盈利賣座等問題,卻也是真心實意地將藝人看作朋友、知己,因此并沒有出現以演員牟利的行為。再結合本文前面提到的京劇流派的特點來看,我們知道,只有切實考慮過觀賞因素,才可能贏得觀眾喜愛,喜愛的人多了才會去追捧、去學習,這也是形成流派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另外,這一時期的文人們“專事”一角兒,所以對各位藝人的個人特點十分清楚,于是創作劇本時也會考慮如何才能更多的展示藝人的技能,怎樣才能揚藝人之長并避其短處?甚至細微到擅長什么板什么調,唱詞適合什么韻轍等等。除了技術方面,文人們在創作時還兼顧演員的性格為人、身材扮相等因素。齊如山為梅蘭芳在編戲時就有意展示其雍容華貴、端莊典雅的一面。又考慮到比起表情神態,梅蘭芳更擅長歌舞,故在寫戲時會考慮怎樣最大程度發揮其歌舞技能。因此齊如山把古代的各種舞,如羽舞、拂舞、垂手舞、杯盤舞、綬舞等想方設法地安插在不同戲中。這無疑對梅蘭芳個人風格形成流派起到強有力的推動作用。
結合藝人聲腔特點編寫獨具其藝術風格的劇目也是這一階段文人致力追求的。羅癭公在為程硯秋組班時曾說過“要自立門戶,就要有自己獨創的戲。”[2]遵照這點,羅癭公為程硯秋量身打造了一系列劇目,如《青霜劍》、《金鎖記》等。同樣,輔佐其他三大名旦的文人也為角兒們策劃編寫了個人風格明顯的代表劇目。“代表劇目”的出現使得各流派傳承進一步具體化,從學某個人具體到學他的某出戲,這不失為一條便捷的傳承之道。
除此之外,這一時期的文人們參與京劇創作等種種行為,也讓我們看到京劇流派雖是個人風格的擴散,但卻不意味著只靠一個人就可以完成從流派的產生到發展傳承的全部環節。只有各方人才通力協作相互作用,才能刺激產生優秀的作品,才能促使流派孕育而生,繼而傳承發展。在這個過程中,文人集團的參與絕對是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他們輔佐名角大家尋找并最終確立其獨有風格,編寫具有專業指導性的權威典籍,為流派做闡釋,比較研究區別各流派的異同,分析流派的各自特點等等。當然我們也知道,盡管文人集團對流派傳承的影響至關重要,但不等于說文人在流派傳承過程中起決定作用,更不意味著文人是流派傳承的主角。
分析清末民初文人集團的參與對京劇流派傳承的影響,其更為深遠的意義在于引起我們當下文人、研究者的思考。在今天,京劇流派傳承基本處于停滯或者是盲目摹學的狀態,對此,我們這些文人又能做些什么?這是值得我們長期關注和認真思考的。
【參考文獻】
[1]陳培仲,史論京劇流派的含義、形成和發展[J],戲劇藝術,1983(03):87
[2]程永江編.程硯秋史事長編·上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12):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