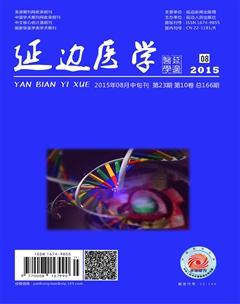從不同教材人參功效差異探討中藥功效認定
潘宇政 朱翠香
摘要:通過比較不同版本的中醫藥教材和書籍,發現高鵬翔主編的第八版《中醫學》對中藥人參功效的描述和功效認定存在較大差異。根據中藥功效的認定與論述所應遵循原則,我們提出教材對中藥的功效認定應該符合全面、系統、準確和表述規范化的特征。
關鍵詞:教材;人參;中藥;功效
由于教學上的需要,最近我們閱讀了高鵬翔主編的全國高等醫藥院校的教材《中醫學》(人民衛生出版社.第八版.),并參閱了一些相關的中醫藥教材和書籍,發現這本教材關于人參功效的表述與傳統公認的功效存在明顯差異,甚至還增加了一些新的功效。在此,我們特提出來供大家一起討論,并探討中藥功效認定的一些原則。
關于人參的功效,不同版本的中醫藥教材和書籍表述如下:
高鵬翔主編的第八版全國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中醫學》(供基礎、臨床、預防、口腔醫學類專業用.人民衛生出版社):“益氣固脫、大補元氣、益氣活血、益氣攝血、益氣促脾、益氣補肺、益氣生津、益氣安神” [1]。
鄭守曾主編的第五版全國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中醫學》(供基礎、臨床、預防、口腔醫學類專業用.人民衛生出版社):“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增智。”[2]
凌一揆主編的第一版全國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中藥學》(供中醫.中藥.針灸醫學類專業用.上海科技出版社):“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止渴、安神增智。”[3]
高學敏主編的第二版全國高等中醫藥院校規范化教材《中藥學》(供中醫藥類專業用.中國中醫藥出版社):“大補元氣、補脾益肺、生津、安神增智” [4]。
江蘇新醫學院主編的《中藥大辭典》(上海科技出版版):“大補元氣、固脫生津、安神.”[5]
2010年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大補元氣、復脈固脫、補脾益肺、生津養血、安神增智” [6]。
縱觀以上不同版本的中醫藥學教材、詞典及藥典中對人參功效的描述,我們發現高鵬翔主編的《中醫學》對人參功效的描述有兩個比較明顯的差異:一是認同人參具有“大補元氣、固脫、補脾肺、生津養血、安神增智”等功效,但語言表述明顯不同;二是新增加了“益氣活血、益氣攝血”兩個功能。
對于高鵬翔主編的《中醫學》中所出現的這些差異,我們查閱了歷代的有關文獻和當代著名的中藥典籍,并參考中藥功效認定所應該遵循的普遍原則,我們認為是不妥當的,非常值得商討。
首先,新增加的“益氣活血、益氣攝血”兩個功能,缺乏歷代文獻、臨床療效以及現代藥理研究成果的支持。把間接功效當作直接功效,違背了人參功效認定業界所達成的普遍共識。
《神農本草經》是公認的最早的本草學專著,成書于漢代,至今已兩千年左右。它反映了秦漢時期最高的藥學成就。秦漢時期可以說是中醫藥理論體系發展的一個巔峰時期,奠定中醫藥理論體系基礎的兩部巨作《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即成書于此時期。《神農本草經》里人參功效的記載為:“主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其對人參功效的敘述沒有“益氣活血、益氣攝血”這一類提法或相關內容。一千多年后的明代,李時珍編寫的《本草綱目》,是舉世公認的又一部本草學巔峰之作,被譽為中國16世紀的百科全書。關于人參的功效,它沒有專門的論述,但在“主治”一欄中寫到:“補五臟、安精神、定魂魄、止驚悸、除邪氣、明目開心、益智……治療女子一切虛證,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反胃吐食,瘧,滑瀉久痢、小便頻數淋瀝,勞倦內傷,中風中暑,痿痹,吐血、嗽血、下血、血淋、血崩,產后諸癥”。在此,李時珍認同了《神農本草經》上關于人參功效的描述,并沒有提出新的功效,僅僅在人參的主治范圍上作了進一步界定與拓展。
在當代,《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中藥大辭典》、《全國中草藥匯編》,是現代中藥研究的經典之作,它們匯總了前人及當代中藥研究的成果。關于人參的功效,最新版本的《藥典》(2010版)以及《中藥大辭典》的記載已如前所述。《全國中草藥匯編》的記載為“補氣、固脫、生津、安神、增智。”[7]這些記載與《藥典》和《中藥大辭典》基本一致。亦沒有提及“活血攝血”等功效。
高鵬翔主編的《中醫學》給人參增加的“益氣活血、益氣攝血”這兩個功效,我們考慮其可能是出于以下兩個原因:一個是編寫者個人的用藥經驗及體會;另一個是把人參的間接作用(或間接功效)當作了人參的功效。中醫認為,氣具有“推動、固攝”等作用。在氣與血的關系上,氣可以推動血的運行,并統攝血于脈中而不溢出于脈外。氣虛時,即可能出現瘀血、出血等情況。此時,用人參補氣,便可以起到推動血液運行和固攝血液不外溢的間接作用。這里人參的“活血、攝血”作用,只是補氣的間接效果,而非其直接作用。根據雷載權、張廷模主編的《中華臨床中藥學》關于中藥功效認定與論述的原則:間接功效一般不列入“功效”項內[8]。所以,根據功效認定業界所達成的共識,“益氣活血、益氣攝血”這項功能不應列入人參功效一欄里面。
其次,人參功效的表述上違背了中藥功效認定和表述所應該遵循的“用語力求規范,直接功效和間接功效涇渭分明”等原則。
高鵬翔主編的《中醫學》在人參功效的認定和論述上,除了“大補元氣”之外,還在其它功效之前加上“益氣”二字,把人參功效描述為“益氣固脫、大補元氣、益氣活血、益氣攝血、益氣促脾、益氣補肺、益氣生津、益氣安神”。“益氣”本就是人參功效之一,即大補元氣。從文字上分析,連續在多個功效前綴加“益氣”二字,是指這些功能與“益氣”功能分不開,兩者有因果關系;這樣的“因果關系”會使人誤認為“健脾、補肺、安神、生津”這些功效是“益氣”的結果,是人參的間接功效,并不是人參的直接功效。
雷載權、張廷模主編的《中華臨床中藥學》認為中藥功效的認定與論述應遵循以下幾個原則:一是功效認定應藥物的臨床療效為基礎;二是功效認定時應充分考慮到方藥配伍的情況;三是功效不宜與應用相混淆;四是功效表述上應力求直接功效與間接功效涇渭分明,間接功效盡可能不列入“功效”項目之內;同時表述語言應力求規范[8]。根據以上原則,我們認為高鵬翔主編的《中醫學》將人參功效描述為 “益氣固脫、大補元氣、益氣活血、益氣攝血、益氣健脾、益氣補肺、益氣生津、益氣安神”的表述是不妥當的。
教材,亦即教科書,是供教學用的核心教學材料。這些教學材料一般不是原始研究成果,而是對某學科現有的知識、成果進行綜合歸納和系統闡述,較少作出新的探索或提出一家之言。教科書在材料的篩選、概念的解釋、不同觀點或學派的介紹以及學科知識的綜合歸納、分析論證和結論等方面,都應該具有全面、系統、準確的特征。一些有爭議的或者純屬一家之言的見解、意見,不應該列入教材的內容。作為高等醫藥院校教材的《中醫學》,我們建議人參的功效應該參照《藥典》等當代中藥的經典著作,表述為“大補元氣、復脈固脫、補脾益肺、生津養血、安神增智。”
參考文獻:
[1] 高鵬翔主編.全國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中醫學[M].第八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3:182~183.
[2] 鄭守曾主編.全國高等醫藥院校的教材中醫學[M].第五版. 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01:207~208.
[3] 凌一揆主編,顏正華副主編.全國高等醫藥院校教材中藥學[M].第一版. 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4:209~210.
[4] 高學敏主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國家級規劃教材中藥學[M].第二版. 北京:中國中醫藥出版社,2007:424~425.
[5] 江蘇新醫學院編.中藥大辭典[M].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79:32~33.
[6] 藥典編委會.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M]. (第一部).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2010:8.
[7] 全國中草藥編編寫組.全國中草藥匯編 [[M]. (卷一).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75:8~13
[8] 雷載權,張廷模主編.中華臨床中藥學[M].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98:6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