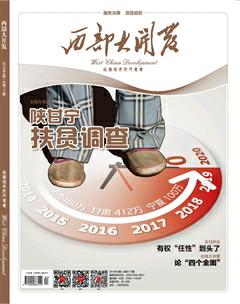土地利用與“多規合一”
王偉軍
“兩規”的實施認識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施蒂格利茨曾說過“21世紀影響全球發展的兩件大事,一件是美國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另一件就是中國城鎮化的進程。”在中國整體的快速城市化和單個城市的迅猛發展歷程中,城市規劃學科指導與規劃行政管理起到了重要作用,作出了無可否認的貢獻。但過度快速的城市化,使得城市生態、環境、資源、產業、人口、就業、交通、居住、休憩、社會貧富差距等一系列矛盾層出不窮,城市規劃正承受著超越自身學科能力和公共管理職能的巨大壓力。
1980年代中后期開始,以保護耕地資源為出發點,全國第一輪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工作異軍突起,并借助陸續建立的層層分解、環環相扣的土地規劃一計劃一供應一監督一執法等體系,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剛性較為突出的土地行政管理體系,給以地方政府主導的、比較注重城市化空間拓展而失控于城市用地規模的傳統城市規劃管理體系以較大壓力。
由于兩大規劃的編制管理分置于不同部門,導致對一座城市而言,土地利用總體規劃與城市總體規劃“兩張皮”的現象普遍存在。兩規在城鄉土地利用上的諸多矛盾,給城市發展戰略的落實和日常建設項目審批管理均帶來了極大困難。兩規的“分立”,甚至“沖突”,還削弱了各自的嚴肅性和權威性,“有空可鉆”現象比比皆是,往往成為沖擊、破壞城市整體形態和空間結構的突出因素。
現行空間規劃主要問題
傳統以土地資源為支撐的城鎮發展模式在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下,日漸顯現出資源高速耗散、城市空間無序蔓延、空間利用低效等問題。
由于城鄉發展的空間載體具有唯一性,對于同一個空間主體而言,各級政府和各部門需要在統一的平臺上表達不同的發展訴求、實現空間的統一規劃與管理。而現行的三類主要空間規劃之間,在規劃內容、規劃標準和協調機制方面存在的問題導致了各規劃結果之間的矛盾和沖突。
一是規劃內容交叉,規劃結果矛盾
人口規模預測方面。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從經濟發展與人口規模的關系人手,城鄉規劃基于人地掛鉤的考慮,土地利用規劃出于節約和集約用地要求,都會進行符合自身要求的人口規模預測。但由于規劃目的和統計口徑方面存在的差異,往往致使各規劃的人口規模預測結果相距甚遠。
土地利用空間布局方面。建設用地、農用地的發展方向、空間布局是城鄉規劃與土地利用規劃存在矛盾的地方。城鄉規劃從發展的角度,確定建設用地的空間結構,布局建設用地;土地利用規劃從農用地保護的角度,立足土地資源的現狀特征進行土地利用空間布局,兩者進行土地利用空間布局的出發點不同,常出現矛盾。
管制分區界定方面。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要求劃定重點開發區、優化開發區、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等四個主體功能區,城鄉規劃要求劃定禁建區、限建區和適建區三個管制區,而土地利用規劃則要求劃定允許建設區、有條件建設區、限制建設區和禁止建設區四個管制區,三規在區域劃定依據和劃定范圍存在不同的規定,因此也造成同一空間上區域劃分混亂的局面。
二是規劃標準存在矛盾
規劃標準的不同主要反映在各主管部門的土地分類標準上。在城鄉規劃中,按照《城市用地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中的10大類、46中類、73小類進行劃分的,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編制,是按照《全國土地分類》(過渡期間適用)中的3大類、10中類、52小類進行劃分的。兩者用地分類差別較大,用地類型同名稱不同內涵、同一類用地分類方法不一致、用地分類彼此交叉或包含,最終造成用地基礎數據和規劃目標的不一致。
三是規劃協調機制未完全建立
各類規劃組織編制雖然都統一于各級人民政府,但具體的執行部門為政府各職能部門。在下級政府對上級政府負責的職能設定與履行過程中,橫向的部門規劃存在“越位”、“錯位”現象,部門規劃協調存在“缺位”現象。雖然《土地管理法》、《城鄉規劃法》等相關法律文件要求相關規劃進行協調銜接,但缺乏較為具體的措施,協調銜接的內容也有待討論。
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編制存在的問題
一是土地利用發展戰略等研究薄弱,影響規劃合理性
土地規劃對于土地利用現狀和規劃關注的重點往往落在農用地、建設用地與其他土地之間的結構關系、耕地和基本農田保護等方面。對土地利用與城鎮化的發展戰略關系研究較為薄弱,導致耕地與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布局與城鎮空間布局缺乏有機聯系,規劃建設用地無法集中布置,只能穿插于耕地和基本農田中,導致規劃圖件上出現“羊拉屎”現象;同時,對地方實際發展戰略把握不準導致新增建設不可避免地需要占用耕地或者基本農田,規劃提出的目標往往難以實現。對規劃方案制定的合理性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
二是重點項目難以確定,影響規劃的實施性
規劃重點項目由于選址、規模變化等系列不確定因素影響,在項目可研和施工階段均需要不斷進行修改,按照土地規劃嚴格項目落界的要求,規劃方案確定前必須進行數次調整和修改,部分地區規劃通過審批后地方還不斷提出項目修改需求,嚴重影響了規劃的實施性。
三是指標設定缺乏有效支撐,影響規劃的科學性
主要調控指標的分解是土地規劃中一項重要內容,通過自上而下的編制方法,將規劃指標逐級向下分解。雖然在指標預測中會使用部分定量分析方法,但總體上缺乏其它研究依據的有力支撐,尤其在縣區和鄉鎮層面指標分解中大多以長官意志為轉移,規劃實施中實際的用地需求和用地供給往往產生較大矛盾,降低規劃的科學性。
從規劃內容互補角度來看,土地規劃中的發展戰略研究不足和重點項目難落實的問題可以通過城鄉總體規劃和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規劃中各自的規劃內容補充來解決,同時多個規劃融合所開展的系統研究可以為土地規劃指標的分解提供強有力的依據,也有利于分散長官意志對指標分解的主觀影響。因此,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編制可以嘗試采用“多規合一”的工作開展思路,在克服土地規劃自身缺陷的同時,減少各規劃之間的矛盾,加強彼此間的協調銜接,使得空間規劃尤其是土地規劃真正成為城市建設和管理的依據,城市經營的重要手段。
“多規合一”下的土地利用規劃的內容
在“多規合一”中,土地規劃要結合城市規劃的宏觀發展預測和戰略分析、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目標和重點建設的項目,側重對土地利用現狀、經濟社會發展對土地的需求等進行分析,開展土地利用潛力調查與評價。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土地資源供給目標,在兼顧耕地保護、生態保護和城鄉建設等問題的基礎上開展行政轄區內的用地平衡,分解下達各項土地利用調控指標。總體要按照“統一口徑、總量控制、城鄉統籌、布局一致”原則協調用地布局。
一是按照“統一口徑”的原則統一技術標準
統一規劃期限。《城鄉規劃法》規定城市總體規劃的期限一般為20年,《土地管理法》規定土地利用規劃的期限由國務院規定,本輪到2020年,因此“多規合一”城鄉總體規劃的期限應到2020年,既要與土地利用規劃的規劃期限一致,又在城市總體規劃的期限范圍內。
統一規劃范圍。雖然《城鄉規劃法》確立了“城鄉統籌”的基本原則,但城市總體規劃的規劃區往往還是中心城區,土地利用規劃則以市域全部土地為規劃對象,要實現“多規”的空間協調,首先要構建統一的空間平臺,以全市行政區域作為規劃范圍,對各類用地進行統一核算。
統一用地分類。城鄉建設用地以城鄉規劃部門的用地分類標準為主,非建設用地以國土資源部門的分類標準為主,因此,必須整合形成城鄉統一的用地分類。
二是按照“總量控制”的原則銜接用地規模
城鄉總體規劃中建設用地規模、范圍應當與上層次城鎮體系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規模、范圍相一致,并結合城鎮和村莊的發展需要確定建設用地、農用地等分區,落實基本農田保護和撤并后村莊的土地整理,在保證耕地不減少的情況下,摸索小田變大田的農業規模經營,以及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與農村建設用地減少相掛鉤的土地流轉模式。
三是按照“城鄉統籌,布局一致”的原則協調用地規劃布局
城鄉總體規劃應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用地指標,土地利用結構、基本農田保護、耕地總量平衡等內容在符合城鄉發展要求的前提下,在空間布局上予以落實,從而有效緩解城鄉發展與耕地保護的矛盾,協調城鎮建設,土地供應、土地開發三者的關系。
在規劃編制中應以空間資源的優化配置為主線,根據產業布局、生態環境保護、基本農田保護等要求,協調城鄉發展功能分區,科學進行各類土地用途(包括建設用地和非建設用地)的總體布局,統籌確定“四區四線”空間管制區域和管制要求,并指導和約束空間發展的時序性和方向性。
其一,結合城鄉建設用地擴展邊界設定建設用地“彈性圈”。采取建設用地總量指標依據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具體布局按照“剛性框架、彈性利用”的理念,在土地利用規劃確定的城鄉建設用地擴展邊界外,按一定比例(如15%)設定建設用地“彈性圈”,圈內不布局基本農田,盡量少布局耕地,確保在建設用地總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城鎮可根據市場需要在圈內彈性規劃用地布局。
其二,通過前置性用地評價確保基本農田保護區不被侵占。規劃編制中可在用地評價和規劃方案中增加現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用地性質、規模等內容,并在用地評價圖、現狀圖和規劃總圖中,標示基本農田保護區的范圍界限,確保基本農田不被侵占。
(作者系中研智業集團規劃院規劃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