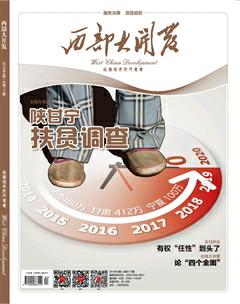基于“三層四線”的“多規合一”管理平臺建設
羅以燦
目前我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等規劃的編制與管理由不同職能部門主導,彼此間存在空間范疇、規劃目標及技術標準等方面的差異,甚至存在矛盾之處,給具體的城市規劃實施造成了困難。分析這些差異和矛盾,并協調各類規劃的統一標準體系勢在必行。
主要差異分析
一是基礎數據的差異
由于各職能部門編制規劃時主要采用本部門或本系統的各類基礎數據采集所采用的空間坐標系、數據格式及數據統計口徑等存在較大的差異。例如,所采用的空間坐標系有國家西安80坐標系、北京54坐標系,還有地方坐標系;而所采用的數據格式有支持Arcgis平臺、Mapgis平臺以及CAD平臺等;上述的差異導致了基礎數據無法在統一的平臺下共享交互。
在基礎數據的統計方面,特別是人口數據、現狀建設用地數據,由于所采用的統計口徑、統計方法、對建設用地內涵的不同界定。導致基礎數據不具備可比性。
二是規劃目標的差異
當前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在行政上分屬不同的職能部門,各部門在行政職責、關注重點的差異,導致各規劃在規劃目標上各不相同。
(1)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戰略性、綱領性、綜合性規劃”,也是“政府履行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責的重要依據”,其關注的重點是目標與政策,但由于與空間不對接,容易導致項目無法落地,如某區“十二五”規劃中安排了重點項目多達100余項,其中已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進行建設用地安排的僅60項。此外,兩個規劃中存在同一項目卻使用不同名稱的情況。
(2)城市總體規劃的目標是“協調城鄉空間布局,改善人居環境,促進城鄉經濟社會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但常因追求“空間布局”的協調或過多考慮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導致其劃定的建設用地布局與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布局不銜接,建設用地規模遠遠超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建設用地規模控制指標,如某區城鄉規劃截至2020年,規劃期末的建設用地總規模為169.42km2,而同期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建設用地總量控制指標僅為144.81km2,缺口近25 km2。
(3)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目標是“實行土地用途管制,將土地分為農用地、建設用地和未利用地。嚴格限制農用地轉為建設用地,控制建設用地總量,對耕地特別是基本農田實行特殊保護”,然而由于對土地的自然界線過多考慮,對土地與城市發展的關系考慮不足,一些地方基本農田保護區的劃定犬牙交錯,導致城鎮布局結構不完整,基礎設施難以實施。
三是規劃期限的差異
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的規劃期限通常為5年,與地方城市政府執政一屆相對應的5年有比較完整意義的對應關系。城市總體規劃的規劃期限一般為20年,同時還會對城市更長遠的發展作出預測性安排。土地利用規劃的規劃期限由國務院規定,一般為10-15年。
目前,很多城市“三規”并非同時展開,“三規”的基期年、目標年和規劃期限不一致,導致各規劃之間難以銜接。
四是用地分類標準的差異
用地分類標準的差異,主要涉及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目前,土地利用總體規劃采用的規劃用地分類標準是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數據庫標準中的土地規劃分類體系,而城市總體規劃采用的則是《城市用地分類與規劃建設用地標準》(GB50137-2011),兩者對規劃用地的分類標準、內涵存在較大的差異,且無法直接對應。例如,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中水利水工建筑屬于建設用地,但城市總體規劃中沒有對應的分類,在城市總體規劃圖中此類用地一般根據用地性質部分表達為市政公用設施用地,部分表達為水域或其他非建設用地。這也是導致“兩規”建設用地總規模不一致的原因之一。
建立統一的標準體系
由于“多規”之間存在的上述差異,因此,“多規合一”及其管理平臺建設的基礎就是要制定協調各類規劃的統一標準體系,具體如下:
一是統一坐標系統
坐標系統主要包含國家坐標系統和地方坐標系統兩大類,分別為北京54坐標、西安80坐標和地方坐標共3種。“多規合一”工作須建立統一空間坐標系統,實現一圖雙坐標(西安80坐標系、廣州坐標系)的對應轉換。
二是統一規劃目標
雖然,一個地方的多個規劃在規劃目標上存在差異,但是地方城市政府的發展思路是唯一的,指導各個規劃的內容也只有一個,就是城市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多規合一”的城市發展目標與戰略層面應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為指導,結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生態環境保護規劃等,使其發展思路和規劃目標一致,實現目標(發展方向與重點項目)、指標(用地指標)和坐標(空間布局)協調統一。
三是統一規劃期限
綜合考慮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總體規劃等規劃期限長短的利弊,強化規劃實施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兼顧政策措施調整的靈活性,將“多規合一”的規劃期限明確為10-15年,每5年評估修訂一次,以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空間環境變化,增強規劃的宏觀調控功能。
四是統一用地分類標準
建立涵蓋國土城鄉、內涵統一的規劃用地分類標準,明晰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中建設用地、城鄉建設用地、建制鎮用地、農村居民點用地等內涵定義,建立協調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用地與城市總體規劃用地對接轉換的關系。
總體框架設計
基于“三層四線”的“多規合一”管理平臺總體框架包括三層一庫,即基礎層、核心層、管理層和現有規劃成果庫,“四線”是指基本農田控制線、生態保護控制線、建設用地規模控制線和建設用地擴展邊界控制線。
一是基礎層
基礎層:包括地籍圖、土地利用現狀圖、行政區劃圖、道路中心線、地下管網、地形圖、影像圖、各類經濟人口統計數據等。所有基礎層數據應在統一坐標系統、統一數據格式、統一分類標準和統一存儲平臺的原則下,建立“多規合一”基礎地理信息層(數據庫),實現基礎地理數據的共享。各類規劃編制,須以管理平臺中的基礎地理信息層(數據庫)作為其規劃基礎數據。
二是核心層
核心層:為各類規劃整合、編制和調整的參考基準,包括空間管控“四線”、法定圖則和重點項目。空間管控“四線”包括基本農田控制線、生態保護控制線、建設用地規模控制線和建設用地擴展邊界控制線。法定圖則主要包括法定文件、土地開發強度和其他控制要求。重點項目是經整理、甄別、排序,按照項目立項和資金情況、成熟程度、開發需求和開發規律進行了分期,并作為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總體規劃重點落實安排建設用地規模的對象。
(1)基本農田控制線
即基本農田保護區邊界線,是為對基本農田進行特殊保護和管理劃定的區域。按照《基本農田保護條例》進行管控,線內禁止進行破壞基本農田的活動,不得擅自改變基本農田用途或者占用基本農田進行非農建設。
(2)生態保護控制線
根據有關法律、法規,綜合分析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城市總體規劃、林業發展規劃、環境與生態保護規劃等相關規劃對生態環境保護的要求,結合城市的實際情況,將自然保護區(核心區)、一級水源保護區、森林公園、坡度大于25°的山林地、主干河流(水利藍線)、水庫、濕地及具有生態保護價值的濱海陸域、維護生態系統完整性的生態廊道和隔離綠地等區域劃定為生態保護控制線,保障城市基本生態安全。
生態保護控制線范圍內,除國家、省市重點交通項目、市政公用、科研和旅游設施及軍事項目,其他情形項目一律禁止建設。線內已建合法建筑物、構筑物,不得擅自改建和擴建,范圍內的原有農村居民點可保留或逐步實施搬遷。
(3)建設用地規模控制線
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建設用地總規模,在落實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確定的重點發展區域和重點建設項目的基礎上,協調城市總體規劃和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建設用地布局,劃定統一的建設用地規模控制線,作為城市的允許建設區域,但必須嚴格區分城鄉建設用地控制線和非城鄉建設用地控制線。
建設用地規模控制線范圍內允許建設,建設內容必須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控制性詳細規劃(法定圖則)控制要求,且非城鄉建設用地控制線范圍內不得安排城鄉建設項目。
(4)建設用地擴展邊界控制線
綜合分析城市拓展方向,避開基本農田控制線和生態保護控制線,在建設用地規模控制線外,總量控制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確定的城鄉建設用地規模的20%范圍內,劃定建設用地擴展邊界控制線(有條件建設區),作為滿足特定條件后可以開展城鄉建設的空間區域。其中,將連片的城鎮集中建設控制區劃為城市增長邊界。
建設項目選址位于建設用地擴展邊界控制線內的,須按照土地利用總體規劃有條件建設區使用辦法,編制有條件建設區使用方案,報有審批權限的管理部門批準后,方可使用。
三是管理層
管理層:包括規劃整合、規劃調整、規劃審批等管理信息。其中,規劃整合是管理平臺中的重點內容。它通過管理平臺核心層“四線”管控、法定圖則和重點項目的整合判讀機制,梳理各層次不同規劃成果,分析其與核心層的沖突和矛盾,按照規劃整合原則和程序,協調解決矛盾,使各個規劃協調統一,實現“多規合一”。
系統實現
根據管理平臺公用性和基礎性的特點,系統架構將盡可能采用面向服務的軟件架構(service-orientedarchitecture,SOA)。SOA是一種組件模型,它通過應用程序功能單元(稱為服務)之間定義完善的接口和契約,來聯系應用程序中的不同服務。
管理平臺開發過程中盡可能將系統提供對外服務的應用程序功能封裝和發布為Web服務,通過服務注冊和服務目錄,向各部門的應用終端提供Web服務,使系統的功能可以采用松耦合的方式實現集成,并使管理平臺提供的功能服務具有可擴展性。
管理平臺海量異構數據的整合工作,是“多規合一”的基礎條件。管理平臺空間數據應按照“數據庫-子庫-專題(分類)-層-要素及屬性”的層次框架建立數據庫,按分類分層原則組織數據。
管理平臺將擁有多種信息表現平臺,包括GIS系統、CAD系統、Web頁面,可實現信息檢索查詢、業務審批、數據更新編輯、信息發布、制圖輸出等功能;針對不同應用權限,定制相應的基本信息配置。
基于“三層四線”管理平臺的構建,分析了各類規劃存在的主要差異,并制定了協調各類規劃的統一標準體系,為建設“多規合一”管理平臺提供了一些思路和方法,但還需要在實踐中不斷修正、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