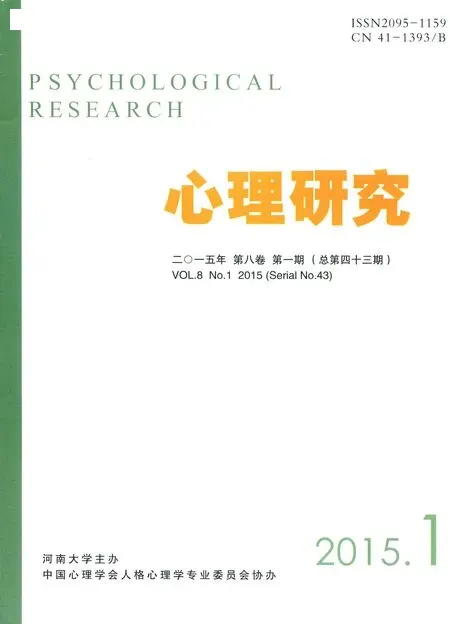微博時代:參與集體行動對群體情緒和行動意愿的影響
馮寧寧 杭婧婧 崔麗娟
(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上海 200062)
微博時代:參與集體行動對群體情緒和行動意愿的影響
馮寧寧杭婧婧崔麗娟
(華東師范大學心理與認知科學學院,上海 200062)
實驗研究,考察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實際行動/閱讀/控制)對集體行動社會心理變量(群體情緒、效能、社會認同、參與意愿等)的影響。將92名大學生被試隨機分成三組,實際行動組被試會參與關于“網絡謠言整治”的集體行動,而閱讀組則是閱讀描述該集體行動的文本,之后兩組被試連同控制組完成相關社會心理變量的測量問卷。結果發現,實際行動組個體會比閱讀組和控制組體驗到更多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在未來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更高,而且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可以中介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與集體行動意愿之間的關系。社會認同和效能類變量不受集體行動實際參與的影響。
集體行動的實際參與;指向外群體的情緒;網絡集體行動
1 引言
集體行動是“群體成員代表群體為改善群體生存環境而做出的行動”[1]。研究者們對集體行動的驅動因素[2]進行了大量的探索,而涉及群體情緒、群體效能感、社會認同等集體行動預測因子的“集體行動的社會認同模型”(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SIMCA)[3]則較好地整合了此前的研究成果。然而,探究參與集體行動對群體成員的心理變量帶來何種影響并最終促成社會變革[4]的工作近來才剛剛展開,如采用實驗法考察參與集體行動后的情緒后果[5],或通過縱向研究分析集體行動成功或失敗結果的影響[6]以及關注網絡對集體行動的調節效應[7]等。
Becker等人將被試分為實驗組和控制組兩組(研究一),實驗組被試參與集體行動,具體做法是使其朗讀一段文字:“我作為瑪堡(Marburg)大學的學生,強烈譴責黑森州(Hessen)政府再次征收學費,并堅決反對政府,我抗議收學費,因為……”此后被試會列舉反對理由,并被告知這些理由將會被呈送至政府[5]。研究發現,參與集體行動會體驗到更多的指向自我的積極情緒(self-directed emotion)和指向外群體的憤怒情緒(outgroup-directed anger)并增加未來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而且參與集體行動會通過產生憤怒情緒而增加未來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
Becker等人的研究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也引發了更多思考。第一,除了Becker等人在研究二中加入的指向外群體的輕蔑情緒之外,其他種類的群體情緒,如擔憂(害怕、焦慮)[8]等,也有可能受集體行動實際參與的影響(假設1)。第二,Becker等人將群體效能信念視為控制變量并未加以重點分析,那么集體行動的實際參與對群體效能信念、參與者效能信念(participative efficacy beliefs)和個體效能信念作用如何呢?參與者效能信念是指“個體可以對旨在取得群體目標的集體努力中做出貢獻”的信念,個體效能信念是指個體對通過自己個人的努力達成群體目標的信念,這兩者與群體效能信念有顯著相關,同時又會在預測不同類型的集體行動上存在差別[9],那么集體行動的實際參與可能會對參與者效能信念或個體效能信念造成不同于群體效能信念的影響(假設2)。第三,Becker等人并未關注參與集體行動對社會認同的影響,而關于網絡集體行動的問卷研究發現,在線政治討論在社會認同對集體行動傾向之間起調節作用,具體表現為參與在線討論的頻率高時,社會認同對集體行動傾向的預測作用才會成立[7]。那么,參與集體行動,特別是網絡集體行動,可能也會影響參與者的社會認同(假設3)。
網絡普及對集體行動的影響隨著越來越多的網絡集體行動而受到研究者的關注[7],因此,當前研究聚焦于網絡環境中集體行動的實際參與對相關心理變量(情緒類、效能類、社會認同、參與未來集體行動的意愿)的影響。研究在Becker等人的實驗范式基礎上[5],設置“整治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環境”研究情境,作為正常網絡用戶的一員,個體會通過集體行動來達到減少網絡謠言的群體目標。如果將自然環境與網絡環境進行類比,親環境行為可以根據行為的努力水平、資源消耗和行為所起的作用分成遵守型(low effort)和主動型(high effort)兩類[10-12],那么保護網絡環境的集體行動可能也可以根據努力水平、所需資源或行為成本和行動效果分為遵守型集體行動(如,在線投票、在線簽名、評論或轉發微博等)和主動型集體行動(如,聯名投訴、聯名舉報等)。事實上,以往研究者關于集體行動的分類已有不同方式,如群體層面(示威、游行、抗議等)vs.個體層面(簽名、投票、捐款等)[2],或者常規集體行動(聯名上書、投票等)vs.非常規集體行動(暴力沖突、騷亂等)[13]等等。Becker等人發現,集體行動的實際參與會增加個體未來參與集體行動(常規/非常規)的意愿,那么參與集體行動(網絡環境中),也可能對未來參與不同種類的網絡集體行動(遵守型/主動型)意愿產生作用(假設4)。
2 方法
2.1被試
被試由某高校學生組成 (N=92,18~25歲,Mage= 21.42,SD=1.31),其中行動組31人(男9人,女22人),閱讀組31人(男6人,女25人),控制組30人(男5人,女25人)。
2.2實驗設計與程序
單因素被試間設計。自變量是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共有三個水平,分別是實際參與行動(行動組)、閱讀集體行動(閱讀組)和控制組。
首先,每位被試來到實驗室后,主試向被試提供屬于其個人的被試編號。請被試閱讀文字材料A,各水平下參與者閱讀內容相同。文字材料A內容如下:
2013年,我國網絡用戶數凈增5358萬人,達6.81億人,互聯網普及率達到45.8%,比2012年提高3.7個百分點。手機網絡用戶規模達到5億人,比上年增加8009萬人,網絡用戶中使用手機上網的人群占比由上年的74.5%提升至81%。
互聯網的發展帶來了快捷和便利,同時一些虛假新聞或不實信息也通過互聯網的各種信息平臺對人們的生活造成影響。2013年8月20日,全國公安機關集中整治網絡謠言專項行動拉開序幕,對謠言制造者和傳播者的打擊立竿見影。
閱讀文字材料A后,行動組被試按照主試指定的微博用戶名及密碼登陸微博(已注冊,僅供實驗用途),在搜索框中鍵入“網絡謠言整治”并查找認證用戶,閱讀結果列表中第一頁的第一條微博并進行轉發。轉發理由框中要求被試輸入指定內容。點擊“轉發”前,主試提醒被試該條微博將出現在微博實時平臺中并被他人閱讀。參與者表示知曉并同意繼續行動時,可以點擊“轉發”。“轉發理由框”中輸入內容如下:
閱讀組被試在閱讀文字材料A后,繼續閱讀與集體行動有關的文字材料B,內容如下:
廣大網絡用戶對整治網絡謠言的專項行動也紛紛表示支持。例如,數以萬計的微博用戶對#網絡謠言整治#等話題下的新聞或辟謠信息進行轉發,并標注“打擊網絡謠言,凈化網絡環境,文明上網,人人有責”等相關口號或評論。
控制組被試在閱讀文字材料A后無其他操作。
接著,在各組完成前述步驟后(行動組完成轉發微博、閱讀組閱讀完文字材料B、控制組閱讀完文字材料A),所有被試填寫因變量問卷,所測因變量包括情緒類變量(指向外群體的憤怒、擔憂情緒)、社會認同、效能信念類變量(群體效能信念、參與者效能信念、個體效能信念)、集體行動類型類變量(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的意愿、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
最后所有參與者填寫個人信息,包括年齡、性別、專業及常用網絡社交軟件或應用等。
2.3測量工具
所有因變量測量指標均采用利克特7點計分,1=完全不同意,2=非常不同意,3=不同意,4=不確定,5=同意,6=非常同意,7=完全同意。
2.3.1指向外群體的情緒
改編自Becker等[5]和薛婷等[8]的問卷,評估被試作為網絡使用者群體成員對網絡謠言制造者的情緒體驗,共有4個項目,考察兩類情緒,一是憤怒(α=0.80),如“作為一名網絡用戶,我對網絡謠言制造者感到憤怒(反感)”;二是擔憂(α=0.79),如“對于網絡謠言制造和傳播者,我感到擔憂(不安)”。
2.3.2社會認同
評估被試作為網絡使用者群體成員的認同程度,將社會認同問卷[14,15]中的“學生”替換為“網絡用戶”,共有4個項目(α=0.79),如“網絡用戶是我的一個重要身份”。
2.3.3效能信念類變量
將van Zomeren等人研究中群體效能信念、參與者效能信念和個體效能信念問卷[9]中的“學生”替換為“網絡用戶”,將“阻止收學費”替換為“減少網絡謠言”:(1)群體效能信念:評估被試對網絡用戶群體通過集體行動達成群體目標的信念,共有4個項目(α=0.87),如“我們網絡用戶聯合起來可以減少網絡謠言”;(2)參與者效能信念:評估被試對在集體行動(旨在取得群體目標)中自身可以做出貢獻的信念,共4個項目(α=0.89),如“我個人可以在我們網絡用戶減少網絡謠言的聯合行動中做出貢獻”;(3)個體效能信念:評估被試對通過個體行動達成群體目標的信念,共有4個項目(α=0.89),如“我相信我個人就可以減少網絡謠言”。
2.3.4參與集體行動意愿
評估被試參與兩類網絡集體行動的意愿,一是遵守型集體行動,根據網絡使用實際情況對常規集體行動意愿問卷[6,13]進行改編,共有3個項目(α= 0.82),如“參與網上投票,建議加強網絡信息監管”;另一個是主動型集體行動,依照微博用戶規范進行編制,共有3個項目(α=0.84),如“當在微博中發現不實信息時,聯合其他用戶,向微博運營方舉報這條微博及該用戶”。
3 結果
3.1三種水平下各變量的初步分析
實際參與行動組、閱讀組和控制組三種水平下各因變量的平均數和標準差如表1所示。

表1 三組各變量的平均數(標準差)(N=92)
三組被試在網絡用戶社會認同上平均數都大于4,且經單因素方差分析可知,三組被試的社會認同沒有顯著差異,F(2,89)=1.69,p=0.19,2=0.04,假設3未得到驗證。而三種條件下,指向外群體的憤怒情緒和擔憂情緒都顯著正相關 (r=0.43,p=0.02;r=0.65,p<0.001;r=0.49,p=0.01)。
3.2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對情緒類變量的影響
為考察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和指向外群體情緒類型(憤怒/擔憂)在指向外群體情緒評分上的主效應和交互作用,進行兩因素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主效應顯著,F(2,89)=4.12,p=0.02,ηp2=0.04;指向外群體情緒類型的主效應也顯著,F(1,90)=6.65,p=0.01,ηp2=0.04;但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p=0.49。
進行配對樣本t檢驗發現,所有被試在憤怒情緒的評分(M=5.64,SD=0.98)上都顯著高于擔憂情緒(M=5.27,SD=1.01),t=3.77,p<0.001。以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為自變量,分別以在憤怒情緒和擔憂情緒上的評分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三組在憤怒情緒上的評分沒有顯著差異,F (2,89)=1.13,p=0.33,ηp2=0.03;但是在擔憂情緒上的評分存在顯著差異,F(2,89)=3.69,p=0.03,ηp2=0.08。經事后檢驗,采用LSD法,結果發現,行動組在擔憂情緒上的評分顯著高于閱讀組和控制組,而后兩者沒有顯著差異,假設1得到驗證。
3.3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對效能類變量的影響
以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為自變量,分別以群體效能信念、參與者效能信念和個體效能信念為因變量,進行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對這三個效能類變量的主效應均不顯著,F (2,89)=1.83,p=0.17,ηp2=0.04;F(2,89)=2.09,p= 0.13,ηp2=0.05;F(2,89)=0.75,p=0.47,ηp2=0.02。但是在事后比較(LSD法)中發現,閱讀組的參與者效能信念顯著低于行動組(t=-0.44,p=0.049),而閱讀組與控制組之間、行動組與控制組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假設2得到部分驗證。
3.4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對參與兩類集體行動意愿的影響
根據兩因素重復測量的方差分析,以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行動組/閱讀組/控制組)和集體行動類型(遵守型/主動型)為自變量,參與集體行動的意愿為因變量,結果發現,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的主效應顯著,F(2,89)=13.30,p<0.001,ηp2=0.13;集體行動類型的主效應也顯著,F(1,90)=11.13,p=0.001,ηp2= 0.06;但兩者的交互作用不顯著,p=0.43。
經配對樣本t檢驗發現,被試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的意愿(M=5.30,SD=1.06)顯著高于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 (M=4.83,SD=1.00),t=4.34,p<0.001。以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為自變量,分別以參與遵守型或主動型集體行動意愿為因變量,做單因素方差分析,結果發現,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對兩種類型的集體行動參與意愿的主效應都顯著,F(2,89)=9.01,p<0.001,ηp2=0.17;F(2,91)=4.98,p=0.01,ηp2= 0.10。采用LSD法做事后比較發現,行動組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的意愿顯著高于閱讀組和控制組(t= 1.04,p<0.001;t=0.67,p=0.01),后兩者沒有顯著差異。行動組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也顯著高于閱讀組和控制組(t=0.66,p=0.01;t=0.68,p=0.01),而后兩者也沒有顯著差異。假設4得到驗證。
3.5擔憂情緒在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和參與集體行動意愿之間的中介作用
因為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和參與遵守型/主動型集體行動意愿在三種條件下存在都顯著差異,所以接下來可以考察擔憂情緒在自變量與集體行動意愿之間的中介效應。首先設置虛擬變量,因自變量有三個水平,則需要設置2個(=3-1)虛擬變量。“參與情況_虛擬1”表示“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參與情況_虛擬2”表示“閱讀組與控制組的對比”,參照組為控制組。采用分層回歸分析的方法考察擔憂情緒的中介效應。
在控制年齡、性別和社會認同的情況下,做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意愿對兩個虛擬變量的回歸發現,“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的回歸系數顯著(B=0.72,SE=0.26,p=0.01),而“閱讀組與控制組的對比”的回歸系數不顯著(B=-0.36,SE=0.24,p=0.14)。然后進行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對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意愿的回歸,發現其回歸系數顯著 (B=0.56,SE=0.27,p= 0.04)。再做擔憂情緒對“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的回歸,發現其回歸系數顯著 (B=0.55,SE=0.23,p= 0.02)。最后,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的意愿對“行動組與控制組對比”的回歸系數會在回歸方程加入擔憂情緒后 (B=0.26,SE=0.10,p=0.01)顯著變小 (B=0.58,SE=0.26,p=0.03;ηp2=0.05,F=6.59,p=0.01),這說明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可以部分中介“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與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的意愿之間的關系。
同理,做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意愿對兩個虛擬變量的回歸發現,在控制年齡、性別和社會認同的情況下,“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可以顯著預測被試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 (B=0.54,SE=0.27,p= 0.047),而“閱讀組與控制組的對比”對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意愿的預測作用則不顯著 (B=-0.002,SE=0.24,p=0.99)。接著檢驗擔憂情緒對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意愿的回歸系數,發現其回歸系數顯著(B=0.38,SE=0.10,p<0.001)。擔憂情緒對“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的回歸系數已在前面的步驟中得到檢驗。最后,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對“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虛擬變量的回歸系數會在回歸方程中加入擔憂情緒后(B=0.35,SE=0.10,p=0.001)變得不再顯著 (B=0.34,SE=0.26,p=0.19;ηp2=0.10,F= 11.69,p=0.001),這說明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在“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和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之間有完全中介效應。采用bootstrapping法,樣本數為5000,檢驗完全中介模型“‘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意愿”的特定中介效應。結果發現,中介變量的95%置信區間為[0.15,0.54],該置信區間不包括0,所以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在“行動組與控制組的對比”和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之間所起的特定中介效應顯著。而該模型中,社會認同的95%置信區間為[-0.09,0.40],中介效應不顯著,這與Becker等人所得結果不同。
4 討論
研究通過操縱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行動組/閱讀組/控制組),發現行動組個體會比閱讀組和控制組體驗到更多的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更愿意參與未來的集體行動(遵守型/主動型),而且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可以在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與未來參與遵守型集體行動的意愿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在集體行動的參與情況與未來參與主動型集體行動的意愿之間起完全中介作用。
研究對前面所提出的問題也做出了回答:第一,盡管所有被試指向外群體的憤怒情緒評分均高于擔憂情緒,但是三組被試在憤怒情緒上沒有出現顯著差異。這也反映出在考察實際參與集體行動后產生的群體情緒并不只有群體憤怒一種,而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探究更多的個體水平的情緒在群體水平的合理性并將其納入集體行動研究框架中。第二,實際參與集體行動對效能類變量(群體效能信念、參與者效能信念、個體效能信念)都無法造成影響,不過閱讀組的參與者效能信念會顯著低于控制組,這可能是因為當閱讀組個體從文字材料中看到內群體成員已參與了集體行動而自身并未行動,從而認為在集體努力中的個人貢獻較低。那么效能類變量會在何種情況下發生改變呢?Tausch和Becker通過縱向研究發現,當集體行動取得成功的時候,群體成員會產生自豪的情緒,該情緒會通過增加群體效能感從而更愿意參與未來的行動[6]。因此,今后的研究可以通過操縱集體行動的結果(成功/失敗)考察其對效能類變量的作用。第三,盡管此次集體行動在網絡環境中開展,研究仍未驗證集體行動的實際參與可以提升群體成員的社會認同。有研究者認為參與集體行動可以使群體成員認同更加“具體”、“激進”的身份[3],所以未來的研究可以嘗試在因變量中加入更“具體”、“激進”的社會認同指標。最后,研究也發現,在保護網絡環境這一研究情境下,相比于要付出更多個人努力或成本的主動型集體行動,所有被試都更愿意參與資源消耗較低的遵守型集體行動,這與常規型/非常規型集體行動的研究結果類似[5,9,13]。但是當個體實際參與了集體行動之后,這一經歷會引發其指向外群體的擔憂情緒,從而更愿意在未來參與主動型或遵守型的集體行動。
1Wright S C,Taylor D M,Moghaddam F M.Responding to membership in a disadvantaged group:From acceptance to collective protest.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90,58:994-1003.
2van Zomeren M,Iyer A.Introduction to the Social and p sychological d ynamics of c ollective a ction.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9,65:645-660.
3van Zomeren M,Postmes T,Spears R.Toward an integrative social identity model of collective action:A quantitative research synthesis of three socio-psychologicalperspectives.PsychologicalBulletin,2008,134:504-535.
4Louis W R.Collective Action and Then What?Journal of Social Issues,2009,65:727-748.
5Becker J C,Tausch N,Wagner U.Emotional c onsequences of c ollective a ction p articipation:Differentiating s elf-d irected and o utgroup-d irected e motions.Personality and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2011,37:1587-1598.
6Tausch N,Becker J C.Emotional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of collective action as predictors of future action intentions:A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in the context of student protests in Germany.British Journa of Social Psychology,2013,52:525-542.
7Alberici A I,Milesi P.The Influence of the i nterne onthep sychosocial p redictorsof c ollectivea ction Journal of Community&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2013,23:373-388.
8薛婷,陳浩,樂國安,等.社會認同對集體行動的作用:群體情緒與效能路徑.心理學報,2013,45:899-920.
9van Zomeren M,Saguy T,Schellhaas F M H.Believ ing in“making a difference”to collective efforts:Participative efficacy beliefs as a unique predictor of collective action.Group Processes&Intergroup Relations,2013,16:618-634.
10萬基財,張捷,盧韶婧,等.九寨溝地方特質與旅游者地方依戀和環保行為傾向的關系.地理科學進展,2014,33:411-421.
11Ramkissoon H,Weiler B,Smith L D G.Place attachment and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in nationa parks:the development of a conceptual framework.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2012,20:257-276.
12Thogersen J.Acognitive dissonance interpretation o consistencies and inconsistencies in environmentally responsible behavior.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2004,24:93-103.
13Tausch N,Becker J C,Spears R C,et al.Supplemental m aterial for e xplaining r adical g roup b ehavior:Developing e motion ande fficacy r outes to n ormative and n onnormative c ollective a ction.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11,101:129-148.
14Smith E R,Seger C R,Mackie,D A.Can emotions be truly group level?evidence regarding four conceptual criteria.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93:431-446.
15van Zomeren M,Leach C W,Spears R.Does group efficacy increase group identification?Resolving their paradoxical relationship.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10,46:1055-1060.
The Influence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on 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 and Future Intentions in the Era of M icroblogging
Feng Ningning,Hang Jingjing,Cui lijuan
(School of Psych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Evidence pointed to the predictors of collective action,but the emotional and behvioral consequence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was remained relatively underresearched.The present research investigated the effects of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on outgroup-directed anger/worry,social identity,efficacy beliefs and intentions to engage in low/high effort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future.Result of an experiment(N=92)that manipulated participation in collective action showed that whereas in all conditions they felt more outgroup-directed anger than worry,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nts experienced more outgroup-directed worry(rather than anger)than read and control conditions.Additionally,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increased willingness to engage in both low and high effort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future,which were mediated by outgroup-directed worry.Nevertheless,social identity and efficacy beliefs were unaffected.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outgroup-directed emotions;online collective action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項目批準號11YJA190001
崔麗娟,教授,博士生導師。Email:ljcui@psy.ecn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