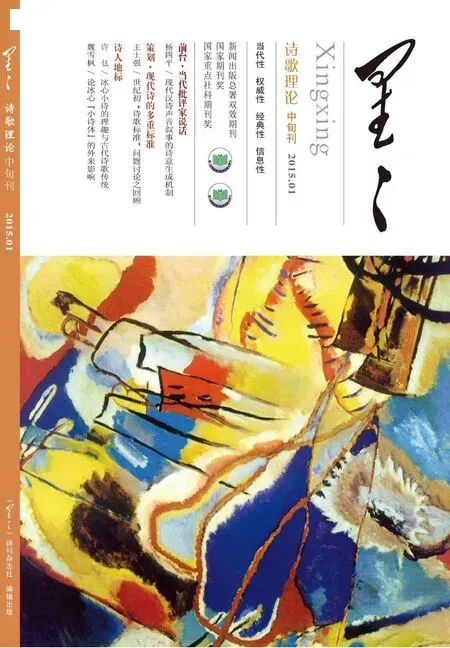后視鏡里的鄉村與詩
木 朵
后視鏡里的鄉村與詩
木 朵
當我們認為存在一種“鄉村詩”(對某一類詩的統稱)——尤其存在一種與時俱進的、更好的“鄉村詩”——時,很可能觸碰到了城鄉二元論這副顯在的衣缽:由來已久的觀念骨骼、思維定勢的殘骸。仿佛我們在談論這個詞時,手心里還攥著另一個詞:城市詩。
在現在——我們中有人說、有人看、有人聽的這一刻——并沒有“鄉村詩”這個類型、概念以及與之相關的成為問題的現實情況。有的只是我們自以為有的、心目中的“鄉村詩”:一種修辭措施、眾人之間的假象與分歧。經驗積累到了一個必須說出它——累累碩果(它們、復數)歸于一個它(單數)——的契機,但說出來,又因訴說的途徑、氛圍、節奏有別,會像是一次個別人的頓悟,此時此刻,訴說者是明白他打算說出來的對象,他瀕臨雄辯的關卡,又逡巡自我反省的邊疆。有一個時刻,“鄉村詩”會被表述得最充分,但這個時刻不一定正是“現在”。我們現在聚在一起探討的、說與聽相結合的事宜,都是對那個最充分表達的時機的模仿。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個談論“鄉村詩”的權益,因“現在”(“現在”是“過去”不完美的投射、闡釋)的殘缺、不充分而成為一個我們捉不到的自己的身后長影。
這有點玄乎。也很懸。我們如果意識到現在不應再寫某種樣式的“鄉村詩”,要有一種嶄新的思路,那么,這個被認為成問題的“鄉村詩”現象就真的擺在我們面前了。我們無法返鄉,返回一個更早的鄉村背景中,一個對鄉村景觀有情有義的心靈圖景之中,我們陷在此地、“現在感”中,無法做記憶中的那個鄉村詩人。鄉村的敗落已成定論似的,我們就像是見證人,承受著壓力,一方面要用并不敗落的語言來勾勒現況的不如意,另一方面又要為這種鄉村景象塑造出、喝令出一種更為進化的語言模式。而比較真實的一個境況在于,面臨敗落的、日益被污染的鄉村現實,關于鄉村的詩也處于一種退步狀態之中,也沒看頭,老舊,停滯不前,缺乏新意,不可戰勝來自城區的五彩斑斕的現實以及與之相關的詩。不妨說,鄉村詩的窘境正是合乎鄉村當前的落后和落落寡歡。
而我們中的一股正義的聲音是,詩人必須用如椽大筆去直指鄉村的“惡之花”。去掉以往鄉村詩中的明月、外婆家的瓦屋、貓叫、霜、荷塘,直面鄉村中的垃圾場、人際關系的退化、留守兒童的慘況、老人村的悲鳴、拆遷戶的無根意識等等,要求新的“鄉村詩”(“后鄉村詩”)務必裝入新情況、新元素,并且希望詩人們聚集在一起研討出一個得體的協作(寫作)方案來。一個個從鄉村走出來的詩人力圖重返鄉村采風,以發現更多不被寫過的素材和主題,但往往回城最大的感喟在于他們認為無法回到心目中的既定鄉村,描寫的側重點變成了一股油然而生的鄉愁,而不去觸及剛剛看到的一幕幕活生生的現實;這些現實太近,或者早已被圖片新聞搶先報道、塑形,他們還不便賦予這些現實一種足以融入詩句中的情感。寧肯繼續懷念兒時的青山綠水、紅肥綠瘦。而另一個極端就是,極盡批判之意識,將鄉村的前景和命運一棍子打死,顯示出詩對新聞調查的遙相呼應。懷舊型的詩,是憑借一個舊我形象,而批判型的詩,是圍繞他人的處境,二者都避開了對自我現時刻的觀察、探悉。或許,現在寫好一首“鄉村詩”的關鍵在于:我們如何在鄉村中(以及關于鄉村的反思中)經歷自我的曲折?
我們不應認為“雞鳴桑樹顛”就是一首鄉村詩的兌現,而“游戲宛與洛”為城市詩辨識出了一條邊界。但我們要注意到的是二者都關乎創作者自我的感受。詩句中選用的景觀、布景雖然有鄉村或城市元素,但并不限定為鄉村詩或城市詩的類型。如果這樣界定鄉村詩與城市詩(或鄉村詩與非鄉村詩)的關系,那就太便宜了。與“鄉村詩”相近的叫法有“田園詩”、“山水詩”或“隱逸詩”(而對立的叫法有“宮廷詩”,或者過于妖冶的“宮體詩”),但現在感十足的當代詩人如果在以鄉村現況為主題的一首詩中謳歌田園之美、山水之趣,就很可能被當成了“偽鄉村詩人”。把鄉村詩寫得像田園詩,悠然恬靜,只怕會被認為缺乏某種道德感,或者不了解當今的鄉村內情。贈送陶淵明一頂“鄉村詩人”的帽子,怕是人家嫌小,戴不上。
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連串問題是:誰在寫“鄉村詩”?誰是“鄉村詩”的第一讀者?構成“鄉村詩”的要素有哪些?我們意識到如今應該寫不同于早先的“鄉村詩”,這種意識——或可作為“后鄉村詩”的淵藪——帶來了怎樣的界限感、進化感?真的有一種更切合實際的、高級的鄉村詩?是什么力量催促我們去探察“鄉村詩”的新姿態:鄉村到底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每個詩人談論的鄉村印象(真相)之間存在怎樣的差別與共性?一個詩人的“鄉村詩”是否恰好是另一個詩人陳舊寫法的克星?如果我們現在寫不出與時俱進的“鄉村詩”,是否就意味著我們不(能)關切現實?鄉村意味著關切現實,而非鄉村就是不食人間煙火,就是宮廷詩所描述的權力高層的糜爛生活,或者再不濟就是宮體詩的純粹胡鬧嗎?要是把鄉村鎖定在唱一出對臺戲,是在對其他類型詩的拯救,這樣一個角色,就很可能限制了“鄉村詩”的手腳,好比是把鄉村出租給詩才不久,就要收繳巨額租金,難讓詩發達起來、繁茂起來。
我們很可能忽視了一個問題:與景色的鄉村屬性不同的是,人的鄉村性則不易捕捉到。這也正是我們在談論鄉村詩的前景時,會遇到的一個有可能動搖鄉村詩根基的阻力:鄉村之人隨時都可能不事稼穡。我們除了談論鄉村受到的污染和排擠——就好像鄉村已然成為現代生活觀念中的一個贗品、仿品——之外,往往擅長談論的就是農民的困境。但是,一個具體可言的農民有條件離開鄉村棲息在城區,從而主動喪失其鄉村性,變成無名、無根之人。變成我們中的一員,而不再是可歌可泣的他者。如果我們缺乏對自我或類我者的描寫技巧,就很可能無法適應鄉村動靜的移形換位。我們寫不好鄉村詩的根由恰恰在于無法透過已有的詞語體系看到自我。
鄉村詩就像是語言的一個郊區,是對一些詩人在習得的修辭層面感到嬌喘吁吁之際刮來的粗野之風,是緩解與緩沖,作為一個永恒中立的鏡像存在于斯。很難想象一個詩人只寫所謂的“鄉村詩”,并以“鄉村詩人”的頭銜厘清自身跟城里頭其他詩人的關系,尤其是同活在鄉村卻寫另類的其他鄉村詩人劃清界限。我們時代的癥結同樣在“城市詩”里也處處可覓。但一個明顯的境況在于,從鄉村走出去的農家子弟在成為詩人之際,他們已經丟失了鄉村屬性,他們變成了城里人,變成了一個對立于鄉村組織的客體(旁觀者),鄉村在他們驅車離開時的后視鏡里顯現真貌,有些頹廢、狼狽,他們哭鼻子、抹眼淚,為這后視鏡里漸行漸遠的鄉村、鄉愁和根。然而,他們回到城市之家寫下的不再是“鄉村詩”:詩,本質上不只在后視鏡里,不是那鏡面上淺淺一層的臨時漂浮物,而是鏡里鏡外萬般景象,就連那鏡柄、那后視鏡、那汽車、那高速公路統統作為貿易的一環也都算是詩的范疇。鄉村詩這個概念如同一塊摔落的鏡片破碎了,溶解在其他的類型詩中,或如板橋霜上一道轎車輪胎印記,預示著古老的情景交融出現了嶄新的變量。
令我們感喟的慘況不只在鄉村發生,也不只在城鄉交界帶最富有當今中國的荒誕色彩,正如鄉村依然有喜劇入夢,我們不可一門心思地杜絕其他的生路。但我們也不做和事佬。至少有兩點,在今后鄉村題材的創作中尤其值得留心:其一,類似明月、井、瓦上霜、外婆做的年味……的鄉村情景不可單一展示或作為懷舊對象,而必須在詞語層面上凸顯出反思觀念的皺褶,順著這種反思的間隙,追覓鄉村已消逝的鐘點,重建鄉村觀念圖譜;其二,著眼點依然是生活在這片鄉土上的百姓,關注那些個體的命運,但最為關鍵的是,如何讓他者的命運和作者的命運結合起來,簡言之,詩歸根結底就是談論(叩問)自我的命運,雖然有時假借他人之眼、之口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