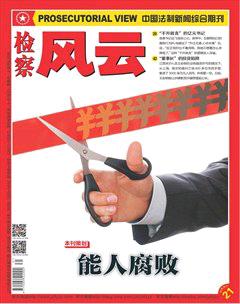漢籍之路
余義林
我提出“漢籍之路”,主要是借鑒我們?cè)缇吐劽澜绲摹敖z綢之路”的說(shuō)法,這樣會(huì)讓人們一聽(tīng)就明白。——柳斌杰
本書記述的是一段讓人永遠(yuǎn)無(wú)法忘記的日子。
話說(shuō)中國(guó)社會(huì)科學(xué)院學(xué)者孫曉在一次例行的學(xué)術(shù)交流中來(lái)到梵蒂岡的圖書館,看到了中國(guó)古籍遭受毀壞的情況,回來(lái)他就開(kāi)始查資料、跑圖書館和相關(guān)的專家進(jìn)行交流,全面了解流失國(guó)外的中華古籍的情況。學(xué)者們都是這樣,認(rèn)準(zhǔn)了某個(gè)選題或課題,往往會(huì)堅(jiān)持不懈的鉆研下去。何況孫曉本來(lái)就屬于比較認(rèn)“死理兒”的主,按北京土話講,他是那種做事很“軸”的人。作為社科院歷史所的資深研究員,多年的學(xué)術(shù)生涯更加強(qiáng)了他的這種性格。他把在梵蒂岡圖書館看到的古籍損毀的問(wèn)題,向有關(guān)部門和同行們反映。真所謂不通氣不知道,一通氣嚇一跳。讓孫曉特別震動(dòng)的是,不僅是在梵蒂岡,在法國(guó)、在英國(guó)、在美國(guó)以及韓國(guó)、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guó)家,都藏有不少中國(guó)古籍,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中晚唐,最近的也是清末流失出去的。就是說(shuō),有三百年歷史的中國(guó)古籍,在這個(gè)領(lǐng)域里算是最“年輕”的了。而國(guó)內(nèi)不僅對(duì)流散海外漢籍的存量缺乏全面的統(tǒng)計(jì),更沒(méi)有一個(gè)系統(tǒng)整理和出版的計(jì)劃。其實(shí),在全世界的各個(gè)角落,每天都發(fā)生著中國(guó)古籍損毀的情況。如果再不采取行動(dòng),很可能若干年后,留給我們的只有巨大的遺憾。
“這是個(gè)工程。這一定得是個(gè)大的工程。因?yàn)榇嬗趪?guó)外圖書館、民間機(jī)構(gòu)及個(gè)人手里的中國(guó)古籍太多了,經(jīng)過(guò)我這幾個(gè)月的粗粗統(tǒng)計(jì),可能有十萬(wàn)冊(cè)之巨。要從這里選取有價(jià)值的版本,這得是個(gè)多大的工作量啊?”在歷史所每周的例會(huì)之后,孫曉總是要說(shuō)起這個(gè)話題。
“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我們的力量肯定不夠。這可是一件大事情,應(yīng)該努力讓它成為一個(gè)國(guó)家項(xiàng)目。”說(shuō)這話的是社科院歷史所當(dāng)時(shí)的副所長(zhǎng)卜憲群。
“東亞與東南亞的文化圈,也有大量的漢籍。但是否要把它們也納入域外漢籍的范疇,恐怕要多方論證,或者還會(huì)產(chǎn)生不同的意見(jiàn)和分歧。”說(shuō)話的是歷史所的賴長(zhǎng)楊,一個(gè)和歷史打了一輩子交道的老學(xué)究。
“這部分漢籍其實(shí)量很大,排除在外也確實(shí)可惜。”卜所長(zhǎng)說(shuō)。卜憲群在讀碩士的時(shí)候,研究方向是魏晉南北朝史,到讀博士時(shí),其主研方向是秦漢史。在歷史所,秦漢魏晉南北朝是一個(gè)辦公室,所以他和同是研究秦漢史的孫曉,算是“同宗”兄弟。因?yàn)樗牟┦繉W(xué)位拿的比較早,所以大家都習(xí)慣叫他博士,而不是所長(zhǎng)。
孫曉和卜博士的思路一碰,碰出了一點(diǎn)火花:“關(guān)鍵是,我們這里所說(shuō)的‘漢’,應(yīng)該不是一個(gè)民族概念。或者,我們不應(yīng)該把它局限于民族概念,而應(yīng)該成為文化概念。”
接著這個(gè)話茬兒,大家紛紛認(rèn)為,把“漢籍”作為一種文化概念而加以拓展,顯然就準(zhǔn)確多了。尤其是我們周邊的國(guó)家,有哪些不是在漢文化的土壤中生長(zhǎng)起來(lái)的呢?
正是在多次討論中,一份定名為“域外漢籍珍本文庫(kù)”的報(bào)告就開(kāi)始在孫曉的電腦里出現(xiàn)了。搶救古籍固然是好事,但這畢竟是“民間”發(fā)起的文化項(xiàng)目,想得到官方認(rèn)可很不容易。那是2004年的隆冬。孫曉他們每到一地,就把凍得冰涼的報(bào)告拿出來(lái),放在相關(guān)人士和部門的辦公桌上,然后簡(jiǎn)單地陳述,然后謙遜地告別。過(guò)后也不敢使勁催。畢竟這么大的一個(gè)項(xiàng)目,驚動(dòng)的也不是一般的部門和領(lǐng)導(dǎo),領(lǐng)導(dǎo)們也很忙,不能很快做出回應(yīng)也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只能懷著一顆火熱的心,加上一腔愁緒,在沒(méi)有消息的時(shí)候盼望著消息,在毫無(wú)動(dòng)靜的時(shí)候等待著動(dòng)靜。
一晃幾個(gè)月過(guò)去,終于到了春暖花開(kāi)的時(shí)候。在此期間,包括孫曉在內(nèi)的歷史所的幾位學(xué)者,頻繁出動(dòng),先和出版界的朋友們接洽。因?yàn)楹瓦@件事情關(guān)系最近的就是出版,他們的最終目的當(dāng)然也是出版。黃社長(zhǎng)和周社長(zhǎng)就是在這個(gè)時(shí)候加盟的,或者說(shuō)他們最終是被孫曉們的執(zhí)著精神所打動(dòng)的——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師大出版社,愿意作為出版單位承擔(dān)域外古籍的出版工作。兩家出版社聯(lián)名,向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遞交了報(bào)告,將域外古籍整理項(xiàng)目列入國(guó)家“十一五”重點(diǎn)出版項(xiàng)目,同時(shí)聘請(qǐng)了國(guó)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zhǎng)、國(guó)家版權(quán)局局長(zhǎng)柳斌杰擔(dān)任“域外漢籍珍本文庫(kù)”編纂出版委員會(huì)的主任。后來(lái),柳署長(zhǎng)不僅同意擔(dān)當(dāng)此職,還提出了“漢籍之路”的概念(本書的名字就取自這里)。
2007年,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師大出版社決定上馬這個(gè)項(xiàng)目。盡管從經(jīng)濟(jì)效益來(lái)看,這套書還說(shuō)不好是不是能得到市場(chǎng)的認(rèn)可,甚至因?yàn)槠渲谱鞒杀靖撸赡苓€會(huì)賠錢,但是,“我們看到國(guó)家的珍本,看到這些好書沒(méi)有得到應(yīng)有的保護(hù),心疼!應(yīng)該讓它們回歸祖國(guó)。錢,畢竟不是唯一追求的東西。”這話是后來(lái)我采訪黃社長(zhǎng)的時(shí)候,他滿臉認(rèn)真告訴我的。和他的一席談,也讓我印象深刻。一個(gè)出版人對(duì)書籍、對(duì)傳統(tǒng)文化的感情、責(zé)任和憂慮,深深打動(dòng)了我。我以為,如果沒(méi)有這些出版家的鼎力支持,這套書的出版或許還會(huì)推后許久。
同年,在人民出版社和西南師大出版社的共同推動(dòng)下,《域外漢籍珍本文庫(kù)》終于作為國(guó)家“十一五”重點(diǎn)出版計(jì)劃獲批。在列入“十一五”之前,孫曉他們也沒(méi)閑著。他們?cè)趪?guó)內(nèi)外學(xué)界調(diào)研,動(dòng)員各界人士關(guān)注、參與這樣一個(gè)古籍編纂工作。他們知道,這套大型古籍對(duì)編纂和出版要求極高,要保證其質(zhì)量,必須有頂級(jí)專門家給予支持。或許是“精誠(chéng)所至,金石為開(kāi)”吧,經(jīng)過(guò)數(shù)百個(gè)日夜、數(shù)千次交談后,很多人都認(rèn)可了這個(gè)“民辦官助”的文化項(xiàng)目,數(shù)百位海內(nèi)外專家愿意為此聚集在一個(gè)名不見(jiàn)經(jīng)傳的小字輩的麾下。在本書的采訪和寫作過(guò)程中,《域外漢籍珍本文庫(kù)》的編撰和出版工作也同時(shí)進(jìn)行著高效率地運(yùn)轉(zhuǎn)。從2008年第一輯問(wèn)世,截至2014年底,《域外漢籍珍本文庫(kù)》已出版四輯共645冊(cè),其中正編第一輯90冊(cè),第二輯180冊(cè),第三輯103冊(cè),第四輯98冊(cè),還包括幾十個(gè)叢編本和單行本品種。文庫(kù)所收錄的海外文獻(xiàn)內(nèi)容豐富,包括宋元珍本、明清佳刻、名稿舊抄以及域外精著,共計(jì)600多種文獻(xiàn),絕大多數(shù)為國(guó)內(nèi)首度出版。將來(lái)出齊的時(shí)候,預(yù)計(jì)將達(dá)到800冊(cè),囊括2000多種來(lái)自海外的中華珍稀典籍。而目前出版的古籍已占項(xiàng)目總進(jìn)度的81%。可以這樣說(shuō),一個(gè)當(dāng)代中國(guó)宏偉而輝煌的搶救古籍出版工程,正在落下帷幕。
欄目主持人:黃靈 yeshzhwu@fox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