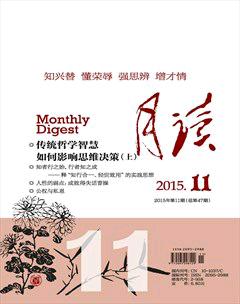許倬云談西周的歷史地位

周人以蕞爾小邦,崛起渭上,不僅代替文化較高的大邑商,成為古代中國的主流,而且開八百年基業,為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個時代。在新石器時代的中國,若干平行發展的文化,各在一個地區滋生發達,相互影響,彼此交流,遂使各個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漸接近。商王國的文化圈可能遠超過其政治權力所及的范圍,但是商人與各方國之間,大多有戰爭及貿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約只有商王畿之內的人以此認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個廣泛的共同意識。
殷商時代可以看作一個主軸的政治力量,逐步擴張充實其籠罩的范圍,卻還未能開創一個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終不脫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為大國,其立國過程必須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時代,周人于崎嶇晉南陜右的山地,采擷了農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長處,終于與姜姓部族結為奧援。此后翦商經過,也是穩扎穩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歸仁,也未嘗不是多所招撫的另一種說法。及至克商以后,歷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經營,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撫輯殷人,以為我用,再以姬姜與殷商的聯合力量,監督其他部族集團,并以婚姻關系加強其聯系,同時進用當地俊民,承認原有信仰。新創之周實際上是一個諸部族的大聯盟。周人在這個超越部族范圍的政治力量上,還須建立一個超越部族性質的至高天神的權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權也須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個“天下”,不是一個“大邑”;周人的政治權力,摶鑄了一個文化的共同體。周人克商,又承認商人曾克夏。這一串歷史性的遞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個文化秩序的延續。這是周人“華夏”世界的本質。中國人從此不再是若干文化體系競爭的場合。中國的歷史,從此成為華夏世界求延續、華夏世界求擴張的長篇史詩。中國三千年來歷史的主旨是以華夏世界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須逐漸進入這個主流,因為這個主流也同時代表了天下,開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對西北采守勢,當系由于以草原文化為主的西北,本來不是農耕的華夏文化所能進入。周人對東南采攻勢,則因為當地農耕文化的地盤,原與華夏農耕的本質只有程度的高低,沒有根本性的互斥。
分封在外的諸侯,一方面是華夏的代表,一方面也與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觸與交流。西周三百多年來,華夏意識滲入中原各地,自西徂東,無往而沒有分封網的觸角伸入各地;當地文化層次,一方面吸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華夏文化,經過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華夏世界終于鑄成一個文化體系,其活力及韌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擬。這一段過程中,政府不復僅以人治為本而趨于組織化與制度化。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點狀的殖民與駐防,而趨于由邦國與田邑層級式的組織。甚至世官世祿的貴族社會,也因若干新興力量的出現,而較為開放。華夏世界的韌力,經厲王、幽王兩度喪亂的考驗,王室的威權削弱了,但是華夏世界凝聚性之強,足以維護其世界于不墜。平王東遷,王綱不振,這一個政治體系竟可由強大的諸侯接過去,依舊維持了對外競爭的團結。齊晉先后領導華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荊楚,只能歸之于華夏世界內部因共同意識而產生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斷擴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極為強大。任何文化體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開放的“天下”觀念,這個體系就難以接納別的文化成分,也難以讓別的文化體系分享其輸出的文化成分。華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時,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觀念以及隨著道德性天命而衍生的理性主義。為此,華夏文化不致有強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擴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時期,南方的楚文化與中原華夏文化相激相蕩而終逐漸融合,為華夏文化增添了更豐富的內涵,對南方文化的吸納而統攝為更廣大的華夏文化,這一成就,也當歸功于華夏世界有廣大的包容性及開放性。
華夏文化體系,兼具堅韌的內部摶聚力,及廣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國三千年來不斷成長不斷擴大,卻又經常保持歷史性共同意識。世界上若干偉大文化體系中有些有內聚力強的特質,如猶太文化系統;也有的包容力特強,如伊斯蘭教與基督教的兩大系統。中華民族的華夏文化卻兼具兩個特點,而且都異常
強勁。
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是中國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為他體認了華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學說是華夏文化的闡釋,儒家理想人格是擇善固執,是以仁恕待人,這種性格,可稱為外圓(包容)內方(執善),也正是華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為中國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型期,正是在西周形成華夏文化本體的時候。
(選自《歷史分光鏡》,中華書局。作者為著名歷史學家,學貫中西,善于運用社會科學的理論和方法治史,研究領域主要為中國文化史、社會經濟史和中國上古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