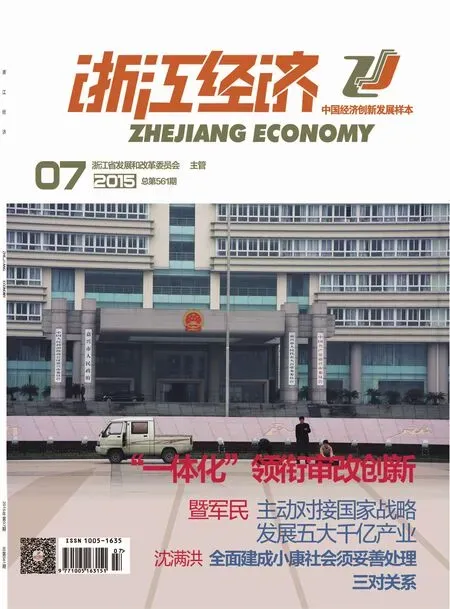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一季度的經濟數據尚未披露,從各方面傳來的消息,似乎有點不妙。總說是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增長軌跡從高速轉為“中高速”,但時下看來,下行的慣性不小。一不當心,滑落到我從提及新常態以來(2014.4.25起)一向只使用的“中速”概念,似乎也相去不遠了。
傳統的產業和經濟模式一路走衰,我們靠什么挽救中國經濟?其實,“條條大道通羅馬”,天無絕人之路,就看你選什么路子去走了。現在可以對沖經濟下行的最大亮點,恐怕就是十八大倡導的“創新驅動發展”,或者說是本次“兩會”上克強總理大聲疾呼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了。
說起這個“兩創”,浙江才是“原產地”。2007年浙江省第十二次黨代會提出的發展戰略,就是“創業富民、創新強省”這八個大字。隨后在二次(擴大)全會上,還專門通過了一個相應的《決定》。當時的解讀,認為這一戰略是改革開放以來浙江發展經驗的深刻總結,是浙江人民在創業創新偉大實踐中鍛造形成的浙江精神的集中體現,也是浙江繼續走在前列、再創發展輝煌的必然選擇。
如果說今天來回顧這個提法,除了肯定它的精準以外,恐怕還需要強調的一點,就是踐行“兩創”離不開體制改革。就像說了20年的“轉方式”,之所以進展甚微,就是因為不改就轉不起來。更何況有一個“四萬億”的危機應對,還輕而易舉地造成了舊體制的“沉滓泛起”。
從正面的角度總結歷史經驗,36年前的“大包干”改革,才是造就當時經濟奇跡最深厚的根源。執政黨困惑多年的溫飽問題,幾乎在一夜之間去除。那種翻天覆地的變化,的確是讓人印象深刻。但中國人又是健忘的,不信您看看解決當下的種種難題,不是加強領導,就是增加投入,而改一改阻礙“兩創”的體制、破除一下束縛“兩創”的機制,似乎很難真正成為我們工作的重心所在。
如果泛泛而論地講改革,也沒有多大的意思。再“高大上”,也超不過三中全會全深改的《決定》。而真正的難點,正在于敢不敢觸及利益格局。大包干講起來改的是農業經營體制,實質是國家、集體和個人的收益分配體制。一句“交夠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早已把專家學者多少本專著講的還云里霧里的道理,整得個明明白白、亮亮堂堂!
把“給公家的”明確、鎖定,剩下的你多勞多得,隨你,沒有天花板,這不就結了嗎!那老農民的起早貪黑,汗珠子掉地摔八瓣,還用得著你政府和領導們操心嗎?過往忙乎了30年,糧食就是不夠吃,但現在不用趕,也不用管,還“尥蹶子蹦高了干”,其間的落差,果然是“霄壤之別”了!
那么好了,眼下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如何解決好“發展起來的問題(鄧小平語)”。大體說來,是能不能就業和增收;能不能公平和正義的問題。對此,中央早有了“四個全面”的總戰略,其中也提示我們:發展要靠改革、治理要靠法治。改革本身就是創新,但創新卻是一個更寬泛的詞兒。我曾多次講過,凡對既有舊的改良,都可謂之創新。
經濟走勢嚴峻,當務之急是“穩增長”。老方子已然失效,再“打腫臉充胖子”也無濟于事。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靠“兩創”引爆的增量進行對沖,或謂周其仁先生曾提及的“創新突圍”。但對比一下當年“大包干”的分配改革,我們敢如法炮制嗎?我們的科研經費,可以買設備、可以坐車住店,但就是不能激勵給個人。現在更有一些“杯弓蛇影的神經”,這也不行、那也不行。不要說市場拿來的項目收益只能“隔岸觀火”,就連政府有意扶持的科研資金,也是干瞪眼“花不出去”,如不想惹什么麻煩,最后還是“一繳了之”。
周其仁先生最近在正和島創新大集的論壇上有個演講,新媒體的標題黨整了這么一句:“阿里巴巴一上市,天下多少年輕人就不睡覺了?”我受此慫恿,翻尋到相應的文字,原來正是說收入分配制度的:“因為創新風險極高,所以非有大獎不可。為什么要保護企業家?沒有一個超級大獎在那里,誰來玩?市場開出天價的大獎,沒有什么不公,頂多有點運氣成分,那也應當保護。政府、輿論、公眾要咬牙堅持,因為‘一將功成萬骨枯’”。
有利于創新的激勵機制,這是最最緊要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經濟走勢嚴峻,當務之急是“穩增長”。唯一的出路,就是要靠“創新突圍”


浙江省政府咨詢委學術委副主任、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