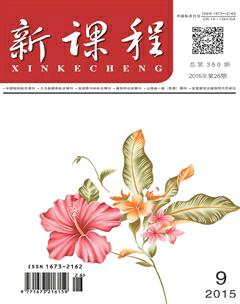托物寓意鳴不平
高生杰
韓愈的散文,明代茅坤將其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他的散文中,論說文占有重要地位,其論說文,除了弘揚儒道、反對佛教的政治、經濟、哲學著作和闡述自己文學創作思想的論文外,嘲諷社會現實的雜文更具有戰斗鋒芒。這類文章,在他青年時代的作品中尤為突出。《馬說》(《雜說》其四)就是其中的名篇之一。
韓愈出身平民之家,弱冠之年赴京都長安應進士第,因無背景,三試不中。直至25歲,求人薦舉后,參加第四次考試,才好不容易登進士榜。然而在吏試場中又接連受挫,三試博學宏詞都未能入仕。他只得奔走于權貴豪門之間,多次上書求薦遭受冷遇,滯京十載,志不能遂,對社會現實積郁了滿腔怨懣。一般認為,《馬說》(《雜說》其四)就反映了他當時的情緒。
這篇雜文分為三段,第一段闡述伯樂難得,因而千里馬只能被埋沒。開頭“世有伯樂,然后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幾句,十分精彩,有引人入勝的效果。剛讀前兩句時,覺得此話似乎不符合事物存在的客觀規律,應是不管有無伯樂,千里馬總是存在的,怎么意思顛倒了呢?讀了后兩句,就不難理解了,若是世上沒有善于識馬的伯樂,千里馬是不能被發現的,現實正是如此,千里馬常有,而能發現千里馬的伯樂卻太少了。正因如此,它只能像尋常的馬一樣,委屈地茍活著,碌碌無為地老死于槽櫪之間。下面作者用一個“故”字做銜接,就把因果關系點明了,不但使人對“伯樂不常有”的現象產生的后果感到惋惜,而且引發人們對這種現象進行思索,開頭幾句,立論新奇,令人感到突兀,仔細體會,卻包含了千里馬和伯樂間的辯證關系,真是不同凡響的高論。清代王錫周評之為“起法超卓”(《古文小品咀華》),確有道理。
第二段闡述了在沒有伯樂的情況下千里馬的慘淡景況。“奴隸人”既然不識千里馬,當然不懂得如何飼養和使用、怎樣對待的方法了,只能和尋常的馬一樣喂養、使喚。千里馬“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日行千里的特長怎能得到施展呢!作者直接寫千里馬的不幸境遇,仍然是嘆息沒有伯樂這樣具有識馬慧眼的人。
第三段喟嘆世上并非沒有良馬,而是沒有識馬伯樂,抨擊那些站在千里馬面前卻大嚷“天下無馬”的人是有眼無珠。這些人駕馭著千里馬卻不會發揮它的全部才能,面對千里馬的不平之鳴又不解其意。這組排比句有力地鞭撻了對千里馬一無所知的“執策人”,把他們無知、愚蠢、庸碌、無能的嘴臉勾畫得淋漓盡致。最后,以嚴厲的語氣詰問“其真無馬邪”,再次指出,不是沒有千里馬,而是沒有認識千里馬的伯樂。結尾鏗鏘有力,表達了作者的激憤情緒,而且巧妙地回應開頭,讀了使人有一氣呵成的雄健氣勢。
這篇雜文通篇說馬,其實,真正說的是應當如何對待人才。韓愈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文學家,從這篇短文中,可以看到他精湛的藝術技巧。
構思巧妙,委婉含蓄。作者對權貴當道、扼殺賢智的社會現實非常不滿和憤懣,但在文中卻沒有采用直抒胸臆的寫法,他在文中以極其巧妙的構思來表達自己的憤怒情感。他用通篇比喻的手法,以千里馬比喻自己和社會上的賢人智者,以伯樂喻統治集團中知人善任的明智人士,以“奴隸人”“執策人”喻昏庸無能、賢愚不辨的權貴,用千里馬不遇伯樂的悲慘景況喻社會現實。這種通篇不出現本體的托物寓意,借題發揮的寫法,不僅構思新穎,曲折委婉,且有分量,耐人尋味。韓愈提倡“文以載道”,即以“道”(思想內容)為靈魂,去充實“文”(形式)的肉體。《馬說》體現了這個觀點,觀點鮮明,說理透徹。這篇雜文雖用曲筆,但沒有晦澀之嫌,讀來饒有情趣,古人以千里馬比喻賢人智者的文例不鮮,如郭隗以“千金買骨”的故事,說服燕昭王“請自隗始”而賢者紛至;汗明借用“驥服鹽車”的故事,希望求得春申君的重用等,都是流傳至今的美談,但這些例子的共同點都是歌頌統治者納言從善、禮賢下士。韓愈以人們熟悉的千里馬為材料,使人很容易地理解千里馬就是指人才的道理。他沒有為統治者唱贊歌,也沒有對當權者寄予厚望,而是別出心裁地傾瀉自己的怨恨,諷刺權貴的愚蠢,揭露社會的黑暗。千里馬被踐踏埋沒,就是杰出人才受排擠受摧殘,這種毋庸置疑的道理說得十分精辟,比前人的寓意更加深刻,思想內涵更加豐富,給人以啟迪和教育,具有積極的社會意義。
語言簡潔,文筆犀利。全文總共只有151個字,但包含的內容卻非常豐富,可見其文字精練、功夫之深。如寫千里馬受糟蹋,“辱于奴隸人之手,駢死于槽櫪之間,不以千里稱也”幾句中的“辱”“駢”“稱”字,“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句中的“見”“等”字,“策”之、“食”之、“鳴”之、“臨”之等,均言簡意賅。“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則使封建權貴的丑態躍然紙上,十分生動,筆鋒非常犀利,表現力極強,無怪連柳宗元都說韓愈“猖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與司馬遷“相上下”而“過揚雄遠甚”,可見韓愈的文字表現力已達到爐火純青的程度。
參考文獻:
汪德懷.《馬說》的教學策略[J].語文教學通訊,20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