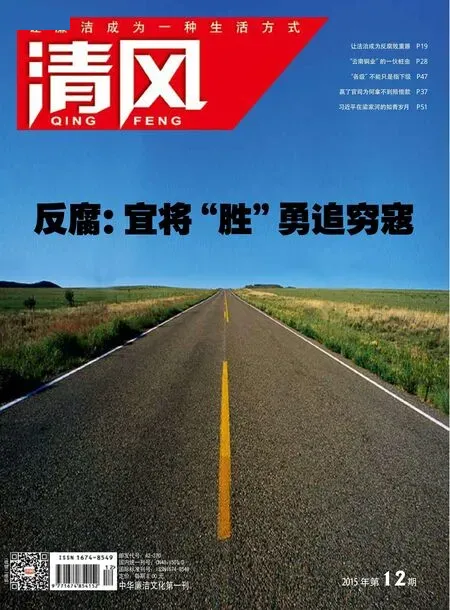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文_冷月
雄關漫道真如鐵,而今邁步從頭越
文_冷月

說到“打虎”,除了武松,許多人還會想起蔣經國。1948年,由于濫發紙幣兼官商勾結,國統區經濟瀕臨崩潰。為挽狂瀾,蔣政府試行“幣制改革”。此舉被寄予莫大厚望,當時的《中央日報》喻之為切除發炎的盲腸:“割得好則身體從此康強,割得不好則同歸于盡。”蔣經國奉父命親赴上海操刀,壯志滿懷地號召,對付那些抵制幣制改革的官商要毫不手軟,并且“只打老虎,不拍蒼蠅”。
的確,打虎之初,他的“鐵腕”迅速見效,就連杜月笙的女婿、兒子也與其他62名巨商大戶一道被捕。一時間,滬上為之震動,物價有所穩定,境內外媒體盛贊蔣經國為“國民黨的救命王牌”“蔣青天”“活包公”“中國的經濟沙皇”。可他很快碰上了硬骨頭——杜月笙舉報:你家“表弟”孔令侃的揚子公司也在非法囤積物資!結果,在宋美齡和蔣介石的親自干預下,蔣經國不得不放過孔令侃,虎頭蛇尾,威信掃地,揮淚離滬。
“經國打虎”留給我們何種啟示?敗退臺灣之際,他在日記中所引述的蔣介石評語,正可用于為“打虎”作結:“此次失敗之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成熟與確立;而舊制度先已放棄崩潰……焉得不為之失敗?”
可今日之“打虎”,比當年“經國打虎”的形勢不知好了多少——全國一盤棋,中央有效統領各級各地,而非蔣時代的地方割據、派系林立、陽奉陰違;政局穩定,可以心無旁騖,而非動蕩不安、不得不投鼠忌器;最高層決心刮骨療毒,全力支持而不是動輒掣肘……縱然“雄關漫道真如鐵”,也已完全有條件“邁步從頭越”。
關于腐敗問題,英國思想史學家阿克頓勛爵有句名言廣為流傳:“絕對權力導致絕對腐敗。”換言之,假如沒有了道德、法律、制度的種種約束,人性深處的惰性和貪欲必定會像驟然松開的彈簧那樣,強力反彈。想當年,隋文帝楊堅畢生“反對享樂主義”,強力壓制“奢靡之風”,卻未能避免身后兒子楊廣原形畢露、放蕩揮霍,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真正確立一套有效的機制,去扼住掌權者身上那個“好逸惡勞、喜奢畏儉”的“人性彈簧”。
在反腐取得階段性成果之際尤須深思,今天,我們拿什么來壓住這個“彈簧”?如果說打蛇須打七寸,那么“貪腐”之蛇的“七寸”在哪里?毫無疑問,“四風”不過是長在患處的菌絲、覆于蛇皮的鱗片;“官本位”、權力過度集中、權力配置不科學,才是蛇之七寸、病之根源;換言之,“公共權力運行鏈”上的“生態失衡”,才使得“四風”土壤肥沃、“貪腐菌絲體”頻頻出現。
從憲法、黨章的文本看,我們的公共權力運行機制,本來應該是個環環相扣的閉合系統。以黨組織為例,權力機關(黨員代表大會)產生執行機關,執行機關領導各部門和下級組織,下級組織領導黨員,黨員反過來通過選舉產生代表和權力機關。按照這個系統設計思路,它完全可以實現良性循環,將以權謀私拒之門外。
可現實中,一些地方官場,往往存在一把手獨大,下屬依附上級的亂象,有的權力大的地方領導扼住了當地整個體系的咽喉,變成了凌駕于黨組織之上的力量;官大一級壓死人,有的地方“大官”一切說了算,“小官”及普通黨員只有盲目服從的份,要想獲得較好的生存發展資源,唯有去討好“大官”——這種“在體制上不斷突出‘官’的核心地位”的制度,給了“官本位”以最深厚最肥沃的營養。“權力”與“腐敗”就這樣淪為一對“連鎖基因”。
一語概之,“權力生態失衡”才是貪腐之虎“打而不死”的根源。而看清了病癥所在,便可乘勢而進,盡快著手,在體制改革上下功夫,從上述權力配置、權力監督環節實現“突圍”,將兩年前王岐山那句“治標,是為治本贏得時間”的宣言落到實處,以“治本”來鞏固和擴大此前刀光劍影雷厲風行的“治標”成果,以鄧小平當年所說的“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的剛性制度,來遏制住“人性之惡”這個害人的“彈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