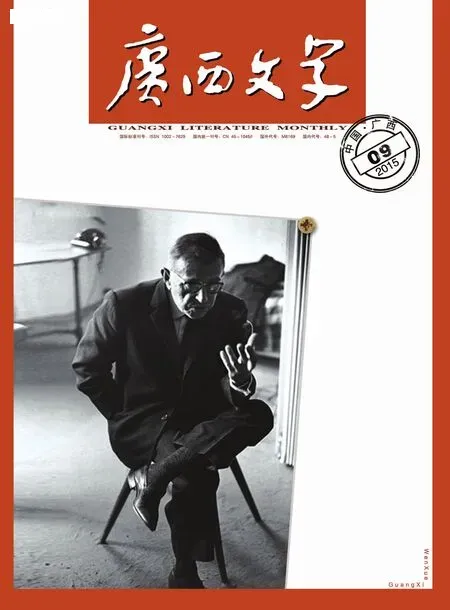風把什么吹走(外一篇)
寒 云/著
1996年有點遙遠了。那年我高考,就在我緊張應考的日子里,我的祖母因心肌梗死而猝然離世。父親把消息封鎖起來,不讓人告訴我。當我高考結束,返回老家的時候,祖母已經不見,只有莫花嶺上一抔新鮮的泥土,在風里被吹拂來、吹拂去,像漂在海上的一艘無帆船。
我自小就跟祖母親近,上初中之前,一直和她睡。她睡覺的時候無聲無息,呼吸幾不可聞,又喜歡仰睡,直條條的,肌膚有點微冷,晚上突然觸碰她,總以為她已經僵死了,常常把我嚇出一身恐懼的冷汗,哇哇地哭喊:“阿爸快來,阿奶死了,阿奶死了……”盡管如此,我還是愿意與她親近,愿意與她睡,因為她身上總有神秘的東西吸引著我。
祖母會講故事,盡管她講的故事不怎么精彩,但常充滿蠱惑力。她喜歡講鬼怪的故事,而且聲音在冷靜的夜晚,總是那么輕慢,有條不紊的,總給人一種想聽又怕聽的感覺,欲罷不能。祖母的鬼故事都是有據可尋的,故事里的人物都是村莊里的,有名有姓,輩分清晰,發生的地點又可以考證,真實得讓你無法質疑。她講得最多的,就是啞奶的故事。她說啞奶是一個啞巴女,是我的第七代祖奶,嫁給我的第七代祖公有恒公。啞奶不會說話,但卻是一個巫婆,她能給人下蠱,還會把小孩的靈魂招出來,讓小孩變得愚鈍。村里以前有幾個人被她下蠱,結果一輩子都瘋瘋癲癲的,直到死;而有三四個小孩也被她抓過魂,變得像豬一樣笨,連娶了老婆也不會生小孩,必須靠父母幫忙……村里人為了躲避啞奶,在有恒公過世之后,就把她鎖在了屋子里,不讓她出來害人。啞奶死之后,村里人沒有把她埋在莫花嶺上,與我的第七代祖公有恒公合葬,而是潦草地用一張破席子卷了,埋到一個離村很遠的荒坡上。不想這卻得罪了啞奶的鬼魂。有一天,一頭水牛無意間爬到啞奶的墳頭吃草,哇啦一聲,墳墓坍塌了,一群黑壓壓的蚊子從墳墓里面沖出來,徑直往村里飛來,見人就咬,見家禽畜生就叮,鬧得整個村子慌亂一片。很快,村里傳染了瘧疾,死了很多人。為了對付蚊子,村里人學會了用焚燒艾草葉子的方法來驅蚊,再后來又改用裝有敵敵畏的噴霧器殺滅蚊子。然而不管人們使用什么手段,一百多年過去了,村里的蚊子始終無法殺光。
“這都是啞奶的鬼魂在作怪,她死得不服氣啊。”祖母說。
為了證實祖母有關啞奶變蚊的說法,我特地去問過村里“知識最淵博”的伯父。伯父說哪有這種事,都是你奶奶編出來的。我回來跟祖母一說,祖母就瞪著一雙眼,驚慌地說:“你不能聽你阿伯的,他讀書讀壞了腦筋,不知道鬼怪的厲害。你不信,晚上就要被蚊子咬出幾個大包來的。”果不其然,那天晚上祖母雖用煤油燈燒凈了蚊帳里的蚊子,但下半夜還是有幾只大蚊子鉆進蚊帳里面來,在我的臉上咬出了幾個奇癢無比的大包。第二天,祖母邊給我擦風油精,邊告誡我說:“我就說嘛,得罪了啞奶的鬼魂,就要被咬啦,這不是應了嗎?鬼魂到處都在,你說什么,它都聽得見的,以后可不能再亂說話了,懂了不?”經過了這番“驚魂”的經歷,我自然再也不敢亂說鬼怪的“壞話”。
祖母既然知道這個世界上有人會下蠱,有人會巫術,有鬼怪出來嚇人害人,她就自然會有一套辟邪免禍的法子。她說河水里面有水鬼,專門抓小孩去抵命,所以小孩子絕不能下河游泳,如果要下河,必須跟大人一起去;她說泉水里有笑尿鬼居住,保護泉源,小孩子不能往泉眼里撒尿,誰要是往泉眼里撒尿,鬼就會循著尿味,半夜跑到誰的家里來陪他睡覺,讓他感冒發燒肚子痛;她說莫花嶺上鬼最多,因為那里埋的死人最多,所以小孩子不能亂到那里去玩,也不能吃墳墓上的野果,那樣會肚子疼,更不能吃莫花嶺上抓到的動物,比如蛇、穿山甲和貓頭鷹,這些動物都是鬼變化而成的,吃了會生怪病……為了讓我們這些小孩子不被鬼怪“傷害”,祖母給了我們很多“辟邪”的方法:去有墳墓的山坡上砍柴時,祖母會給每個人一個打著活結的草結子,據說這樣鬼怪一旦靠近我們,就會被草結子縛住,動彈不得;晚上走夜路,祖母會在每個人的口袋里裝上一枚銅錢,這樣夜鬼見了就會自動避開;在路上見到陌生人,心里要不斷地默念“鬼符不近我”的咒語,這樣就可以防止別人下蠱;去到別人家,沒有征得別人的同意,不能亂摘別人家的瓜果來吃,以防被蠱蟲迷惑心竅,患上失心瘋……
對于祖母來說,這個世界就是人鬼共存的世界,相對于人,鬼神法力更大,故而是不能得罪的。因為鬼神無處不在,所以禁忌也就無處不在。祖母每天做事,總是有很多禁忌,就連出工時邁個門檻,也要告誡一聲:不能踩著門檻出門,那樣會做事不順。我不知道祖母的這么多禁忌是從哪里來的,似乎在別人家的祖母那里,都沒有這么多的規矩。然而說來也怪,村里人雖然對祖母的禁忌常常不以為然,但一旦和祖母在一起,他們卻又正正經經規規矩矩起來,似乎約好了一般,每個人都遵循著祖母的告誡行事,該忌諱的話堅決不說,該避諱的事情也不會去干。有一次,我的小舅子海忠在莫花嶺上放牛時,從一座墳墓里抓到了一條萬花蛇,準備拿回家來燉湯喝。祖母知道了,就心急火燎地跑去阻止,讓海忠舅把蛇放了,說那是祖宗的鬼魂變的,不能吃,吃了會遭祖宗記恨,會讓他生怪病。海忠舅本來就不信邪,但見祖母有些氣急敗壞,也不想惹她不高興,于是悻悻地把蛇給放走了。像這樣的事情,在村里還發生過很多次,以致后來大家又約定俗成地達成了另一個默契,就是如果拿到了什么好東西,這東西又是我祖母忌諱的,大家就盡量隱瞞,不讓祖母知道。當然,這樣的隱瞞最終還是被祖母察覺到了,她沒有去跟他們理論什么,只是語重心長地跟我和我的兄姊們告誡道:要敬畏鬼神,不能學他們那樣,不然遲早是要被鬼神懲罰的。
上了中學,學習了科學知識,知道祖母的諸多鬼怪故事和忌諱都是迷信后,我就開始不太聽祖母的話了。這讓祖母感到很難過。每次我說了不吉利的話,或者是做了她所禁忌的事情,祖母不再像小時候那樣給我說一通話,而是默默地到神龕前燒香禮拜,嘴里喃喃不停,請求鬼神恕我冒犯之過。而往往這時,我總是給她一陣譏笑,笑她老腦筋,笑她迷信,笑她被鬼神迷住了心竅,是個怕鬼的膽小鬼。
1996年春節前夕,祖母在沒有任何征兆的情況下,猝然離世。她沒有留下什么遺言,也沒有留下什么財富和家當,這個守寡守了半個多世紀的平凡的女人,在無聲無息中離開了我們。她的離開,甚至沒有給我帶來多大的震動,因為幾個月之后,當我站到她的墳墓之前時,我的悲哀已經被思念所代替,眼角想擠出幾滴淚水,結果也沒有擠出來。
祖母的過世,似乎讓整個村子的人都在暗地里松了一口氣,他們曾經背著祖母做的一些事情,現在終于可以坦坦然然地去做了,再也沒有人用各種禁忌去約束他們。他們像解除了緊箍咒的孫猴子,毫無顧慮地,開始了一種自由自在、為所欲為的生活。短短幾年間,村里人就把小河里的魚類趕盡殺絕,使那條小河變成了名副其實的死河;有了自來水之后,曾經滋養了十幾代人的泉眼很快就被垃圾和廢土填平了;莫花嶺上的蛇、兔子以及貓頭鷹、穿山甲和呱呱叫的烏鴉,也全部被不懼鬼神的村民抓的抓、殺的殺,最終全部絕了蹤跡;人們平時再也沒有什么忌諱,什么話都敢說,什么事都敢干,于是村子里戾氣暴漲,原本安靜平和的小村落,現在被吵架斗毆、鉤心斗角所取代……
當生活變成一團亂麻之后,人們突然又懷念起我祖母在時的那段舊時光。他們懷念祖母那張虔誠而慈祥的臉,總是提醒大家:頭頂三尺有神明,不管做什么事,都不能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他們懷念祖母坐在村頭廢石磨上的身影,因為只要有她坐在那里,再狡猾的小偷也休想從村里偷走半根雞毛;他們懷念祖母逢年過節挨家挨戶送粽子和糍粑的禮俗,雖然東西普通平常,但那種濃濃的人情味讓人感到溫暖和喜慶;他們懷念祖母在清明節祭拜祖先時那套看似繁瑣的儀式,那種對祖先的虔誠和感恩,是發自內心深處的,沒有一絲敷衍和馬虎……然而所有的懷念,再也無法追討回來。
祖母走了,她的墳墓上長滿了野草,風每時每刻都在吹拂著它們,有時把它們吹綠了,有時又把它們吹成一片枯黃。我不知道風把什么吹走了,但我確切地知道,祖母化成了草尖上的花魂,輕盈地舞蹈,喃喃地訴說,與生養她埋葬她的這片天地同在,與深愛她的親人同在。
愛隨風在
每天,當夜幕從四面八方圍攏,黑暗即將降臨,在空中閑散飛翔的鳥雀,在山坡上到處覓食的牛群,在田地里為生活打拼的人們,紛紛地,都往故鄉深處趕。鳥雀羽毛上的陽光和塵土、牛背上風干的老泥和蠅尸,以及人們頭發上的草粒和夕陽,都將在返回故鄉后被啄理、清洗干凈。而當年關將至,清明來臨,奔波在天南地北的人們,也如這鳥雀、牛群一樣,帶著一身疲憊和榮辱,帶著各自不同的故事,不同的悲喜,紛紛地,也都往故鄉深處趕。這是一場宿命式的回歸,幾千年來,一直如此。鳥飛得再高,也高遠不過故鄉的天空,人們走得再遠,也永遠走不出故鄉的廣袤。
這場宿命式的回歸,構筑成故鄉永不褪色的鄉愁。唯有鄉愁,才是故鄉生生不息的秘訣,才是故鄉永久存在的根基。
在彌漫不散的鄉愁中,有一樣東西始終是人們邁不過去的坎,那就是時間。時間讓人們匆匆而來,又匆匆而去。時間的無始無終,帶給人們的卻只有短促而渺小的一生。人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日夜輪換中,就都漸漸老了,死了,留下新的一代,繼續長大,繼續老了,死了,如此循環往復,生死相銜。在這生與死的銜接中,唯有一樣東西能夠貫穿時間的風雨,撕破生死的銅墻,始終伴隨我們身邊,那就是記憶。死亡可以奪走一個人的肉身,卻奪不去他散落在風中的故事。那些故事,被風吹散到各地,如同蒲公英的種子,植根于人們的記憶之土,并在心里發芽,只要有人念叨到他的名字,緊隨而來的,就是他的影像,就是他的行跡,看似影影綽綽的,但卻無比鮮活,仿佛他依然還在村莊里走著、笑著、哭著,活得有聲有色。
在喑啞逼仄的時光隧道里,風中的故事,構成了故鄉最厚重、最遼闊的背景。
我是一個喜歡在風中搜尋故事的人。在故鄉,風中的故事如同草坡上艷麗多姿的花朵,散發著多種令人迷醉的香氣。翻撿那些交織纏繞的動人故事,突然發現這樣一個奇怪的現象:不管什么人,不管他在故鄉生老病死也罷,出外客死他鄉也罷,你要了解他生前的故事,必須返回故鄉深處,才能了解最詳盡的細節、最真實的影像。不管外界流傳多少個版本,唯有故鄉的那個版本是最真實和最豐滿的。故鄉就像一盒磁帶,保存著每一個人最隱秘的故事、最細微的情節。故鄉因為這個功能,變成了所有人生命歸途的終點站。當年華已逝,生命枯萎,每個人都渴望回到出生的地方,實現人生的輪回,這就是葉落歸根的思想。衍生這種思想的,正是源于故鄉的這種貯存故事的強大功能:模范一生的人,希望自己的故事能夠在故鄉得以流傳,并被后世子孫所銘記和贊頌;而做了壞事和犯了錯誤的人呢,外鄉容納不下他,也只有故鄉張開博大的胸襟包容他,并允許他享有一席長眠安魂之地。
正因為此,每天,每月,每年,你都會看見我開頭描寫的那種宿命式的回歸場面在故鄉深處動人上演。風中的鄉愁日夜飄溢,像一首旋律舒緩的老歌,用古老的傷感,把人們不知不覺帶到那段遙遠的記憶之中去……
小時候,我瞎眼的姑媽從遙遠的玉林地區回來探親。一晃眼出嫁十幾年,姑媽的臉上都是斑駁的線條,頭上的發絲也是銀灰色的,那雙不停向上翻動的白眼睛,使她看上去更像一個活在油布上的木偶人。那時候,祖母建造的老瓦房還在,門前的曬坪是用竹子搭建起來的,月明星稀的夜晚,姑媽就背對著老房子坐在竹曬坪上,一邊搖蒲葵扇,一邊給我和來看望她的人講述村里的老故事。她的聲音慈祥而好聽,講起故事來娓娓動人,經常能讓周圍的人都陷入沉思中,她嘆氣,聽著的人就跟著嘆氣,她微笑,大家也就微笑。她是我這輩子遇到的最具魔力的講故事高手,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人能超過她。幾乎整個家族史都裝在她的腦子里,她眼睛雖然看不見,但卻能把故事講得繪聲繪色,生動形象,仿佛那些人物、那些故事都是她親眼所見一般。在她回來探親的一個多月時間里,幾乎每到晚上,我家的竹曬坪上就會坐滿了人,大家都是來聽姑媽講故事的。那些夏夜,每個人都搖著蒲葵扇,每個人都認真傾耳聽,生怕漏掉了哪個細節。那一刻,風在夜色里微弱地流動,螢火蟲在天空漫天飛舞,孩子們在村里追鬧著——它構成了我記憶深處最溫馨的畫面。這畫面,后來就代替了故鄉這個詞語,成為奔波在外時我追憶故鄉的情感支點。
有幾個晚上,家里吃過了飯,曬坪上還沒有聚集村民,姑媽就教我念唐詩。我那時候還小,四五歲,但已經有了別于常人的記憶力,在短短幾天時間,就能夠跟著她背誦十幾首唐詩,還能在她背后跟風,南郭先生一樣讀完毛主席“老三篇”中的《為人民服務》。這讓姑媽既感驚訝又感欣慰,直夸我以后會大有出息。那時,我曾問祖母,姑媽會那么多東西,為什么不去當老師,她比我們小學那個什么都不懂的代課老師強得多了。祖母一聽,眼淚就來了,說你姑媽命苦啊,她哪里有這個享福的命哩?原來姑媽小時候眼睛是好的,人也長得漂亮。她念過幾年書,記憶力不錯,能背誦很多詩詞歌賦和革命文章,是村里的才女。“文革”開始之前,村里的小學沒有教書先生,當生產隊長的父親就想讓姑媽去當代課老師,然而就在即將開學的時候,姑媽嫁了人,后來又忙著生孩子,她當老師的機會就這樣錯過了。好不容易生下了我的表姐,她的丈夫卻突然生惡病死了。丈夫的死亡讓她肝腸寸斷,她哭得傷心欲絕,幾天幾夜不停息,恰逢村里鬧紅眼病,她也患上了,病毒趁機把她脆弱的眼睛給毒瞎了。孤兒寡母,自己又變成了瞎子,姑媽沒有辦法生活,只好搬回家來和祖母一起過。家里的生活本來就不好,加上兩張只會吃飯的嘴,日子就愈加艱難了。幾年之后,一個玉林人來村里打爆米花,聽說我姑媽是單身寡婦,于是就上門給他遠在家鄉的哥哥提親。祖母原本是不同意的,因為玉林太遠,姑媽又是瞎子,加上那邊沒有親戚照應,怕姑媽和我表姐過去后被人欺負。但姑媽沒有聽從祖母的勸阻,帶著我的表姐毅然跟著玉林人走了。
姑媽注定是苦命的人,嫁過去后生了一男一女,眼看日子即將變好起來,她的男人又突然病死了,丟下了她娘兒四人孤苦地生活。有一段時間,家里窮得揭不開鍋,姑媽整日里以淚洗面,覺得愧對三個兒女,又為自己的命運悲嘆,如果不是因為眼睛看不見,她早就上吊自殺了。好在我的表姐長大了,她嫁了一個家境比較好的男人,從而擔起了撫養一家人的重任。姑媽雖然遠在玉林,但心里時時刻刻想著我的祖母和父親,想念生養她的故鄉,日夜想著能回來再“看”故鄉一眼。為了了卻母親的心愿,我表姐攢了一點錢,帶著姑媽和我的小表妹坐了兩天兩夜的車,終于回到闊別多年的故鄉。姑媽回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給祖母下跪,向她哭訴內心的委屈和愧疚,后悔當年沒有聽從祖母的話。祖母本是有點怨的,但見到姑媽這樣,也就原諒了她。因為老房子沒有變,所以姑媽回來之后依然可以憑著記憶在房間里自由走動。她撫摸每一面墻壁,知道每根柱子的方位,還能準確地找到墻角里的米舂,需要的時候還能幫母親舂上一回米。有一次,她想讓我帶她去莫花嶺上看看。我因為害怕嶺上的墳墓,就沒有答應她。她后來又叫表姐帶她去,表姐沒有同意,祖母和父親也勸她別去。在大家的合力反對下,她只好作罷。我當時不知道她為什么想去莫花嶺,后來才知道,她是想去看看她前夫的墳墓。我并不知道祖母、父親和表姐為什么要那樣極力反對她,也許是因為擔心一個再嫁的寡婦去了會讓我姑爹的鬼魂不得安寧吧。
姑媽珍惜著在故鄉生活的每一天,每天她都要在竹曬坪上坐上幾個小時,什么事也不做,什么話也不說,就像一個凝固不動的聽風者。她坐在竹曬坪上被風吹拂著的背影,孤獨而落寞,后來雕刻成了我心中揮之不去的一尊塑像。一個月后,姑媽跟著表姐回去了。幾年后,姑媽病死在玉林,她的尸骨被埋到了那片異鄉的土地上。姑媽出葬的那天,祖母在故鄉的老房子前,默默地向遠處張望,眼里噙滿淚水。
時間繼續滴答滴答地走,很快就走到了1995年的夏天。此時姑媽已經去世十幾年了,她先前坐著的竹曬坪已經被拆除,就連她無比熟悉的老房子也要被推倒了,因為有了一點錢的父親準備在原址上建一棟新式的樓房,好讓守了一輩子寡的祖母能有個舒適的住所安度晚年。那年的夏天一如既往的明亮。父親翻了幾遍老皇歷后,選擇了一個良辰吉日,便招呼來一撥身強力壯、打著赤膊的人,用一根長長的木柱子,“一二三,哦——”,齊聲發力,把祖母那棟建了幾十年的老房子推倒了。泥墻倒下來的瞬間,瓦塵翻飛,漫天躥起的塵霧,在故鄉闊大的背影里,像炸開的一朵橘黃色大花。那一刻,仿佛預示一場時空的毀滅,又仿佛預示一場時空的新生。
父親的初衷是好的,但他忘記了這所老房子對于祖母的重要性。房子推倒的時候,祖母就站在高處,俯首看著陪了自己一生的房子被眾人轟然推倒,躥起一陣漫天的塵霧。等到塵埃落定之后,她有老半天沒有出聲。其時,祖母并沒有哭,嘴角反而帶著一絲微笑。父親以為祖母心里一定樂開了花,看著祖母的笑容,他甚至有些洋洋得意。他沒有察覺到祖母的微笑是僵住的,是一朵沒有生命的花,塑料花。
房子倒下去之后,眾人開始收拾殘土斷瓦。在墻土不斷被鏟走的過程中,祖母也在老房子的廢墟上走走停停地忙碌起來。說她在收拾殘跡,還不如說她在收拾記憶。憑借記憶,她能準確地在房子的各個角落里找到一些殘片,譬如一把斷了很多梳條的木梳,一只木椅子的半條斷腿,一枚壓在床柱下的銅錢等等。這些東西,都是在房子推倒之前認為不要了的東西,但現在,又被祖母一一拾起,并小心地,把它們整理妥當。幾天以后,老房子的一大部分泥土瓦礫被運到村道上填充了凹陷,每天車子、牛蹄和人腳踩踏不停,不出一個月,就和道路融為一體,再也看不出那是一堵墻的顏色。還有一部分泥土被拉到幾家親戚的自留地上堆放。據說這種泥土最適合種植南瓜,于是第二年春天,那里就長滿了肥碩豐腴如女子的南瓜藤蔓,在陽光的照耀下迅速拔節抽枝、開花結果,一片熱鬧非凡。父親要蓋的是水泥磚樓房,所以祖母老房子上的瓦片突然就失去了用處,一部分送給了窮親戚窮鄰居,用于修繕他們破爛不堪暫時沒有能力改變的老瓦房,另一部分質量好一些的,則賣給了外村的陌生人,是拿去蓋了學校還是修繕墳墓,不得而知。
祖母默默看著她積攢一輩子的房子,就這樣贈的贈,賣的賣,踩的踩,丟的丟,沒有做聲,她心里在想什么,也許只有風知道。等新房子開始打地基了,她開始分批處理她撿到的東西。斷楞條斷木梳斷凳子腿,統統在房前的空地上燒了,堅決不給父親拿去當柴火用于煮飯炒菜。幾枚銀幣和銅錢,用布片包扎好,分四個角落,埋到了新房子的柱基下。還有一些破損老舊的陶碗杯筷,她用稻草綁好,拿到莫花嶺上,埋到了爺爺墳墓旁的一塊空地上。埋完,她還對爺爺的墓碑丟了一句:“可便宜了你!”在我的想象中,那時的她應該沒有傷感,臉上應該掛著那副什么時候都安靜平和的表情,皺紋里靜靜流淌著的,也應該是1995年無比響亮的陽光。
父親在推倒老房子之前,先在后院起了一排水泥磚房子,以便推倒老房子之后作為一家人棲息之所。這排房子只有三個小房間,一個是父母的,一個是祖母的,還有一間是經銷店,三個房間中間隔著廚房。父母的房間安放了兩張床,可以睡四個人,祖母的那間因為要堆放雜物,只能安一張床,供祖母和弟弟安睡。家里那時還是窮的,東西盡管不多,但也夠父親受的。除了一部分寄存在左鄰右舍,剩下的不得不想盡辦法在這一排水泥磚房子里強制安置下來。于是,祖母的房間除了堆積如山的桌椅、籮筐、農具,還不得不裝下祖母的那口棺材。說到棺材,不得不多說幾句。祖母這口幾十年前早早備下的棺材,是用一蔸老楓木的四塊木板做的,很不多見。厚重結實的木板,給人一種凝重嚴肅的感覺。與這口老棺材相比,現在的棺材就太不像樣了,不說好一點的棺材要用十幾二十塊小木板才能合拼成,單講一些不良商家,為了賺錢,竟然在加工棺材時用組合板內充水泥漿來冒充棺材板,質量和檔次極低不說,價錢還昂貴得令人咋舌。這種棺材,釘裝潦草,制作漫不經心,盡管也涂著黑色的看似凝重的墨漆,但弄虛作假的質地給人的感覺就是不莊重、不嚴肅,沒能和死亡的悲壯混為一體,表面上是尊重死亡,實質上是對生命的敷衍了事,是對死亡的另類褻瀆,令人憎惡。老一代人在有生之年就備好了厚實的棺材,說明他們對生命更加珍愛,對死亡更加坦然和尊重。
據說祖母的棺材是祖父去世之前,留給祖母的唯一家產。但這只是傳聞,問過伯父和父親,他們說時間久遠,已經記不清楚了。不管傳言是否屬實,反正父親小的時候,這口棺材就堆在堂屋里了,他小的時候趴在上面睡過覺,我和哥哥姐姐小的時候也趴在上面睡過覺,家里來客人,凳子不夠的,也墊著屁股坐在棺材上,喝茶燒煙,自然得很,沒有誰感覺不自在。人未死,先備棺,這是那朱屯老久留存下來的習俗,據父親說,這樣可以“添官加壽”,圖的是吉祥如意。如果在城里,一進門就見個棺材橫在家里面,那是要嚇死人的,但在我的印象中,祖母的棺材不僅不可怕,反而是我最親近的東西之一。那里面平時裝著稻谷,平淡無奇,但只要不注意,哪天祖母就會從暖烘烘的稻谷里面挖出幾串金黃的芭蕉來,或者幾個軟乎乎甜歪歪的紅柿子來,讓人驚喜不斷。我和哥哥一直很想打開棺材來看看,一探究竟,但棺材板很厚重,我們小孩子很難打開,于是這口棺材便成了祖母的神秘保險箱,讓人經常浮想聯翩。一個夏日午后,我放學回家,突然看見祖母的棺材打開著橫在曬坪上,被六月的陽光曬出一片金碧輝煌。原來是父親發現棺材邊緣有白蟻的蹤跡,把里面的稻谷清理后,拿來暴曬驅白蟻的。我第一次看見了這口神秘棺材的內部。老實說,讓人大失所望,因為那棺材太簡單了,一目了然,就是三塊木板合成的一個槽子,橫在曬坪上,和喂馬用的食槽沒什么兩樣。但路過的大人們見到棺材,都嘖嘖稱贊:“好棺!真是一口好棺!”但好在哪里,他們一個字也沒說。
1995年夏天,父親的新樓房以驚人的速度拔高。祖母也忙里忙外,為施工隊煮飯、炒菜、遞物品,一點也看不出什么異樣。父親計劃在春節前搬進新家。在施工隊的加班加點下,計劃如期實現,一家人如愿住進了新房。祖母也從雜貨房里解脫出來,住進了新房間。1996年春節過后,新房的二樓樓頂封頂大吉之后,父親提著一罐氣味刺鼻的綠油漆,開始在家里忙上忙下,給一樓的十扇門窗涂漆。三月里的一天傍晚,祖母突然感覺胸口發悶,呼吸困難,她對父親說窗框上涂的油漆氣味太濃了,她有點不習慣。父親忙于裝修,不以為然,說胸悶你就好好休息吧。祖母聽從父親的話,沒有吃晚飯就早早回屋休息去了。第二天上午祖母全身無力,已經無法起身。到了下午,這個守了一輩子寡、過了一輩子窮日子的女人在新建的房子里死于心肌梗死,享年七十五歲。八天之后,祖母躺在她的那口楓木棺材里,在一片綿綿春雨中,被人抬到了莫花嶺上,長眠于她去年剛剛埋下碗筷的那片土地上,與她的丈夫并排一起,結束了她近六十個春秋、極其漫長的寡婦生涯。
祖母去世之后的第二年,一場霜雪天氣襲擊我們村。在一陣陣刺骨的寒風吹拂下,我家門口的幾棵果樹蔫了,枯萎了,死了。這些果樹都是祖母有生之年種下的,現在祖母過世了,也帶走了它們。祖母帶走的,絕不僅僅是這幾棵果樹,她還帶走了大半個村莊的記憶。祖母的老房子被父親的樓房取代之后,村莊就突然變得陌生了好多,很多人走進村頭,都會不由自主地一陣驚訝,以為自己走錯了村子,待發現沒有錯時,內心里卻掠過一抹莫名的失落。但失落了什么,又說不清道不明。去外地打工回來的人,這種失落感更加強烈。他們再也找不到記憶里那個熟悉的老房子,再也找不到那個熟悉又慈愛的老人:時常坐在院門口剝南瓜苗的老人,拿著棍子驅趕雞鴨出菜地的老人,跟所有路過的人都微笑打招呼的老人,傍晚時候高聲叫喚孫子回家吃飯的老人,陣雨來臨時大聲招呼村人“快點收谷咯”的老人,買東西時靠彎曲手指算錢的老人,農忙時幫全村人照看孩子的老人,唯一穿著上世紀大衩黑布褲子的老人,懂得用清水和瓷碗刮痧治病的老人,喜歡在村里一邊吃炒玉米一邊走路的老人,提醒所有人這要注意那要禁忌的老人……還有祖母的那口棺材,成了村里生前備棺風俗的最后一個符號,隨著祖母去世,那口棺材埋入泥土之下,村里再也沒有人肯在家里安置一口等死的棺材,屬于祖母的那個時代就這樣結束了。
姑媽和祖母,兩個女人,一個在異鄉悄然死去,一個在故鄉溘然長逝,她們的身影,隨同那所轟然倒下的老房子一起,永遠消失在故鄉的時空里。但她們并沒有真正離開,她們只是換了一種存在形式,依然活在風中,活在被她們愛著的和愛著她們的人們的心里。故鄉依然時常憶起她們,講述她們的故事,追憶她們的神思,讓她們漸漸變成鄉愁的一部分,供像我這樣漂泊異鄉的人用以療傷,撫慰游子那顆疲憊不堪的心。
記憶里的故事漸漸塵封,新的故事又要在風里揚起,時間從來沒有停止它編造故事的筆。我也是一個在外漂泊打拼的人,每年,我也和那些四處覓活的人一樣,在重要的日子里返回故鄉。每次回去,我都會到村里去走走看看,見見那些久不見面的親戚,和兒時的伙伴喝幾杯酒聊聊生活。閑聊里,無不是故鄉的記憶,無不是現實的光景。我們聊起兒時的趣事,也聊到外面世界的豐富多彩。盡管他們聊起時下的生活時都眉飛色舞的,但我知道他們都是一些普通的村民,在村里沒有什么地位,在外面就更加了,吃盡人情冷暖看慣嬉笑怒罵,很快對生活學會了逆來順受,成為這個時代最底層的人。他們在外面受盡委屈,人前低聲下氣,失去了做人的尊嚴,所以回到故鄉的時候,他們要竭力找回丟失的東西。他們穿上光鮮的衣服,洗漱一番之后煥發多年未見的神采,拿的手機和抽的香煙,在村里都是上點檔次的。他們試圖讓講話的口氣理直氣壯一些,眼里也盡量閃出讓人敬慕的光澤來。然而這些,在故鄉的風中,很容易就被掀開其表面的光鮮,露出人生的心酸和苦楚。只要走上三家,對同樣一個問題聊開去,很快就會掌握事情的真相。我也懶得去追究這些所謂的真相,因為他們那樣做也沒有什么過錯,誰骨子里沒有一根叫作尊嚴的筋呢?只要這根筋還在,處境再如何艱難都無法讓他們倒下,只要不倒下,生活就會繼續,村莊的未來就有希望。
雖然對他們來說,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充滿誘惑,但它無法與鄉愁相抗衡,他們依然眷戀著這片生養自己的貧弱的土地。其實他們之所以無數次地返回故鄉,就是因為他們在外面找不到屬于自己的根。唯有站在故鄉的土地上,他們才能感覺到內心踏實,因為他們的祖宗在這里,他們的親人在這里,他們一輩子的回憶在這里。
我兒子出生在外地,又在城市里長大,他對故鄉的感情沒有我這樣濃烈,每次,如果不是迫于我的壓力,他是不愿回的。他說他出生在城市里,城市就是他的故鄉。我曾試圖在他回老家的日子里,給他講講村里的老故事,關于我姑媽、祖母和老房子的故事,關于散落在風中的許許多多的故事,以期喚醒他對故鄉的感情。然而,收效似乎不大。也許,他已經不屬于坐在竹曬坪上聽姑媽講故事的一代人,已經不屬于在風中撿拾故事的一代人,已經不屬于為一株草一朵花一段往事傷感的一代人。甚或,他這一代人,已經不屬于故鄉,因為,他們本身就沒有故鄉!
今年六月,我回家給年近古稀的父親賀壽。在進村口的時候,一群小學生剛好放學回家。他們看見我,紛紛打聽這是誰啊,然后人群里響起了我四歲小侄子石文禹得意的聲音:“這是我的阿叔,我睿哥的爸爸,你們不知道嗎?”“哇——”其他小孩子恍然大悟一般喊起來,一個小女孩跑過來親切地問我:“文睿跟你回來嗎?我想跟他玩,聽說他在城里寫字獲得大獎,我要跟他學寫字。”我很好奇,說:“你怎么知道他寫字獲了獎的?”她得意地說:“文禹的阿公說的。”
那一刻,我突然感受到鄉愁的力量,無比強大。也許我兒子以后很少回到故鄉,但故鄉絕不會把他遺忘,更不會把他開除。不管他在何處出生,也不管他在何處長大,或者以怎樣的方式在別處生活,他終將被故鄉所銘記、所牽掛,他的故事終有一天會像我的姑媽和祖母那樣,吹拂在故鄉的山水之間,飄蕩在故鄉人們的心里、記憶里,成為鄉愁這座浩繁工程里豐富多彩的一部分。
是的,我要把這份鄉愁,傳遞給我的兒子。我要讓他知道,城市,不是他的故鄉,因為城市里沒有那份原始、單純、綿長、濃烈而甘醇的鄉情。這份鄉情,不是由鋼筋混凝土搭建而成,也不是由功名利祿組裝而成,它是由天空、大地、山川搭建而成的,靠無數的情感和愛組裝而成的。而在遍地鋼筋混凝土、物欲橫流的城市,人情味變淡了,零散了,風吹過城市,風里不會留下太多的東西,昨天剛剛搭建靈堂的地方,今天也許就已經布置成熱鬧非凡的超市和商店,昨天有人跳樓自盡的地方,今天也許已經擠滿了各種地攤。這樣的地方,不是故鄉,它只是大多數人漂泊人生里的驛站,而不是理想中那片靈魂的安息之所。
是的,我要讓風中的故事,在兒子這里得到傳承。只要風中的故事不間斷,愛就不會間斷;而愛隨風在,鄉愁就會永存,就連冷酷無情的時間,也無法把它像生命一樣熄滅和埋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