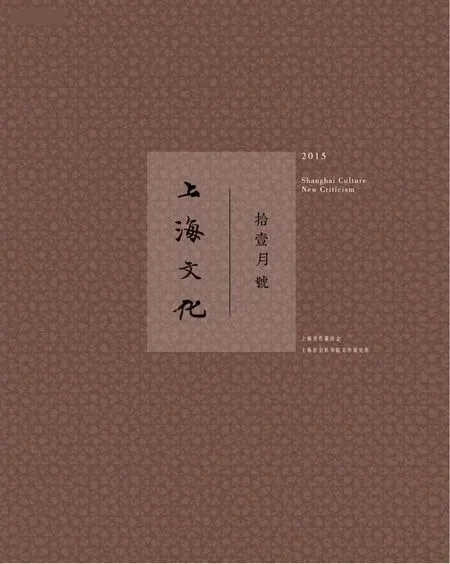史 詩①
哈羅德·布魯姆 翁海貞譯
史詩
哈羅德·布魯姆翁海貞譯
伊利亞特
赫克托爾對他的力量
非常得意,很是瘋狂,他依賴宙斯,
不尊重別的凡人和天神;他大發脾氣。
他祈求神圣的曙光女神趕快露面;
他威脅要砍掉我們高立在船尾的尖頂,
放出大火燒毀船只。在上面殺死
我們這些被煙子熏糊涂的阿開奧斯人。
這就是我的心里非常害怕的事情,
擔心眾神實現威脅,我們注定
死在特洛亞,遠離養馬的阿爾戈斯。
奮發吧,要是你想在最后時刻從特洛亞人的
叫囂中拯救阿開奧斯人的受難的兒子們。
你日后會感到非常苦惱,禍害造成,
找不到挽救的方法。
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定大志的。
你為何坐在羊圈內、聽群中吹笛的聲音呢。在流便的溪水旁有心中設大謀的。
基列人安居在約旦河外。但人為何等在船上。
亞設人在海口靜坐,在港口安居。
西布倫人是拚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處、也是如此。
(士師記5:15-18)
Ⅰ
西蒙娜·韋伊(Simone Weil)素愛《伊利亞特》和四部福音書,并且別扭地兩相比附,好似耶穌是希臘人,而非猶太人:
四部福音書是希臘天才的最后奇觀,正如《伊利亞特》是最初的奇觀……與《希伯來書》一樣,災厄是罪愆的確鑿征象,從而正當地成為招人鄙賤的對象。在這里,上帝也痛恨被制伏的敵人,宣判抵償所有種種罪愆 ——正是這樣一種觀念容許殘暴,誠可說使殘暴必不可少。在《舊約》里,除《約伯記》一些片段之外,無一處文本殆可埒美希臘史詩的意蘊。基督教上下二千載間,無論在行止或文字之間,《羅馬書》和《希伯來書》一貫深得賞識、閱讀、仿效。每有人犯下罹法,欲為自己辯白,總能切當地引據這些文本之中的文句。
這番解讀對《希伯來圣經》雖有些惡意,但也只是襲履陳腐,猶太人慣有的自憎,甚至在基督徒反閃族主義的疲敝隊列之中,又添上一樁范例。然而在這段話里別開生面的卻是,韋伊把《伊利亞特》讀作“力量的詩歌”這一強大誤讀,譬如她說:“其忿恨是唯一合乎情理的忿恨,因此忿恨發自人類的靈受制于力量,歸根結底,也即受制于物質。”韋伊所謂的“人類的靈”(human spirit)是指什么?她的靈自然是希伯來人的靈,而根本不是希臘人的靈,從而與《伊利亞特》文本格格不入。套用荷馬的措辭,她的文句原該將合乎情理的忿恨,也即阿喀琉斯和赫克托爾的忿恨,究因于“人類的力量受制于諸神和命運的力量。”因為這才是荷馬眼里的人類;他們不是幽囚于物質之中的靈,而是活生生的、在知覺、在感覺的力量或沖動。我在這里因襲布魯諾·斯奈爾(Bruno Snell)在《荷馬的人類觀》(“Homer’s View of Man”)一文的著名陳述。在他的評述里,阿喀琉斯、赫克托爾,以及其他所有英雄,甚至包括奧德修斯,“自視為諸種任意力量和玄秘威勢交戰的疆場。”亞伯拉罕、雅各、約瑟、摩西顯然不會自視為任意力量相犯的陣地;大衛,及其可能的后裔耶穌,自然也不會如此看待自己。《伊利亞特》當然是力量之詩,一如《創世記》、《出埃及記》、《民數記》無疑是雅威的意志之詩,雅威自有他的任意武斷和玄秘的方面,但他的力量是公正的,他的威勢也是狡猾的。
Ⅱ
依我看來,在古人當中,《伊利亞特》的詩人唯有一位對手,那就是《創世記》、《出埃及記》、《民數記》率多文本的本原作者,學者稱其為雅威作者,或J作者。除了二人同樣賦有的玄秘崇高之外,荷馬與J作者之間絕無共通處,并且二人以迥異的模式而崇高。在一種深層意義上,他們是爭競者,雖然彼此不曾聞知,或聽聞另一人的文本。他們角逐西方國家的意識。在西方文學和生活中,滋養分裂的感性的首要因素,大約就是此二人之間這場遲遲而起的紛爭。因為西方的特色就在于其苦惱感,也即認知趨向一個方向,精神生命則趨向另一方向。除希臘的思考方式之外,我們再無別的方式,我們的道德和宗教——外在和內在——則在《希伯來圣經》中尋找終極本源。
撒迦利亞(撒迦利亞書9:12-13)所宣達的上帝的訓諭這個負擔,預言了我們這場文化內戰永遠不會歇止:
你們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轉回保障。我今日說明,我必加倍賜福給你們。
我拿猶大作上弦的弓、我拿以法蓮為張弓的箭.錫安哪、我要激發你的眾子、攻擊希臘的眾子、使你如勇士的刀。
與《希伯來圣經》一樣,荷馬是圣典,也是知識普及書。兩者勢必依然是主要的教科書,唯獨莎士比亞序列第三位,這第三人最深刻地展現了希臘的認知與希伯來的精神這一分裂。一來由于荷馬的語言及其蘊含的社會經濟結構迥異于我們的時代,再加上另有其他一些原因,刻下倘要不曲解文本,尤其在閱讀《伊利亞特》之時,大抵是不太可能。無論我們是非猶太人或猶太人,信徒或懷疑信仰者,黑格爾主義者或弗洛伊德主義者,其間真正的差異在于雅威與奧林匹斯山上那些糾葛不清的宙斯及諸神,命運與魔性世界(daemonic world)。不論我們算是基督徒、穆斯林、猶太人或其駁雜的后裔,我們全都是亞伯拉罕的兒女,而不是阿喀琉斯的子孫。荷馬最強大的時刻,可能是表現人與諸神爭戰之時。雅威作家或J作者為我們描述雅各與無名的埃洛希姆摔跤之時,也同樣地強大,但這是獨有的例外時刻,并且雅各的搏持,并非要戰勝那無名的埃洛希姆,而是將他拖延。況且雅各不是赫拉克利特;他摔跤并不是出自本性,誠可說,他是要給我們一個瑰大的修辭,譬諭以色列始終不渝地求索一種無涯的時間。
因為西方的特色就在于其苦惱感,也即認知趨向一個方向,精神生命則趨向另一方向
在雅威作者、但丁、莎士比亞之外,《伊利亞特》是西方迄今產出的最非凡的著作,但倘若試作細想,我們在精神上接納或能夠接納多少?阿喀琉斯和赫克托爾固然不是同樣的人物,因為我們無法想象阿喀琉斯在城邦里過日常生活,但他們俱同樣地頌揚戰斗。對我們大多數人來說,抗戰不再比攻擊戰更理想,在《伊利亞特》里,兩種戰爭俱近乎最高的善舉,也即勝利。在一個平常生活即是戰場的世界里,還能想象怎樣的終極價值?確實,講述者及其人物角色心頭始終糾葛著和平的比喻,但是誠如雷德菲德(James M.Redfield)論述,這些比喻的旨意“并不是描繪和平之世,而是生動地烘托戰亂之世。”確實,在《伊利亞特》里,和平之世本質上是人類與自然之間的戰爭,一如戰場上虜獲戰利品,農人采摘果實谷粒。這就幫助解釋了《伊利亞特》何以無須頌揚戰爭,因為現實就是不息的爭戰,在這樣的現實里,若想得到好東西,只能掠奪或毀滅他人或他物。
荷馬式理想就是爭逐首席,這絕不是尊讓雙親的圣經理想。雷德菲德以及其他一些學者將《伊利亞特》讀作“赫克托爾的悲劇”,我以為實難如此解讀。臨死之際,赫克托爾被剝奪了悲劇的尊嚴,可以說,幾乎被剝奪了全部尊嚴。頗為反諷的是,這篇史詩實是阿喀琉斯的悲劇,因為他雖掙得了首席,卻未能克伏不免一死的忿恨。他只是半神,荷馬似乎就是以此將一個英雄定義為悲劇。然而,這不是圣經意義上的悲劇,圣經的兩難境地,也即亞伯拉罕和雅威在去往所多瑪的途中爭執,或者雅各與死亡天使相搏,實是這樣一種需要:好似自己能夠支配自己一般地行事,縱然心里明白,與雅威相比,自己絕不能自主。阿喀琉斯既不能自主地行事,也不能相信縱使相比宙斯,自己是束手無措之人。因此,哈姆雷特和莎士比亞的其他英雄的文化先祖是亞伯拉罕和雅各,而不是阿喀琉斯。
倘若將阿喀琉斯比較與其相當的人物大衛(在雅威眼里,他顯然是亞伯拉罕子孫當中最出色的),那么做“希臘第一英雄”究竟意味著什么?無疑不是做眾人當中最完全的人。一如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允當地評斷,最完全的人非奧德修斯莫屬。希臘第一英雄是能殺掉赫克托爾的人,那么換一個說話,在美國人的英雄背景里,阿喀琉斯便是西部槍法最快的牛仔。或許大衛也可能是那樣的人,況且,正如阿喀琉斯痛悼帕特洛克羅斯一般,大衛固然也痛悼約拿單,這一點提醒我們,大衛和阿喀琉斯皆是詩人。但阿喀琉斯坐在帳篷里發脾氣時,實是個小孩,瞻前顧后,正如布魯諾·斯奈爾所展示,這也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的魄力、感知、情緒俱各各分離。而大衛縱使兒提之時,便已賦有成熟獨立的自我(ego),再附以他的人生感、對其他自我的識野,他的情感天性,所有這些融匯為一個嶄新的人,一個雅威決定去愛的英雄,而且要藉他的子嗣使他不朽,永遠不會失去雅威的寵愛。迥異于西蒙娜·韋伊的解讀的是,耶穌只能是大衛的后裔,而不是阿喀琉斯的子孫。抑或簡單地說,阿喀琉斯是一個女神的兒子,大衛則是神的兒子。
在“現代”作家當中,唯有托爾斯泰堪可比擬《伊利亞特》的詩人和J作者
Ⅲ
在“現代”作家當中,唯有托爾斯泰堪可比擬《伊利亞特》的詩人和J作者,不論《戰爭與和平》或者晚年的杰作,即短篇小說《哈吉穆拉德》(Hadji-Murad)。在其文章《論伊利亞特》(允當地得到荷馬翻譯家羅伯特·菲茨杰拉德的評介,認為此文傳寫了荷馬的技藝是何其渺遠、何其典雅精煉),瑞秋·貝斯帕洛夫(Rachel Bespaloff)卻犯了一個迷謬,誤以為由于《圣經》和荷馬悉如托爾斯泰,兩者必定彼此相似。荷馬與托爾斯泰的共通之處在于他們皆非凡地平衡行動中的人與行動中的群體,唯獨這個平衡使史詩得以準確地表現戰斗。雅威作家與托爾斯泰的共通之處在于反諷的玄秘模式,這種模式悖違無可比擬的實體的不協調性,即雅威或普遍歷史與人之間慘酷的沖突或并置狀態之中的遭遇。但雅威對群體無甚興趣;在西奈山上,當福祉從精英人物轉移到眾百姓之時,他略帶不屑地自遠遠人。在荷馬那里,諸神與人相犯,或者命運與英雄的沖突始終不是全然不可比擬的力量之間的較量,縱使英雄必須死,或死在詩內,或死在詩外。
撇開二人對于自己(the self)的表現,雅威作者與荷馬之間的首要差異必然是雅威與宙斯之間不可名狀的差異。此二者皆具人性,然而將二者徑行并置之時,這個說法便顯得荒謬。埃里希·奧爾巴赫(Erich Auerbach)比較《奧德賽》的詩人與埃洛希姆作者,也是雅威作者的修改者,推源模仿的差異在于《奧德賽》強調“前景”,而《圣經》則仰賴潛滋的“背景”權威。這個對比固然有些道理,但我們若從《奧德賽》轉到《伊利亞特》,從埃洛希姆作者轉到雅威作者,其間的對比差異也漸消退。與雅威作者不同,《伊利亞特》不太需要的詮釋,但讀者若不下一番功夫探索其審美背景,也是極難領會這個文本。迥異于雅威作者筆下的人物,《伊利亞特》的人與弗洛伊德所謂的“心理學之人”鮮有共通之處。
約瑟可能是雅威作者為大衛所描繪的形象,他與父親雅各形成后-俄狄浦斯的絕妙對照,然而阿喀琉斯似乎從未與父親珀琉斯有任何關系,他的父親只是微賤老人的一種類型,等待老死這樣一種不值一提的死法。誠然,《伊利亞特》和J文本之間的酌然對比,在于普里阿摩斯的哀悼與雅各認定約瑟已死之時的悲痛之間的差異。在荷馬這里,老人多半僅配充作哭喪者,而在雅威作者這里,老人象征父輩的智慧和德行。雅威是亞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甚至在后世作為摩西的上帝、大衛的上帝、耶穌的上帝。然而宙斯不是任何人的神,或者可以說,阿喀琉斯也大可不必有父親。
普里阿摩斯的哭悼赫克托爾,僅在承接阿喀琉斯的哭悼帕特洛克羅斯之時,才能讓普里阿摩斯得以挽回泰半尊嚴,然而,年邁的雅各本人就是尊嚴,一如在他之前的祖父亞伯拉罕。尼采的刻畫十分公允。對于一個民族來說,當其理想是角逐首席的爭衡之時,必定要在尊奉父母這方面落后,而推崇父系和母系的民族則將爭衡轉移到時間王國,在時間王國里角逐,就不是為了一時的勝利,而是繼承福祉,那福祉的承諾落在無涯時間里更長遠的生命中。
雅威是那福祉的本源,在J文本里,雅威雖時常神秘莫測,卻從來不是漠然的旁觀者。沒有哪個希伯來作家能夠想象僅作觀眾的雅威,無論是看得入迷或是無動于衷。荷馬的神祇是人性的——太人性——尤其是他們能夠可惡地旁觀苦難,幾近當作消遣。阿摩司及其后的眾先知口中的雅威,距離荷馬的奧林匹斯宙斯遙遠得不能再遠。
可以說,在審美上,諸神作為旁觀者這一手法使荷馬踔越于《希伯來圣經》的諸作者。神祇觀眾無時不在的感覺,既為荷馬的人類聽眾提供妙不可言的相互感應,也確保阿喀琉斯和赫克托爾在比自己更偉大的崇高觀眾面前表演。以諸神為觀眾,從而增益、推崇荷馬這些英雄。雅威頻頻藏匿,你縱然哭著喊他,他也不會出來見你,或者,他可能冷不防地叫你的名字,你就只能應答:“我在這里。”宙斯的確反復無常,但終究為命運所拘。雅威會威脅你,而他自己卻毫無拘束。他不會做你的觀眾,好讓你得些尊嚴,縱然如此,他又絕非恝然。他拿紅泥搓出一個你,往你的鼻孔里吹他自己的氣息,把你做成活物。你讓他傷心或歡喜,然而正如弗洛伊德的看法,他實是你思慕的父親。宙斯卻不是你思慕的任何什么人,就算你是赫拉克利特,他的親生兒子,他也不會來救你。
荷馬的神祇是人性的——太人性——尤其是他們能夠可惡地旁觀苦難,幾近當作消遣。阿摩司及其后的眾先知口中的雅威,距離荷馬的奧林匹斯宙斯遙遠得不能再遠
Ⅳ
在荷馬這里,你為了做最優秀的人而上戰場,擄奪敵人的女人,盡可能活得長久,卻不必忍受可鄙的老年。然而,這不是你在《希伯來圣經》里爭戰的原因。在那里,你在雅威的戰爭里操戈,這震駭了那位苛刻的圣徒西蒙娜·韋伊。在這篇導言的結尾,我想比較兩篇浩蕩的戰斗頌歌,其一是《士師記5》的底波拉和拉巴的歌,其二是《伊利亞特》第十八卷的神妙之筆,阿喀琉斯為追回武器、盔甲、帕特羅克洛斯的尸體重新上戰場:
捷足的伊里斯這樣說完離開那里,
宙斯寵愛的阿基琉斯立即從地上站起,
雅典娜把帶穗的圓盾罩住他強壯的肩頭,
又在他腦袋周圍布起一團金霧,
使他的身體燃起一片耀眼的光幕。
有如煙塵從遙遠的海島城市升起,
高沖云空,敵人正在圍攻城市,
居民們白天不停歇地從城市護墻上
同敵人展開激戰,但一等太陽下山,
他們便燃起縷縷煙火,炫目的火光
直沖天際,使鄰島的居民都能看見,
好讓他們駕駛船舶前來救援。
阿基琉斯頭上的火光也直達天宇。
他來到壁壘前面塹壕邊,沒有加入
阿開奧斯人的隊伍,牢記母親的規勸。
他站在那里放聲大喊,帕拉斯雅典娜
遙遙放聲回應,使特洛亞人陷入惶顫。
有如陣陣尖銳的號角聲遠遠傳揚,
通告兇殘的敵人已經進襲到城下,
埃阿科斯的后裔的吶喊也這樣遠傳。
特洛亞人聽到阿基琉斯的銀嗓音,
個個心里發顫,就連那些長鬃馬也
立即掉頭轉向,預感可怕的災難。
馭手們個個驚恐萬狀,當他們看見
勇敢的佩琉斯之子阿基琉斯頭上冒著
目光炯炯的雅典娜女神燃起的火光。
偉大的阿基琉斯三次從塹壕上放聲吶喊,
三次使特洛亞人和他們的盟軍陷入恐慌,
有十二個杰出的英勇將士被他們自己的
長槍當即刺死在他們自己的戰車旁。
阿爾戈斯人興奮地把帕特羅克洛斯的尸體
抬出戰場,放上擔架,他的同伴們
淚珠滾滾圍著他,捷足的阿基琉斯
走在他們中間禁不住熱淚涌流,
看見忠實的同伴傷殘地躺在擔架上。
當初他用自己的車馬送他去戰斗,
卻沒能見他活著從戰場回來迎接他。
燒灼著雅典娜的神圣火焰,矯顧怒步,阿喀琉斯雖徒首上陣,卻更比渾身鎧胄之時可怖。他的怒吼令特洛伊人莫不震疊,并且女神的回應更增添了恐慌,因為他們知道所面臨的是超凡的神力。在先知以賽亞和約珥那里,雅威大吼之時,雖也吼得“像戰士”,效果卻迥異。這里的差異在于荷馬的人與女神——阿喀琉斯與雅典娜——凜凜威風地叱咤對喝。由于人神之間的力量懸殊得駭人,以賽亞不可能讓國王與雅威呼應吆喝喊殺,彼此助威,但這一天壤之別不能應用于阿喀琉斯和雅典娜。
在這篇淺說的開頭,我并置兩段題銘,其一是奧德修斯精敏地規勸阿喀琉斯,他若不回戰場,赫克托爾燒毀阿開奧斯戰船的“那一天”,“會是你日后銘心的痛苦”,其二是《士師記5》底波拉的戰爭頌歌。赫克托爾“沉酣于威力”(ecstasy of power)會給阿喀琉斯帶來“銘心的痛苦”(rememberedpain),因為力量必須以他人的痛苦為代價,而威力之沉酣源自重創敵人,造下“銘心的”苦難這一勝利。記憶仰賴于痛苦,這是尼采疾悍地以荷馬式分析所有意味深長的記憶。然而,這不是《希伯來圣經》所推崇的記憶。底波拉略帶辛辣的反諷,傲然嘲訕那些不肯攻打西西拉的以色列諸部族,尤其是呂便溪水旁的部族,滿心顧忌、疑惑、猶豫,“心中設大謀的”。她尤其斥責一如既往地過日子的部族,但人等在船上,亞設人在海口靜坐,在港口安居。她遽爾以犀利的詞鋒和道德力量,稱揚那些恪守與雅威的圣約而拚命的部族,那些克伏了“心中的大志”和“心中的大謀”的部族,發出贊美和勝利的雄偉頌歌:
西布倫人是拚命敢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處也是如此。
“高處”一詞既是描述語,也是贊美之辭。高處是保存圣約的處所。西布倫人和拿弗他利人去戰斗,不是為在以色列諸部族當中爭得首座,不是為擄獲西西拉的女人,而是為履行圣約,顯示emunah,即對雅威的信賴。在荷馬這里,人人皆知宙斯不可信。我們必須承認《伊利亞特》卓犖的美學價值。荷馬是詩人當中最好的,始終居席尊,然而他所缺欠的——甚至在美學上——正是信賴,相信神祇記得已經履行的圣約,缺乏感動希伯來詩人底波拉的那種崇高希望:
星宿從天上爭戰,從其軌道攻擊西西拉。
基順古河把敵人沖沒。我的靈阿,應當努力前行。
奧德賽
《伊利亞特》與《圣經》的激烈爭衡,為我們設定崇高的標準,而《奧德賽》卻是更豐贍的著作,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現代文學里
《奧德賽》顯然是《伊利亞特》的續篇,但對于所有讀者來說,卻是截然不同的詩歌。這兩篇史詩若是出自同一個作者,那么從《伊利亞特》到《奧德賽》之間的激變,便如《戰爭與和平》到《安娜·卡列尼娜》,抑或《失樂園》到《復樂園》之間的變化。這個比擬隱示荷馬的識野愈發窅然,亦如托爾斯泰或彌爾頓,但是從《伊利亞特》到《奧德賽》是從悲劇轉變為喜劇,從史詩轉變為傳奇,從阿喀琉斯的難逃死劫的憤怒到奧德修斯謀求匡復妻子、兒子、父親、家庭、王國之時的審慎。《伊利亞特》與《圣經》的激烈爭衡,為我們設定崇高的標準,而《奧德賽》卻是更豐贍的著作,這一點尤其體現在現代文學里。喬伊斯不曾創作題為《阿喀琉斯》的小說,龐德和史蒂文斯也不曾獻詩給《伊利亞特》的英雄;在他們之前的但丁和丁尼生,也皆十分癡迷尤里西斯。然而尤里西斯的歸家之途,與但丁分派給他的作為埃涅阿斯的對面角色,尤其是丁尼生介介然差委給他的角色,形成怪異的反差。
《伊利亞特》與《奧德賽》之間的反差的一個恒常謎團,是《伊利亞特》似乎離我們更遠,盡管此詩不似《奧德賽》具有如此眾多離奇或神妙的事跡。阿喀琉斯是一種遙遠的崇高,奧德修斯則是喬伊斯所想象的完人(the complete man),應對日常生活。《奧德賽》的傳奇套路是寫實地描述奇觀,并且似乎殊異與阿喀琉斯、赫克托爾競逐首席的悲劇世界。像我這樣一個并非古典學者的文學批評家,希臘文學得也一般,在閱讀這兩篇史詩之時,卻仍能深刻地體會這樣一位賅博的詩人,在一個傳統里生得太晚,其詩歌的迥然格局的整體性。塞繆爾·約翰遜——我的批評家偶像——陰沉地評道,荷馬之后的每一個西方詩人都是遲來者。依我看來,就《伊利亞特》而言,約翰遜說得十分允當,我無比深刻地感覺《奧德賽》乃是一部遲來的史詩,歌唱凋零之事(things-in-their-farewell)。這實是豐饒的反諷。
我們之所以有故事,因為故事拖延死亡,奧德修斯是奇崛的死亡規避者
我們無法想象阿喀琉斯生活在《奧德賽》的日常世界里,這個世界難容如此死心眼的英雄。你往西去,去亡人島看看,就會發現英武的阿喀琉斯或者埃阿斯(Ajax)的委頓的幽靈,注定永遠屬于第二等。荷馬的奧德修斯,超妙地迥異但丁和丁尼生所謂的埃涅阿斯這一個對面角色,然而實是埃涅阿斯的真正原型,而維吉爾筆下那位道學先生,實是不自覺地拙劣地模仿《奧德賽》中的英雄。苦命的埃涅阿斯須背負奧古斯都皇帝,奧德修斯則不受意識形態的拘束,除非渴望收復曾經為你所有之物這樣一個欲望,也被視為一種精神的政治。
正如批評家所指出,阿喀琉斯未脫稚氣,奧德修斯則須收起孩子氣,在一個會把你凍死也會令你被獨眼怪活吞的世界里存活。自制這一品德與阿喀琉斯格格不入,無疑也不是一種詩歌品質,并且表現在奧德修斯身上之時,似乎并不屬于道德體系。美國人妥當地將荷馬這位后期英雄視為第一位實用主義者,漠視各種無關緊要的差異。對于勢必要精明的奧德修斯來說,生存是一道漫長的障礙跑道,把你與家園阻隔了十年,你踏上歸途之時,又迫使你苦練又一個十年。你終于回到家,最沉重的苦難適才開始,因為在自己家中殺戮——縱使你是據上風的一方,狡詐地殺人,而不是被殺——實在是可怖的景象,可怕的程度勝過特洛伊迎風的大平原上最激烈的戰斗。
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就是那位有受虐傾向卻良善的波爾迪,乃是所有文學中最溫和的角色,盡管現代批評家拿荒謬的醒世說教指摘他。荷馬的奧德修斯是危險的人物,我們敬服他,卻不愛他。他是了不起的劫難生還者,全船的人都覆沒,獨他一人仍然漂浮在海面。你不會想跟他上同一艘船,可你又愿意閱讀或聆聽這么一個人的故事,因為競存是所有故事中最動人的。我們之所以有故事,因為故事拖延死亡,奧德修斯是奇崛的死亡規避者,不似可悲的阿喀琉斯,僅因為自己是半神而冒起焮天怒火,然而以實用主義的說法,他實是汲汲于定數。因此,希臘人當中最好的勇士阿喀琉斯的爭衡,迥異于奧德修斯的明智的沉酣(the sensible ecstasy),僅在不得已之時才爭戰,并且總是為鮮明的目標而戰。爭奪首席的欲望消退,再多活一日的意志煥發其自有的英雄氣概。
對于這個須航行歸家的島國之王來說,波塞冬的敵意何其兇猛,壓得奧德修斯只有兩種選擇:英勇的忍耐或者死亡,除非他肯忘記家園,屈從能為他所用的重重誘惑。他不是屈服者,從而成為其后每一個奮斗之人的表率。正如但丁和丁尼生所展示的,因為這個表率鼓勵人們培養欺罔他人這一能耐,從而他也是一個危險的表率。然而,倘若風起浪涌的茫茫大海與你作對之時,你又不能穩坐在陸地,那么就必須選擇僅剩的自然力量,在火焰中扯開嗓門,一如但丁的尤利西斯。在《伊利亞特》里,火意味著死在戰場,在《奧德賽》里則譬喻生存,火不再是閃亮的武器和盔甲的光芒,而是家里的爐火。在那里,佩涅洛普主持城邦,一面拖延求婚者,一面等待那位實用主義或遲到的英雄回到她身邊,一刻也未嘗忘記他正在回家:
她這樣說,激起奧德修斯無限傷感,
他摟住自己忠誠的妻子,淚流不止。
有如海上飄游人望見渴求的陸地,
波塞冬把他們的堅固船只擊碎海里,
被強烈的風景和險惡的巨浪猛烈沖擊,
只有很少飄游人逃脫灰色的大海,
游向陸地,渾身飽浸咸澀的海水,
興奮地終于登上陸岸,逃脫了毀滅;
佩涅洛普看見丈夫,也這樣歡欣,
白凈的雙手從未離開丈夫的脖頸。
1 The Epic(Bloom’s Literary Criticism 20th Anniversary Collection),本文節選自其中的第一章。
2《伊利亞特》第九卷,第 237-50行。羅念生、王煥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222-23頁。布魯姆引用Fitzgerald譯本。下同。
3 羅念生、王煥生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第483-84頁,202行。
4 譯者為行文方便而擅自改譯。
5 《奧德賽》王煥生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第二十三卷,第231-40行。
編輯/黃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