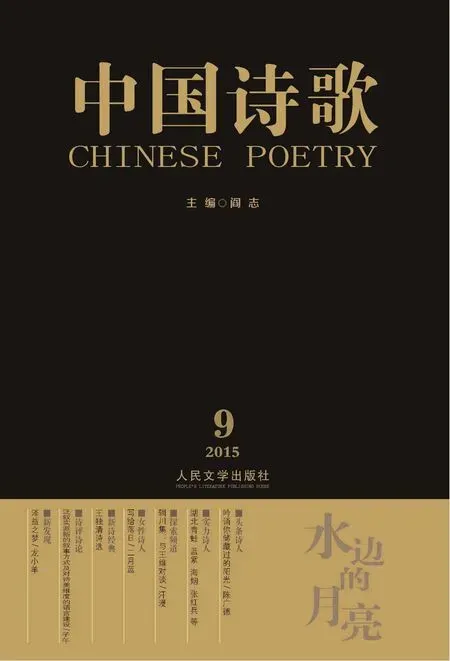黃明山的詩
HUANG MING SHAN
黃明山的詩
HUANG MING SHAN
天氣預報
天氣預報越來越新聞化了
或者說是新聞的前綴
每一陣風
每一場雨
霧。霾。雪。冰雹。還有pm2.5
都似乎暗示著不可回避的事件
不可告人的目的
接下來
洪水。泥石流。森林大火
愈加頻發的自然災害
從電視的屏幕蔓延開去
接下來
溫度養成了壞脾氣,高得出奇
重污染也會接踵而至
而我們還在那里努力,堅持
背景里的輕音樂,照樣
深情厚誼,耳熟能詳的旋律
讓我們一個一個,淪為
虛情假意的旁聽者
草的名字
都這么一把年紀了
還叫不出十種以上草的名字
只知道叫綠草,芳草,野草,小草,青青草
河邊草,抽象得就像一把亂麻
只知道一歲一枯榮
不曉得輪回中的春夏秋冬
這是多么遺憾的事情
如果每年僅僅認識一種草
也不至于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
卻糊里糊涂地
驚喜于草叢中蛐蛐兒的吟哦
或者歌唱
風是最敏銳的眼睛
具體到每一次搖曳
碩大的,渺小的,卑微的
一樣地拿出生命的真誠
三棱草,絆根子草,狗尾巴草
讓河流回憶最初的模樣
幸運草,四片葉
盡管很難見到
我們依然熱衷于張冠李戴
村莊
其實離城市并不遠
然而它叫村莊
或者說村莊就在城市的邊緣
卻時常被城里人遺忘
一只小鳥從村莊飛入城市
約等于誤入歧途
一棵樹的叫聲
讓小鳥的翅膀難以安放
平靜的陽光下
小鳥的羽毛抖動
遠離村莊的慌張
村莊太小
一滑而過
小鳥早就知道
村莊有原汁原味的芬芳
村莊在一片水光中
保持著最初的模樣
村莊總是讓小鳥也讓我忘乎所以
村莊約等于故鄉
是的還需要問一些什么
村莊變與不變
都是我夢中的方向
風乍起
正午的陽光明明晃晃
就像滾燙的隨時都會爆裂的玻璃
大約38°C的道路邊
三位女子手搭陽棚在招的
我注意到她們
是三種不同款式的裙裾
比陽光沉靜精致
一輛輛的士滿載而過
她們吆喝著“的士的士”
風乍起
她們的裙裾在倉皇中飛揚
而且越飛越高
無微不至的曲線
在倉皇中救贖了美麗
清明小記
油菜花高過頭頂
桃花滿樹開
敞亮的田野上也是風情萬種
梨花一浪一浪地白
蠶豆莖莖日上
招引練翅的花蝴蝶
果實還在睡夢中
看得見的生長
一陣雨就會出現一片奇跡
麥地綠成了童謠
抽一根麥秸試作麥笛
吹啊吹
遼遠的天空便觸手可及
小草無言是故鄉
是漸行漸遠的時光
年年踏青
年年都在同樣的地方
回回首
誰的內心沒有傷
這就是清明
淚水與微笑交匯的第一現場
四月的陽光
四月的陽光
從偏南偏南的高處啟程
帶著風的安寧
吹拂
每一個裸露的事物
跨過河流
深入原野
四月的陽光忘我地抵達
讓花朵所有的開放
沾滿燃燒的味道
或者飛翔的欲望
四月的陽光是一只手
一只無微不至的手
撫摸記憶的疼痛
與歡愉
走在四月的陽光之上
沉默再也找不到任何理由
鳥語由近及遠
遼闊無疆
巨大的照耀
就像沒有姓氏的力量
聲聲呼喚
久違的乳名或者腳步的匆忙
小地域之殤
想到一個人,與我交往
曾經是那么地真誠,熱烈
如今變成了冷若冰霜
想到一個人
從前給我懷抱
現在吝嗇到舍不得一個微笑
想到一個人很近復很遠
時常和我秉夜而談或者將我的電話打爆
月短日長,莫名其妙
謾罵之聲響過冬天的驚雷
想到一個又一個人更像一個人
而我,依然是我
我依然溫暖的手
握不住這泔水一樣的變化
我突然想到他們來自同一地域
小小的地域
蜿蜒或者無辜的地名
讓我欲哭無淚,滾落滄桑
不止是炎涼
多年前的刀傷
多年前的刀傷
斜插腰間
成了我隨身攜帶的氣象臺
每每隱隱作痛
常常夢中醒來,就知道
天,又要下雨了
這是不能自圓其說的奇怪
有時比電視里的天氣預報更為精準
回回應驗,絕無例外
不像晚點的火車
不像動不動就延班的飛機
刀傷的記憶狀若預言
刀傷拽動我的筋骨、血液和躍躍欲試的
不安,注視著時間的行走
任何痊愈的傷口
一定深植了疼痛的種子
多年前承載了多少年
瞧,如期而至的雨下得有模有樣
不是我忘不了刀傷
是因為刀傷還沒有把我遺忘
飛翔的壁虎
我站著
透過陽臺的紗窗
毫無目的地注視對面的樓房
高低錯落的空調,如同
一個個補丁
打在城市最起眼的地方
千篇一律的防盜罩
閃著賊亮賊亮的光
其中有幾戶
多年來,一直,沒有裝修
一根被風吹彎的下水管
昂著頭
如同飛翔的壁虎
我的目光上移
觸及深藍深藍的瓦
再往上
撞到了避雷裝置
我條件反射地蹲下,天
就霹靂般地壓過來
始料不及,也讓我措手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