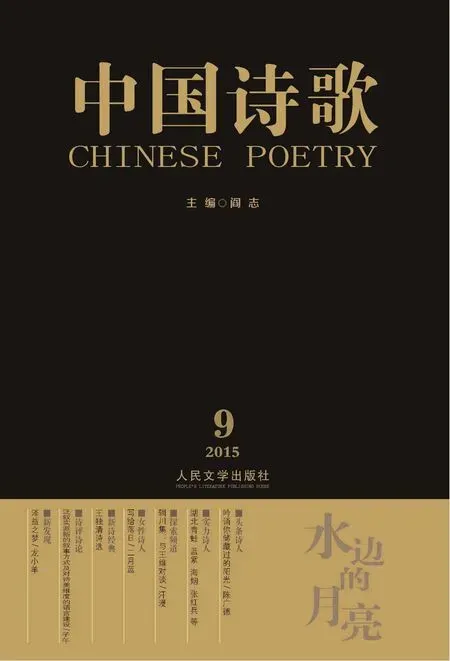泛敘實派新的敘事方式及對詩美維度的語言建設(shè)
■子午
泛敘實派新的敘事方式及對詩美維度的語言建設(shè)
■子午
一、新語境與泛敘實詩派新的敘事方式的形成
筆者曾在《新敘事主義詩歌現(xiàn)象及其提出》一文中指出:“早在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中國詩歌命定地要與這兩個重大的事件相遇:一是新詩潮(或曰現(xiàn)代詩運動)宣告結(jié)束——準(zhǔn)確地說,新詩潮運動結(jié)束于八十年代末;一是由于信息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的發(fā)展而導(dǎo)致大眾文化的勃興(始自九十年代中期)。”(見2008年第5期《上海詩歌》)①正是由于這兩個具有史學(xué)意義的重大事件,加上1993年全國范圍從文學(xué)界波及整個社會學(xué)界的人文精神危機(jī)大討論,在詩歌生成更為廣闊的文化背景上深深引發(fā)并促進(jìn)中國詩歌語境發(fā)生歷史性轉(zhuǎn)型,使得九十年代中期以來的中國詩歌不得不面對網(wǎng)絡(luò)技術(shù)空前的嚴(yán)峻挑戰(zhàn)和詩史上從未有過的災(zāi)難性生存危機(jī),而重新思考詩歌自身的生存方式、傳播方式及其存在價值等一系列根本性問題。
1.詩歌語境的轉(zhuǎn)型
語境(context),即言語環(huán)境,包括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而與語詞使用有關(guān)的上下文、時間、空間、情景、對象、話語前提等都屬語境因素。語境的概念是在1923年由英國人類學(xué)家馬林諾夫斯基提出的。他認(rèn)為語境又分為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詩歌語境(Poetic context)是指一種經(jīng)由詞象形式組合成詩歌結(jié)構(gòu)的語言秩序系統(tǒng)。這是我本人所下的定義。穆瑞·克雷杰將詩歌語境的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界定為一種“結(jié)構(gòu)嚴(yán)謹(jǐn)、強(qiáng)制、最終封閉式的前后關(guān)系”。苗時雨則把這一結(jié)構(gòu)具體化為:“一首詩詞句展開所形成的詞與詞關(guān)系的‘橫組合’(上下文、前后語等),又包括詞語形成過程中受到時代、社會、歷史、文化、習(xí)俗等影響所留遺跡的‘縱聚合’(語義的審美和歷史積淀)。正是這縱橫網(wǎng)絡(luò),構(gòu)成了一首詩的獨特的語境。”(《論詩歌的語境》)
眾所周知,隨著中國當(dāng)代社會在九十年代政經(jīng)格局的深刻轉(zhuǎn)型(史稱后新時期),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包括詩歌)的整體格局也發(fā)生了人文意義及史學(xué)意義的嬗變。那一場持續(xù)近十年、席卷整個八十年代的洶涌澎湃、驚濤拍岸式的詩歌浪潮,連同其一度叱咤風(fēng)云的大部分主將均已淡出歷史舞臺。這就意味著,被詩評家和文學(xué)史家稱為“新詩潮”或“現(xiàn)代詩運動”的中心已經(jīng)消失。唐曉渡稱之為“深刻的中斷”。他說:“八十年代先鋒詩寫作中普遍存在的‘不及物’現(xiàn)象……先鋒詩一直在‘疏離’那種既在、了然、自明的‘現(xiàn)實’。”(《解讀:關(guān)于九十年代先鋒詩》)
與此同時,中國詩歌在現(xiàn)象學(xué)及藝術(shù)學(xué)層面的結(jié)構(gòu)也發(fā)生了歷史性轉(zhuǎn)折和出現(xiàn)新的機(jī)緣,而作為詩歌生成的語境因素——包括情景語境和文化語境不可避免地出現(xiàn)了深刻和重大的改變(或轉(zhuǎn)型)。周雷這樣描述其時詩歌語境的改變:“八十年代前期曾有以《今天》詩派為代表的中心存在,八十年代后期也形成了‘非非’詩派和‘他們’詩派兩大中心。九十年代以來,中心完全消失,而且很難重新建立。”
據(jù)眾多詩評家的考察(筆者也持這一觀點),九十年代詩歌語境的歷史性轉(zhuǎn)型,主要是通過這兩個獨具詩學(xué)意義的語言現(xiàn)象體現(xiàn)出來:一是敘事話語的普化,一是反諷意識和喜劇精神的介入。筆者認(rèn)為,前者使中國當(dāng)代新詩潮從一個只會抒情而不會敘事(歐陽江河語)的“傷痕文學(xué)”和“反思文學(xué)”,轉(zhuǎn)型為對人性、生命本體和詩歌語言的回歸(與同時期的“尋根文學(xué)”小說遙相呼應(yīng));后者使中國詩歌從此注入了更具文化意味和美學(xué)價值的智性話語活力,將詩歌的寫作由一種受體式的感事、觸物而拓展為一種文化層面的心靈閃光式的主體促發(fā)。應(yīng)當(dāng)指出,這一新出現(xiàn)的語境秩序,與深深浸潤了三千多年農(nóng)耕文化血液的意象詩傳統(tǒng)已不可同日而語。
2.新的敘事方式的形成
毋庸置疑,一如苗時雨所言,詩歌語境的轉(zhuǎn)型——“包括詞語形成過程中受到時代、社會、歷史、文化……等影響所留遺跡的‘縱聚合’(語義的審美和歷史積淀)”,在新的詩歌中心來不及形成或相關(guān)條件尚未具備的當(dāng)兒,詩歌自身的運動及其史學(xué)進(jìn)程向我們提出了一個無法回避的嚴(yán)峻課題:時代呼喚著新的敘事方式的誕生!
正是在這個詩歌浪潮缺失、詩歌批評中心話語缺失、獨具個性的詩人及詩歌文本缺失(即“三缺失”)的特定歷史關(guān)頭,一批懷揣詩歌理想的青年詩人,祁人、陸健、子午(原名呢喃)、田原、洪燭、閻志、王明韻等,肩負(fù)著不謀而合的使命于九十年代初陸續(xù)來京尋夢。他們親身經(jīng)歷了現(xiàn)代詩(或曰新詩潮)運動的終結(jié)和第三代詩群流派造山運動的式微,共同面對該時期整個中國詩壇的沉寂、落寞和低迷,義不容辭地承擔(dān)著詩歌的命運和自身的文化命運,并試圖以各自的努力為中國詩歌探尋一種與彼時的人文背景及語境相適應(yīng)的新的敘事方式。
然而,這個時段中國文學(xué)(包括詩歌)深刻的內(nèi)在危機(jī)和創(chuàng)作群體的集體焦慮是顯而易見的。普遍的人文焦慮、話語權(quán)焦慮及語言焦慮深深地籠罩著九十年代以來的整個中國詩壇。從詩人到詩評家都憋著一股莫名的勁兒,意欲沖破詩歌將被邊緣化、甚至有被解構(gòu)之殆的局面。周雷指出:“重建中心意味著重建理想價值。”這就要求詩人“堅持人性深度的審視和理性高度的表達(dá),讓內(nèi)心和言說在超越中呈現(xiàn)真實”。
與全國范圍人文精神大討論遙相呼應(yīng)的,是文學(xué)界適時掀起的一股“尋根熱”。于是,回歸傳統(tǒng)、回歸生命、回歸人性、回歸本真、回歸自然、回歸文學(xué)、回歸主體、回歸語言……等一連串“回歸”,以及對“五四”時期的系列回顧文章充斥著彼時全國的報刊。而詩歌界也提出了“專注于寫作本身”(歐陽江河語)和“以寫作來承擔(dān)一切”(王家新語)的主張。祁人、陸健、子午等則有意識地在《中外詩星》、《中國詩人報》和后來的《中國詩壇》等詩歌報刊,組織創(chuàng)作和編發(fā)一批以寫實為基調(diào),并適度地吸收西方現(xiàn)代詩歌的某些藝術(shù)技巧,而突現(xiàn)本土性、民族性和漢語性特點的詩歌作品。這一以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青年詩人為主體的詩歌族群,由于在詩歌理想、人生閱歷及某些生活方式上的相近,進(jìn)而體現(xiàn)在詩歌的語言風(fēng)格、藝術(shù)傾向及審美立場上漸趨一致,并經(jīng)過約二十年(自九十年代初至今)的時間積淀和美學(xué)淘洗,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泛敘實派詩歌新的敘事方式及藝術(shù)個性。
二、泛敘實派詩歌的藝術(shù)特點
筆者在2005年10月出席第19屆世界詩人大會時曾呼吁:當(dāng)代詩歌應(yīng)提倡一種經(jīng)典意識,并對“經(jīng)典意識”這一概念提出了5個方面的因素或品格指標(biāo)。概括地說,經(jīng)典意識是指文藝創(chuàng)作或?qū)徝烙^念中,一種具有前驅(qū)性和史詩性思維、具有杰出的藝術(shù)獨創(chuàng)性和典型性理念、具有一定的文化積累及藝術(shù)建設(shè)意義的主導(dǎo)思想。大凡經(jīng)典性文藝作品,至少能體現(xiàn)出其史詩性視野、架構(gòu)及“一覽眾山小”的雄偉氣魄和非凡、獨立的思想深度、文化厚度、美學(xué)高度及藝術(shù)難度。具體地說,所謂經(jīng)典意識主要涵蓋以下幾方面因素或品格:1.對人類面臨的生存難題和生活苦難的承擔(dān),對人性及命運永恒悖論的深刻思考和感悟;2.對一定歷史時期的主流文化、權(quán)力話語和時尚性傾向的超越;3.在最理想的維度實現(xiàn)對傳統(tǒng)的批判繼承與突破,并使其具有獨創(chuàng)性或多樣性的藝術(shù)語匯、結(jié)構(gòu)手法和形象典型,呈現(xiàn)出其不可重復(fù)性的特質(zhì);4.在藝術(shù)本體論和文化本體論層面,注重作品多視角、多層面的豐富、厚重的文化容量;5.通過其作品所體現(xiàn)的非凡的開創(chuàng)和綜合的雙重意義,把自身顯示為某種新的藝術(shù)源頭或文化源頭(《當(dāng)代詩歌應(yīng)提倡一種經(jīng)典意識》)②。
從泛敘實派于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初形成到兩個世紀(jì)之交以來的二十多年間,該派7位代表性詩人先后共出版了各類詩集、詩論集近百部(如加上商震、潘紅莉、北塔……等詩人的創(chuàng)作,則至少也有一百五十多部)。縱觀泛敘實派詩人的總體藝術(shù)風(fēng)格及新的語言方式,主要凸現(xiàn)了以下幾個特點:
1.鄉(xiāng)村意象與城市文化符號兩種精神的融合。主要體現(xiàn)在祁人、閻志、王明韻等詩人的系列作品之中。如祁人詩中的“海棠”、“梅”、“茉莉”、“山谷”、“小溪”、“野風(fēng)”,閻志詩中的“山林”、“麥田”、“炊煙”、“鳥群”,王明韻詩中的“鄉(xiāng)野”、“土地”、“河流”、牲畜和作物等,都在語言的深潛層面折射了陶淵明田園山水詩的物象和意趣。在當(dāng)下我國城市化迅猛發(fā)展的進(jìn)程中,人們一方面要學(xué)會適應(yīng)并加快融入日新月異的現(xiàn)代都市科技與工業(yè)社會新的文化精神,另一方面該如何保持并強(qiáng)化人與自然及環(huán)境生態(tài)的理性關(guān)聯(lián),恰恰是身居都市而心懷天下的現(xiàn)代人所應(yīng)保留的一種“鄉(xiāng)村意識”。
2.憂患意識與客觀物象“聲形對稱”的多重交疊。主要體現(xiàn)在田原、子午、洪燭、陸健等詩人的系列作品之中。如田原在黎明看見正在向前奔跑的列車,便敏銳地感覺到了祖國的軀體里已經(jīng)患上的一種“哮喘病”:“我們都是懂得她病因的青年醫(yī)生/……她被在太陽下成熟、飽滿的向日葵的籽粒命中/而這棵向日葵曾經(jīng)是我們心中的太陽神/我們是沐浴著它的光芒長大的一代/小時候我們圍著它跳舞唱歌/長大了我們?nèi)园阉囱龊透桧?她卻倒在了血泊里。倒在了無根的向日葵下//一座新墳就這樣在我的心中/隆起,它高過了中國所有的山峰”(《黎明前的火車》)。又如陸健透過《魯迅的一首佚詩》發(fā)現(xiàn),這種悲劇意味首先就表現(xiàn)在“在食物的選擇上犯了錯誤”,更有甚者,在《重看曹禺話劇》里,“我們的糧食”竟是“吃掉我們的游牧民族”。在源遠(yuǎn)流長的文化史實及其現(xiàn)存的人文秩序里,我們已經(jīng)和正在為這種悲劇意味制造了多么豐富而堂皇的理由——從一代又一代人的失血或染毒的糧食、文化中。
3.對人類命運與死亡意識的“夢幻”式拷問。主要體現(xiàn)在田原、子午、洪燭、王明韻、陸健、閻志、祁人等詩人的系列作品之中。如田原“夢中的樹”被強(qiáng)行移植的命運,而它曾是詩人“夢鄉(xiāng)溫暖的驛站”,當(dāng)這棵樹“在夢中消失后”,馬車也“陷在泥濘的路途”,而枯樹作為樹木的一種特殊形態(tài)(死亡形態(tài)),當(dāng)它進(jìn)入詩人的眼簾,那被毀于一旦的傷痕累累的樹——“一棵千年的枯樹”,“它被剝光的軀體/干裂的傷痕無法愈合”;又如子午的《港口城市》,從一架“藍(lán)鯨巨骨”起初在博物館里一度被“誤讀”,到后來真的有一條巨鯨擱淺在這個城市的海灘,并迅速成了晚報的熱點新聞。
4.獨特的心靈擬象和通感式綜合。主要體現(xiàn)在田原、子午、陸健、祁人、洪燭、王明韻、閻志等詩人的系列作品之中。例如“風(fēng)”這一人們早已司空見慣的自然物象,當(dāng)它一進(jìn)入田原的詩作《風(fēng)》中,這風(fēng)便成了“對萬物一視同仁”的“大地上惟一的法官”,這“風(fēng)是手臂,又是利斧/它輕敲著問候所有的窗戶/它劈倒無人敢碰的老樹”;與此同時,這“風(fēng)”不但能夠在石頭里留下自己的“腳印”,它還能把自己的汗水“滴落在大海里”,甚至滴在“人類的脈管里”,并永不停息地“疾走”。又如子午的《月色(二)》,詩中的“月色”既是某一場景的背景,它同時又是該場景中的一個角色(主要意象),并與詩中的“狼群”構(gòu)成了獨特的“二重唱”關(guān)系;從“狼的鼻尖上沾著草屑”及其“楚楚動人”的叫聲,到最后狼群在“月色”中消失在一片“林間的開闊地”,也許讀者此時才猛然省悟到,這狼群同時也是“月色”的化身。
5.古樸厚重的人文遺跡與心靈故鄉(xiāng)的居所。洪燭是泛敘實派中一位很獨特的詩人,他自認(rèn)為祖國西域的人文氣質(zhì)與他的性格最為吻合,并為他的詩歌創(chuàng)作提供了一片豐沃的“新大陸”。“早晨醒來,覺得自己越來越像另一個人/他的血緣是我繼承的最大一筆遺產(chǎn)/……我不是孤兒,我的詩篇向全世界宣布/我有一位偉大的父親/他沒有領(lǐng)養(yǎng)我,而是我認(rèn)領(lǐng)了他!/……我要用筆來完成他的刀劍無法做到的事情”(《阿勒泰的蒙古族詩人》)。洪燭就像臺灣的女作家三毛,喜愛上了獨行式的流浪,一路上踽踽獨行,漠風(fēng)吹過帕米爾高原西部的塔什庫爾干,白云般的羊群沐浴著金色的陽光,“我來了,在滴血的殘陽下/左手呼喚一匹馬,右手呼喚一把刀/愿意做西夏的最后一名士兵/……我要在上面刻寫自己的名字——/‘洪燭,最后一個西夏人。一個詩人……’”(《在西夏的版圖上》)。
6.對民族化和本土化風(fēng)格的努力及建設(shè)。主要體現(xiàn)在子午、陸健、祁人、洪燭、王明韻、閻志、田原等詩人的系列作品之中。如子午的《從一顆星開始》,筆觸從“黃膚色的植物”到“伸展著”一面面“漢語天空”的葉子,更是賦予自然萬象以民族文化的形象和意象,并使自然的歷史(星光、河流、植物等)和人文的歷史(民風(fēng)、田疇、酒肆等)和諧地融為一體,而自然的歷史和人文的歷史時而平行、交疊,時而彌散、聚合,就像音樂里的二重唱或交響曲里交織穿插的第一、第二主題,二者幾乎達(dá)到水乳交融狀態(tài);又如子午的《隔水相望》,詩中的“農(nóng)歷”、“十二生肖”等,是發(fā)祥于中國、與中國人的農(nóng)耕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獨特民俗;他的《漢字建筑》里“門前,兩行直書的漢字(對聯(lián))”和“兩只蹲在門旁的石獅子”等,更是漢族特有的沿襲千年的民風(fēng)。這些特有的民風(fēng)、民俗及其相關(guān)意象,處處流露和凸現(xiàn)了民族歷史、文化所蘊(yùn)含的博大而永恒的精神……
三、詩體建設(shè)及對語言層面的不懈開掘
泛敘實派詩群是中國詩壇目前最活躍并最具實力的詩歌群體。他們在九十年代初以來的二十多年間,一直不懈地為促進(jìn)中國詩歌的繁榮和健康發(fā)展做出各自的努力。尤其是他們在對中國新詩的詩體建設(shè),以及對詩歌語言的探索和開拓方面,已取得了實質(zhì)性的成果。
1.對中國新詩詩體建設(shè)的實質(zhì)性貢獻(xiàn)
在當(dāng)代詩壇對中國新詩的詩體建設(shè)取得了不菲實績而又最具群體效應(yīng)的,無疑是泛敘實派的詩人族群。該詩派的陸健、子午、洪燭、田原、祁人、王明韻、閻志等均以不同的方式貢獻(xiàn)了各自的詩歌實驗及藝術(shù)智慧。首先,最為值得稱道的是陸健對中國新詩體裁的開拓、豐富及對新詩藝術(shù)形式的突破。
早在1992年9月,陸健的詩集《名城與門》在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問世后,筆者就曾指出:陸健創(chuàng)造了一種新的體裁:詩特寫(Poetry feature)。其后的《34份禮物》(2004年5月)、《非典時期的了了特特博士》(2003年6月)、《楓葉上的比爾》(2006年6月)、《田樓,田樓》(2006年10月)和《洛水之陽》(2007年4月)等詩集的藝術(shù)形式及其風(fēng)格則屬紀(jì)實詩(Documentary poetry)。毫不夸張地說,陸健的詩特寫和紀(jì)實詩系列創(chuàng)作在中國新詩史上均具有開創(chuàng)性及建設(shè)性意義。
詩特寫,是指以詩的形式而化用電影藝術(shù)中“特寫鏡頭”的表現(xiàn)手法來反映社會生活的一種新的體裁。其特點是抓住現(xiàn)實生活中的人物或事件的某一富有特征性部分,進(jìn)行集中、精細(xì)、突出的描繪和刻畫,具有高度的真實性和強(qiáng)烈的藝術(shù)感染力。這一詩歌體裁為陸健首創(chuàng)。紀(jì)實詩,則是指以詩的形式如實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或歷史中的真實人物與真實事件的體裁。由于詩歌自身的藝術(shù)特質(zhì)及語言特性,紀(jì)實詩與紀(jì)實小說、敘事詩、報告文學(xué)等又有著本質(zhì)的區(qū)別。筆者首次以“紀(jì)實詩”這一概念指稱陸健的紀(jì)實性系列詩歌作品(“詩特寫”和“紀(jì)實詩”這兩個概念及定義為筆者首創(chuàng))。
陸健肇始于《34份禮物》的紀(jì)實詩系列實驗,大致涵蓋了集約式寫作、主題詩集、生活原型紀(jì)實等范疇。陸健在詩中不但對詩歌題材進(jìn)行了幾近超越極限的開拓,而且在對人物行為和故事細(xì)節(jié)的關(guān)注、與表現(xiàn)對象互動的可能性方面獲得了非凡的成功。陸健的過人之處在于:拉近或消弭詩與生活的距離,讓生活彌漫著語言元素和詩意,讓詩意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也可以說,陸健的《34份禮物》、《非典時期的了了特特博士》、《楓葉上的比爾》和《田樓,田樓》4部實驗詩集,是“紀(jì)實詩系列實驗的四重奏”,同時也是兩個世紀(jì)之交以來中國詩壇的一個帶有標(biāo)記性意義的現(xiàn)象。
而“子午對新詩多種文本形式和多樣化語言風(fēng)格的實驗和突破,也是很值得稱道的”(秦一川語)。子午的詩歌系列作品涵蓋了自由體、新格律體、小節(jié)式、雙行段式、三行段式、四行段式(詩集中較多使用)……以至多行段式、對話體、獨白式、散文排列式、一氣呵成式、句讀式、短句式、長句式、跨行式、全標(biāo)點式、半標(biāo)點式、無標(biāo)點式、括號嵌入式、引號嵌入式、破折號嵌入式、隔行括號式、有韻體、無韻體、準(zhǔn)民歌體、準(zhǔn)歌詞體、口語體、仿歐式、仿古風(fēng)式、齊頭式、交錯式、準(zhǔn)頂針式、詩體小說式、微型詩劇式……和一些無法歸類的體式。在一本只有百來首詩的集子里,竟差不多囊括了新詩可能有(其中幾首的文本形式純屬獨創(chuàng))的所有體式,這在新詩史上是絕無僅有的!(見秦一川《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處》)
洪燭近十年來為中國長詩的嘔心瀝血的探索及創(chuàng)作實績是有目共睹的。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從2007年至2014年的7年間,他幾乎是以每年兩部的速度寫下了13-14部汪洋恣肆、異彩紛呈的長詩。按時間排列有:《西域》(共四百余首,長達(dá)八千多行,2007年5月寫畢),《青海青,黃河黃》(860行,2007年10月寫畢),《地震心靈史》(日記體長詩,1380行,2008年6月寫畢),《李白》(2600行,2007年12月寫畢),《成吉思汗》(400行,2008年9月寫畢),《清明節(jié)懷念母親》(2800行,2009年4月寫畢),《黃河——寫在南水北調(diào)工程采風(fēng)途中》(770行,2010年12月寫畢),《黛玉葬花》(1000行,2011年6月寫畢),《白蛇傳》(詩劇,2800行,2012年5月寫畢),《屈原》(又名《屈原的江河》,2500行,2012年寫畢),《陸游與唐琬》(330行,2013年3月寫畢),《杜甫》(330行,2013年8月寫畢),《倉央嘉措心史》(8300行,2014年9月寫畢)。
尤其是他長達(dá)八千多行、由四百余首詩歌所組成的龐大的“西域”現(xiàn)代交響長詩,在整體詩美風(fēng)格及藝術(shù)內(nèi)涵上體現(xiàn)了洪燭一以貫之沉雄古樸的總的詩歌精神坐標(biāo),同時也是當(dāng)代詩人自覺接續(xù)并融入中國唐宋詩美傳統(tǒng)的綜合工程的最好體現(xiàn)。實際上,西域的涵義甚為廣博,它包括人文、地理、歷史、文學(xué)、藝術(shù)、民族、風(fēng)俗……等范疇,方方面面,林林總總。詩人筆下異彩紛呈的“西域”,是構(gòu)成多元化世界格局的一個縮影。在這個地球上,你恐怕難以找出第二個像西域這樣多元文明共存的區(qū)域。這里曾使用過的語言文字多達(dá)數(shù)十種。由于絲綢之路這一偉大的紐帶,它成為中國、印度、波斯和希臘四大文明獨一無二的融合區(qū)(洪燭語)。
2.對中國新詩語言的深層開掘和突破
回顧現(xiàn)代漢語的歷史及中國新詩的發(fā)展史,自“五四”白話詩和二三十年代的現(xiàn)代詩,到七八十年代末的新詩潮運動,其詩歌語言、敘事形態(tài)及詩體都是進(jìn)化不徹底、不完善的,沒有實現(xiàn)與現(xiàn)代口語的完全協(xié)調(diào)一致。九十年代以降,中國新詩逐漸取得了與現(xiàn)代口語的協(xié)調(diào)一致(李麗中、謝冕、王家新等學(xué)者均持此說)。但中國新詩與現(xiàn)代漢語的現(xiàn)代化進(jìn)程很快就被大眾文化(含網(wǎng)絡(luò)詩歌)的勃興所中斷。網(wǎng)絡(luò)語言的泛濫導(dǎo)致了現(xiàn)代漢語與詩歌藝術(shù)的失范。正是網(wǎng)絡(luò)語言鋪天蓋地、來勢兇猛的沖擊,迫使中國新詩不得不又一次退回到語言的本體論層面原點——如語素、米尼姆(minimum,語言的最小量)、詞、語音、節(jié)奏(含頓、句讀)、語感……等,去重建詩歌的語言系統(tǒng)及其敘事方式。也許,這就是中國新詩在不到一個世紀(jì)的時段內(nèi)經(jīng)歷了一次又一次重大歷史性轉(zhuǎn)型的語言/文化宿命。為適應(yīng)這一新的話語秩序的轉(zhuǎn)型,《星星》詩刊和《詩刊》相繼于2002年下半年(8月后)將月刊改為半月刊。《星星》詩刊更是將“網(wǎng)絡(luò)原創(chuàng)、民間話語、品質(zhì)時代”,作為其下半月刊打造“中國網(wǎng)絡(luò)詩歌第一品牌”的宗旨。隨后,國內(nèi)的其他詩刊也相繼將月刊改為半月刊,雙月刊改為月刊。
最能體現(xiàn)一個詩人的綜合創(chuàng)作能力及語言實力的是對其母語的質(zhì)地、結(jié)構(gòu)和語素等層面的挖潛及突進(jìn)。語言哲學(xué)的奠基人、數(shù)理邏輯學(xué)家維特根斯坦有一句名言:“我的世界的邊界即是我的語言的邊界。”這恰好印證了語言能力是一個詩人創(chuàng)造力的最直接體現(xiàn)。美國詩人奧爾遜指出:“對于想嘗試的人,我奉勸他:走回這里來,到語言的元素和米尼姆這個地方來。這便是說,要在語言最不疏忽、最不合邏輯的情況下向語言進(jìn)攻……”③
鄭敏非常敏銳地指出:“后新詩潮出現(xiàn)的最大問題是語言問題。‘后’派所要表達(dá)的是后現(xiàn)代主義的觀念。簡單地說就是將事物和諧完整的外表擊碎,以顯露其不和諧的碎裂內(nèi)核。為了形式與內(nèi)容的統(tǒng)一,詩歌語言也必須呈現(xiàn)不和諧狀態(tài),但語言是先于個人而存在的社會、種族的共有財產(chǎn),而且是一個種族的意識的模式與造型者,它一旦被破壞,就不再有傳達(dá)和承載信息、意義的功能,這種語言的頑強(qiáng)獨立性使得詩人比音樂家、畫家更難于進(jìn)入創(chuàng)作的后現(xiàn)代主義。線條、平面、立體、顏色、音符都像零件可以任創(chuàng)作者組裝成所需要的繪畫、雕塑、音樂語言,以體現(xiàn)其意念。因此語言對于后現(xiàn)代主義詩人往往是一個陷阱,誰若想任意擺弄語言,必將受到懲罰。盡管抽象藝術(shù)可以表現(xiàn)碎片意識,變形的人與物,以語言來做這類后現(xiàn)代的試驗卻是很難成功的。”④
泛敘實派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新詩的語言進(jìn)行了語言學(xué)層面及詩學(xué)層面的實驗和開拓:
1.語詞質(zhì)地指標(biāo):具體、質(zhì)樸、簡潔、明快、鮮活、敞亮,充滿寫實的質(zhì)感、動感和層次感;
2.語素⑤結(jié)構(gòu)指標(biāo):強(qiáng)調(diào)節(jié)奏性、彈性、反差性、具象性和開放性,張揚(yáng)語感和詞的硬度、強(qiáng)度及穿透力;
3.語感特色指標(biāo):平實而新穎、簡單而豐富、寧靜而情感充盈,凸現(xiàn)立體、多姿多彩的效果;
4.詞象功能指標(biāo):言之有物、有象、有景、有情、有理、有意、有境,以形成及物性詞象摩擦、激活和物我互生、天人合一的心象運動,從而導(dǎo)致詩的藝術(shù)完形。
所謂語感(一稱“語言直覺”),是指語素和詞自身的色彩、情味、語音、節(jié)奏、語義、語氣,以及由語素和詞所構(gòu)成的詞間、句間的特定關(guān)系、結(jié)構(gòu)、語法、氛圍等(引自筆者的定義)。郭沫若曾說:“大凡一個作家或詩人總要有對于語言的敏感,這東西‘如水在口,冷暖自知’,實在也說不出個所以然。”苗時雨則把“語感”稱為“內(nèi)心視力”。他認(rèn)為語感是“詩歌寫作的基本能力。既是個性與風(fēng)格的基質(zhì),又是個性與風(fēng)格的展現(xiàn)”。
不用諱言,在九十年代中期至新世紀(jì)初這一特定的歷史時段,風(fēng)起云涌式的詩歌浪潮早已消隱,像第三代詩人那樣的流派“造山運動”也沒有了市場。這是一個完全憑個人實力寫作的時期(史稱“個人寫作”時段),它表面上的眾聲喧嘩和暗下里的布滿潛流現(xiàn)象也是很值得深思的。由于泛敘實派詩人的共同努力,他們對中國新詩語言建設(shè)的努力及其新的敘事方式的形成便顯得尤為難能可貴和更具史學(xué)意義。
歐陽江河說:“語境關(guān)注的是具體文本,當(dāng)它與我們對自身處境和命運的關(guān)注結(jié)合在一起時,就能形成一種新的語言策略,為我們的詩歌寫作帶來新的可能和至關(guān)重要的活力。”泛敘實詩派新的敘事方式的形成,一方面為中國新詩的語言建設(shè)提供了最有批評意義的個案,另一方面又在寫作實踐和探索中及時總結(jié)并上升為理論話語,其具有普適性和可操作性的詩歌元素及藝術(shù)語匯無疑又豐富了中國新詩美學(xué)的理論內(nèi)涵。
四、經(jīng)典意識的倡導(dǎo)和對傳統(tǒng)詩美精神的繼承
關(guān)于“經(jīng)典意識”的倡導(dǎo),筆者自2005年10月在第19屆世界詩人大會上呼吁當(dāng)代詩歌應(yīng)提倡一種經(jīng)典意識后,2006年12月10日,在中國詩歌學(xué)會“珠海·中國南方詩歌論壇”上,又宣讀了《守護(hù)靈魂與語言的家園》及《當(dāng)代詩歌應(yīng)提倡一種經(jīng)典意識》兩篇詩論(后收入詩論暨文學(xué)評論集《山水情懷與華夏文化精神》,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8年12月第1版)。接下來,筆者的一系列有關(guān)經(jīng)典意識、新敘事主義理論、泛敘實派詩歌的相關(guān)理論文章陸續(xù)在全國各重要刊物如《詩探索》、《中國作家》、《中國詩歌》、《詩歌月刊》、《世界詩人》、《詩林》、《上海詩人》、《西部新世紀(jì)文學(xué)》、《大昆侖》上接連發(fā)表,又在中國詩歌網(wǎng)、《世界詩人》網(wǎng)、《中國詩人》網(wǎng)、《詩歌月刊》網(wǎng)、影響力中國網(wǎng)、天涯論壇、中國知網(wǎng)、360個人圖書館網(wǎng)、龍源期刊網(wǎng)、詩生活網(wǎng)、中國作文網(wǎng)、百分網(wǎng)等數(shù)十家知名網(wǎng)站轉(zhuǎn)載或引用,并在全國數(shù)十家有影響的博客(包括中國十大知名博客中的兩家博客)轉(zhuǎn)載。可想而知,其在全國所產(chǎn)生的持續(xù)信息效應(yīng)及連鎖文化效應(yīng)是影響巨大的。這無疑對于在中國詩壇倡導(dǎo)經(jīng)典意識起到了相當(dāng)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泛敘實派詩人群體的詩歌作品專輯從2008年6月起,也接二連三地在全國各重要詩刊和文學(xué)期刊上推出。如《詩歌月刊》2008年6月號、《中國作家》2008年第11期、《詩歌月刊》2008年12月下半月刊、《詩歌月刊》2009年4月下半月刊、《西部新世紀(jì)文學(xué)》2009年4月下半月刊等都推出過,并配發(fā)子午的詩論《新敘事主義視野下的泛敘實詩派》。此外,該派的7位代表詩人也各自在全國各大報刊發(fā)表了大量優(yōu)秀詩歌作品。作為中國十大知名博客的洪燭博客、祁人博客也相繼推出了各自的詩歌力作,尤其是洪燭近年所寫的多部長詩在廣大網(wǎng)友中引起了持續(xù)而巨大的反響。應(yīng)該說,像泛敘實派詩人群體從詩歌理論到詩歌作品接連不斷地、大面積地在全國各大報刊及網(wǎng)站隆重推介,在中國詩歌史上實屬罕見。可想而知,這對泛敘實派的造勢和推波助瀾作用是尤為顯著的,其影響也是空前和深廣的。
鄭敏在《新詩百年探索與后新詩潮》一文中指出:“我們可以斷言,二十一世紀(jì)中國新詩的能否存活就看我們能否意識到自身傳統(tǒng)的復(fù)活與進(jìn)入現(xiàn)代,與吸收外來因素之間的本末關(guān)系。”“沒有傳統(tǒng)何談創(chuàng)新?沒有傳統(tǒng)作為立身之地,創(chuàng)新只能是全盤西化,作為西方文化體系中的一個加盟者,這顯然與我們?nèi)該碛凶约赫Z言文化的古老國家的命運不相稱。所以在新世紀(jì)開始的前夕,中國當(dāng)代新詩一個首要的、關(guān)系到自身存亡的任務(wù)就是重新尋找自己的詩歌傳統(tǒng),激活它的心跳,挖掘出它久被塵封土埋的泉眼。讀古典文史哲及詩詞詩論,想現(xiàn)代問題,使一息尚存的古典詩論進(jìn)入當(dāng)代的空間,貢獻(xiàn)出它的智慧,協(xié)同解決新詩面對的問題。”⑥
對于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shù)精神傳承,在泛敘實派的詩人族群中,洪燭和陸健尤為喜歡以一種幽默的方式楔入傳統(tǒng)。洪燭的幽默無疑是他對語言和人生現(xiàn)實大徹大悟式的靈光閃現(xiàn)以及詩美立場的升華。透過《屈原》、《李白》和《杜甫》三部長詩,洪燭的幽默風(fēng)格幾已發(fā)揮到了極致。如在長詩《李白》中,洪燭通過對李白的盡情調(diào)侃而獲得了全身心的快感:“李白在長安城下崗了/才去走江湖,成為一個體制外的詩人”,“他沒見過比楊貴妃更美的女人/他還是比白居易強(qiáng):白居易見到琵琶女/就驚艷了/白居易沒親眼見到楊貴妃/卻寫出《長恨歌》,真有兩下子……/李白走出大明宮,丟了魂似的/寫不出更多的贊美詩:美,離得越近/越使人啞口無言”。
陸健寫畢于2012年9月的長詩《一位美輪美奐的小詩人之歌》堪稱中國當(dāng)代的經(jīng)典長詩。他將自己對中國文化及古典詩歌傳統(tǒng)的精神傳承,形象而傳神地寫在長詩的第一章里:“我的主食是面粉、稻谷、玉米/儒家和道家的筆墨。通過翻譯/品嘗面包和西方文化的滋味//我是農(nóng)耕文明的產(chǎn)物,被機(jī)器/快速裹挾,一頭扎進(jìn)計算機(jī)里/小心翼翼,護(hù)住自己的軟肋”。隨即,陸健考之有據(jù)地指出當(dāng)代詩歌“語言肌理”及“骨質(zhì)結(jié)構(gòu)”的病理所在:“詩人應(yīng)該向字、詞的皮癬負(fù)責(zé)/語言的脾胃不適,它攝取的營養(yǎng)單一/以致骨質(zhì)疏松,體質(zhì)時常虛弱”(長詩第十一章)。
陸健在這部長詩中,一方面將《神曲》三部曲(全詩共14233行)的鴻篇巨制結(jié)構(gòu)微縮成以26個英文字母標(biāo)識的章節(jié)形式(全詩702行),另一方面又在詩歌的內(nèi)容及思想題旨上將艾略特的“荒原”意識貫穿到底。詩的每一章均由“主題詩”(或稱上闋)和“對題詩”(或稱下闋)兩部分組成,其中作為大寫的“主題詩”共九行三小節(jié),而作為復(fù)調(diào)形式的小寫“對題詩”則是十八行六小節(jié);同時,“對題詩”所帶出的主題也可視為對“主題詩”的一種藝術(shù)延伸、變奏、呈示、發(fā)展和再現(xiàn)。這由一奇(九行)、一偶(十八行)所組成的獨特的詩行結(jié)構(gòu),無疑是對中國道家思想“一陰一陽”格局的借鑒及化用。
房偉和周寶紅經(jīng)對子午的詩歌創(chuàng)作及詩歌理論的考察、研究,認(rèn)為子午一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將中國古典詩歌的藝術(shù)精神向現(xiàn)代詩的融入和轉(zhuǎn)化,并取得了可資借鑒的成效。子午的《〈詩經(jīng)〉——中國詩歌敘事因素的濫觴》一文,將敘事性看作文學(xué)的基本特性及本質(zhì)要素,“他從被奉為中國詩歌及文化元典的《詩經(jīng)》的敘事因素入手,對中國當(dāng)代新詩潮歷史語境發(fā)生的深刻變化尤其是敘事話語的普遍使用進(jìn)行追本溯源,分析詳盡生動,系統(tǒng)深入,實屬作者二十年磨礪的心得。子午以前瞻性的眼光對‘言志/敘事’這個中國詩歌永恒而常新的話題進(jìn)行重新審視,從古典詩歌的文化資源中汲取營養(yǎng)和創(chuàng)作源”。子午和泛敘實派詩人群體的總體努力及其藝術(shù)實踐,為中國當(dāng)代新詩如何繼承傳統(tǒng),如何在詩體建設(shè)及語言結(jié)構(gòu)層面進(jìn)行有益的探索、建設(shè),提供了成功的經(jīng)驗。
結(jié)語
“孤帆遠(yuǎn)影碧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1999年4月中旬的“盤峰論爭”,使詩壇一下子出現(xiàn)了持續(xù)的失重暈眩,中心分崩離析,秩序土崩瓦解。沉寂了15年之久的詩壇似乎一時還沒有從那個“離心反應(yīng)”的混亂和紛爭中完全清醒過來。在此風(fēng)云際會的特定歷史時段,以泛敘實派為代表的實力詩人族群及時調(diào)整了自己的藝術(shù)思路及語言策略,應(yīng)天時、承地利、順人和地為中國新詩的薪火相傳與繁榮發(fā)展做出了值得稱道的努力及貢獻(xiàn)。
回首當(dāng)年,“五四”前夕的1914年1月,胡適創(chuàng)作了第一首白話詩《大雪放歌和叔永》,到今天,中國新詩已經(jīng)走過了風(fēng)起云涌、驚濤拍岸的100個年頭。雖然幾經(jīng)戰(zhàn)亂和救亡,幾經(jīng)沉浮而峰回路轉(zhuǎn),“文革”焚書,精英蒙冤,傳統(tǒng)文化幾度斷裂,所幸泱泱詩國的血脈至今仍然奔騰不息。如果說,泛敘實派在“新敘事時期”作為一支詩歌勁旅讓人猛然眼前一亮,而精神為之一振,那么也許這正是歷史賦予他們的文化責(zé)任和命運。
借此,在中國新詩百年華誕之際,謹(jǐn)以李清照詩《題八詠樓》作結(jié):
千古風(fēng)流八詠樓,江山留與后人愁。
水通南國三千里,氣壓江城十四州。
①此文原題《新敘事主義詩歌芻議》,原載2007年第1輯《詩探索》理論卷。同年11月,筆者將此文修改后題為《新敘事主義詩歌宣言》,參加2007年“中國詩歌90年紀(jì)念”太原詩歌論壇,并獲優(yōu)秀論文獎。后以《新敘事主義詩歌現(xiàn)象及其提出》為題,刊于2008年第5期《上海詩歌》。收入拙著《山水情懷與華夏文化精神》時,題目仍為《新敘事主義詩歌宣言》。
②為方便陳述和易于記憶,筆者將經(jīng)典意識的涵義緊縮為5句話(或要點):1.思想的前驅(qū)性質(zhì);2.對主流和時尚的超越;3.不可重復(fù)性特質(zhì);4.厚重的文化容量;5.新的藝術(shù)及文化源頭。誠然,這里所講的只是一種經(jīng)典意識——亦即體現(xiàn)在詩人創(chuàng)作活動中的一種主導(dǎo)思想,而非經(jīng)典性文藝作品的標(biāo)準(zhǔn)。其后,此文收入筆者的詩論暨文學(xué)評論集《山水情懷與華夏文化精神》。
③引自奧爾遜《投射詩》,見《詩人談詩——二十世紀(jì)中期美國詩論》第219頁,三聯(lián)書店1989年8月第1版。
④⑥見鄭敏《新詩百年探索與后新詩潮》,原載《文學(xué)評論》1998年第4期。
⑤語素,舊稱詞素,是指最小的語法單位,亦即構(gòu)成一個詞的最基本的語言元素。最大的語法單位是句子,比句子小的語法單位依次是短語、詞、語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