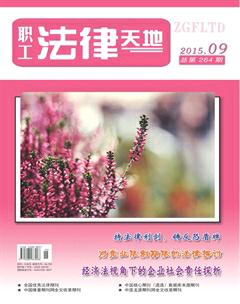論英美法系中注意義務的成立標準及對我國的啟示
摘 要:注意義務是指行為人應當有合理的注意而防范對他人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的義務,注意義務成立是過失侵權成立重要決定因素。英美法中,隨著注意義務理論不斷發展,逐漸誕生了“可預見性”、“近鄰性”、“公共政策考量”三重標準,共同構成了判斷注意義務成立的重要規則,這三重標準對于我國司法實踐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注意義務;侵權;可預見性;近鄰性;公共政策考量
一、英美法系中注意義務的概念及演進
在英美法系,注意義務在侵權責任之中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注意義務是過失侵權的核心,這一點無可非議。對于注意義務的概念,按《牛津法律大辭典》的解釋,是指行為人應當有合理的注意而防范對他人的人身和財產造成損害的義務。雖然是否存在注意義務是是否承擔過失侵權責任的必要條件,但是這一個十分抽象的概念,如何確定注意義務的界限成為許多法官面臨的難題。
注意義務理論源于英國。20世紀以前,英國法院對于原告是否應當承擔注意義務總是根據經驗認定,并沒有一個明確的指導原則。自1932年“唐納格布訴斯蒂文森”案之后,注意義務才逐漸實現理論化。英國上議院通過判例形式確立了一系列認定注意義務是否成立的標準,這些標準已為英美法系國家所普遍認同。
(一)注意義務理論的確立——可預見性
可預見性是由英國大法官阿特金在1932年的著名案例“唐納格布訴斯蒂文森”一案中確立的。原告唐納格布女士與朋友來到一家咖啡館并點了一瓶“斯蒂文森”牌姜啤酒。在她快喝完一整瓶姜啤酒時,她突然發現這個不透明酒瓶中竟然有一只腐爛的蝸牛,頓時感到非常震驚和不適。于是唐納格布女士起訴了“斯蒂文森”公司,訴稱被告在生產中沒有盡到合理注意義務,要求被告承擔相應的責任。
英國上議院最終認為被告對原告負有注意義務,從而支持了唐納格布女士的訴訟請求。而此判例就是著名的“可預見性理論”,即:一個人在他應該合理的預見發生的可能性但并沒有盡到合理注意的時候,他就負有相應的注意義務。[1]可預見性被認為是判斷注意義務的最基礎標準。
(二)對可預見性的擴展——近鄰性
近鄰性又稱近因性或鄰居法則,這一概念首先由Lord Esher在1887年提出,后阿特金大法官在“唐納格布訴斯蒂文森”案中將近鄰性這一概念援引并進一步做出詳細解釋。
近鄰性與可預見性是相輔相成的。在“唐納格布訴斯蒂文森”一案中,阿特金大法官在判決的最后這樣寫道:“你應當愛護你的鄰居,而不應當損害你的鄰居。如果你能合理地預見可能會損害你的鄰居,那么你就必須采取合理的注意去避免某種作為或不作為”[2]按照字面意思來理解,近鄰性就是指行為人與受其行為影響的人具有相當緊密的關系。
在個案中,可預見性所能調整的范圍往往難以界定,而近鄰性可以約束和控制可預見性,防止行為人承擔的責任被無限擴大,從而避免了不公正判決。
(三)注意義務對社會公共利益的回應——公共政策考量
但凡訴訟,法官判決前,不僅要考慮案件本身的事實,更要考慮今后發生同類案件的影響。對案件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進行評估與論斷,就是所謂的“公共政策考量”,通過公共政策考量,法官可以可避免某些案件出現法院本身和社會公眾都不愿看到的結果。“卡帕羅工業公司訴迪克曼”案中,被告因審計紕漏而向一家虧損公司出具了不實審計報告,導致原告基于信賴審計報告而與該公司交易造成經濟損失。但英國上議院對此不予支持,原因在于如果要求被告對公司的每一個股東或債權人都負有注意義務,無疑會形成先例,日后勢必造成濫訴現象。因此上議院認為,被告對原告不負有注意義務。
在這一系列案件中,依次誕生了“可預見性”、“近鄰性”和“公共政策考量”三種原則,這套普適性體系對我國是極具借鑒意義的。
二、英美法注意義務成立標準對我國司法實踐的啟示
案例:2014年7月25日,蘭某、韋某、蒙某得知藍某曾背地里說她們的壞話,因而結伴前往藍某家中找藍某理論。雙方互相進行言語攻擊。后藍某因想不通喝下殺蟲劑,搶救無效死亡。死者家屬認為三被告對藍某的辱罵是導致藍某死亡的主要原因,請求法院依法判決三被告賠償經濟損失。本案主審法官認為三被告對藍某負有注意義務,判決三被告承擔40%的賠償責任。[3]
我國《侵權責任法》并沒有明確注意義務的概念,在一般類侵權案件,被告對行為人是否有注意義務全憑法官自己決斷。因此在該案例中,主審法官認為有三名被告應當對藍某存在注意義務,于是判決應當承擔賠償責任。本文認為,正如案例所體現的,我國司法實踐中,由于法律對注意義務并無明確判斷標準,全憑法官自由裁量,過于隨意。
如前文所述,在英美法中,確定注意義務是否成立遵循“可預見性”、“近鄰性”和“公共政策考量”三重標準,我國法官在一般侵權中完全可以借鑒這三重標準來確定是否存在注意義務。
首先,按照可預見性原則,一個人在他應該合理的預見發生的可能性但并沒有盡到合理注意的時候,他就負有相應的注意義務。三名被告對藍某的自殺是否具有合理的預見性?顯然是不可能預見的,因為與藍某處于同一情形下的人,不會因為被告的幾句謾罵和肢體沖突就服毒自殺,因而三名被告對于藍某的自殺顯然不可預見。
其次,按照近鄰性原則,原被告之間應存在充分的密切聯系。要確認兩者的近鄰關系比較困難,需要綜合衡量。本案中,藍某的自殺雖然是受三名被告的謾罵行為影響,但是并非三名被告直接造成的,而是自己想不開,所以三名被告與原告是否具有近鄰性很難判斷,只能結合可預見性與公共政策考量來綜合考慮。
最后,按照公共政策考量,注意義務是否成立需要圍繞原被告之外的將來可能受案件影響的社會公眾進行考察。該案件已是一般侵權責任范圍的擴張,三名被告擔責將會給公眾一個信號:凡是自殺者的近親屬都可以到法院起訴可能是致自殺的那個人,從而尋求高額的精神損害賠償,這顯然通不過公共政策考量這一關。綜上所述,綜合這三重標準考慮,法院應當對原告的訴訟請求予以駁回。
參考文獻:
[1]彼得·凱恩著,王仰光等譯:《阿蒂亞論事故、賠償及法律》,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69頁。
[2]錢泳宏:“‘不朽的蝸牛――多諾休訴斯蒂文森案述評”, 河南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8年10月。
[3]案件來源:http://www.edu1488.com/article/2014-12/25133457.shtml
作者簡介:
潘晨(1991~),男,重慶,西南大學法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民商法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