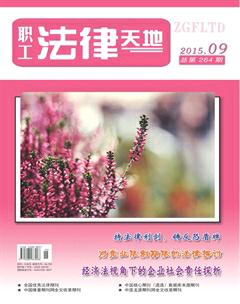論特殊自首的成立條件
李宏武
摘 要:特殊自首是我國(guó)自首制度中的難點(diǎn)問(wèn)題,正確認(rèn)定特殊自首既有力于打擊刑事犯罪,又能夠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權(quán)利。本文從我國(guó)刑法典關(guān)于自首制度的具體條文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出發(fā),結(jié)合理論正義及辦案實(shí)踐,對(duì)特殊自首的認(rèn)定進(jìn)行了深入闡述。
關(guān)鍵詞:特殊自首;強(qiáng)制措施;服刑;其他犯罪
特殊自首,又稱準(zhǔn)自首。根據(jù)現(xiàn)行刑法典第67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是指被采取強(qiáng)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實(shí)供述司法機(jī)關(guān)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行為。最高人民法院《解釋》第2條、第4條,均對(duì)特殊自首的成立作出了規(guī)定。在實(shí)踐中,依據(jù)上述規(guī)定,認(rèn)定特殊自首,應(yīng)具備以下三個(gè)條件:
一、主體要件
根據(jù)《刑法》規(guī)定,特殊自首的適用僅限于三種人,即被采取強(qiáng)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
1.被采取強(qiáng)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
在司法實(shí)踐中,對(duì)于強(qiáng)制措施的范圍存有較大爭(zhēng)議,對(duì)被采取行政拘留、勞動(dòng)教養(yǎng)或司法拘留等非刑事強(qiáng)制措施的人員,主動(dòng)供述自己所犯且尚未被司法機(jī)關(guān)掌握的罪行的,是否應(yīng)認(rèn)定為特殊自首?同時(shí),對(duì)于被取保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等強(qiáng)制措施的犯罪人,但同時(shí)其人身自由又沒(méi)有被完全限制的,是否應(yīng)認(rèn)定為特殊自首?對(duì)此,學(xué)術(shù)界主要有三種不同觀點(diǎn)。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上述情形實(shí)際上屬于一般自首的范疇,形式上也符合一般自首的條件。“特殊自首與一般自首的根本區(qū)別在于,在特殊自首的情況下,由于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被剝奪,無(wú)法實(shí)施自動(dòng)投案的行為,因此法律規(guī)定以自首論”①有的學(xué)者則認(rèn)為,應(yīng)當(dāng)對(duì)準(zhǔn)自首的主體作擴(kuò)張的司法解釋或立法解釋,將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或勞動(dòng)教養(yǎng)等人身自由受到依法剝奪的人員包括在準(zhǔn)自首的主體范圍內(nèi),認(rèn)為這種解釋是有利于犯罪人的,都屬于“以自首論”的主體范圍。②有的學(xué)者認(rèn)為,包括被采取剝奪人身自由強(qiáng)制措施的處于“在押狀態(tài)”的犯罪人,還有被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強(qiáng)制措施的出于“非在押狀態(tài)”的犯罪人,都屬于準(zhǔn)自首的主體范圍,都可以認(rèn)定為準(zhǔn)自首。③
筆者同意第一種觀點(diǎn),認(rèn)為只有人身自由被剝奪,無(wú)法實(shí)施自動(dòng)投案的犯罪人,才屬于“以自首論”的主體。首先,筆者認(rèn)為被行政拘留、司法拘留或勞動(dòng)教養(yǎng)等人身自由受到依法剝奪的人員,不應(yīng)當(dāng)包括在準(zhǔn)自首的主體范圍內(nèi),原因有三:第一、我國(guó)現(xiàn)行《刑事訴訟法》對(duì)強(qiáng)制措施的范圍作了明確規(guī)定,僅包括拘傳、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拘留、逮捕五種強(qiáng)制措施,在理解《刑法》第67條第2款中表述的“強(qiáng)制措施”一詞時(shí),應(yīng)當(dāng)與《刑事訴訟法》中的表述相一致。第二、被采取行政拘留或勞動(dòng)教養(yǎng)的犯罪人,在行政拘留、教養(yǎng)期間,向公安機(jī)關(guān)如實(shí)供述司法機(jī)關(guān)尚未發(fā)覺(jué)的犯罪事實(shí)的,應(yīng)該屬于“罪行尚未被司法機(jī)關(guān)發(fā)覺(jué),僅因形跡可疑被有關(guān)組織或司法機(jī)關(guān)盤問(wèn)、教育后,主動(dòng)交代自己罪行”的情形,對(duì)此,應(yīng)當(dāng)視為自動(dòng)投案。④第三、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意見(jiàn)》中明確規(guī)定:因特定違法行為被采取勞動(dòng)教養(yǎng)、行政拘留、司法拘留、強(qiáng)制隔離戒毒等行政、司法強(qiáng)制措施期間,主動(dòng)向執(zhí)行機(jī)關(guān)交代尚未被掌握的犯罪行為的,對(duì)此也應(yīng)當(dāng)視為自動(dòng)投案。這一問(wèn)題事實(shí)上已經(jīng)得到了妥善解決。
其次,筆者認(rèn)為,被采取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兩種強(qiáng)制措施的犯罪人,如實(shí)供述其犯罪事實(shí)的,不宜認(rèn)定為特殊自首。從設(shè)立特殊自首的目的來(lái)看,是為了解決已被羈押、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人無(wú)法主動(dòng)投案,但其到案后又能主動(dòng)如實(shí)供述司法機(jī)關(guān)尚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的,由于其具有自首的本質(zhì)特征,故此,我國(guó)現(xiàn)行刑法典才規(guī)定了特殊自首制度,將不具備主動(dòng)投案條件,但仍具有自首的本質(zhì)特征的行為“以自首論”。而對(duì)于處于取保候?qū)彙⒈O(jiān)視居住期間的犯罪嫌疑人,僅僅處于限制人身自由狀態(tài),其完全具備主動(dòng)投案的條件,且該類主動(dòng)投案與其他犯罪分子的自動(dòng)投案在本質(zhì)上并無(wú)明顯差別,故此不宜將此類自首認(rèn)定為特殊自首。
2.正在服刑的罪犯
對(duì)于“正在服刑的罪犯”,有廣義和狹義兩種理解。從狹義上來(lái)講,“服刑”是指在看守所、拘留所、監(jiān)獄等羈押場(chǎng)所執(zhí)行拘役、有期徒刑、無(wú)期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等刑罰的罪犯。⑤從廣義上來(lái)講,“正在服刑的罪犯”不僅包括上述罪犯,還應(yīng)當(dāng)包括正在執(zhí)行管制、剝奪政治權(quán)利等附加刑及正處于緩刑考驗(yàn)期、假釋考驗(yàn)期、監(jiān)外執(zhí)行的罪犯。⑥最高人民法院在《解釋》中將“正在服刑的罪犯”解釋為“已宣判”,事實(shí)上已經(jīng)將被處以緩刑、假釋、管制以及被適用附加刑的罪犯包括在特殊自首的主體范圍之內(nèi),筆者認(rèn)為,該解釋值得商榷。
有學(xué)者認(rèn)為,一般自首與準(zhǔn)自首在此問(wèn)題上的根本區(qū)別在于犯罪人是否具有人身自由, 一般自首的主體能夠自由支配其身體,因此可以主動(dòng)前往司法機(jī)關(guān)投案自首;而特殊自首的主體是被司法機(jī)關(guān)采取了相應(yīng)強(qiáng)制措施并限制其人身自由的犯罪人,由于無(wú)法主動(dòng)前往司法機(jī)關(guān)自首,而是在司法機(jī)關(guān)的控制之下供述其本人還未被掌握的其他犯罪事實(shí)。⑦筆者完全同意此種觀點(diǎn),故此認(rèn)為,正在被執(zhí)行管制、剝奪政治權(quán)利等附加刑及正處于緩刑考驗(yàn)期、假釋考驗(yàn)期、監(jiān)外執(zhí)行的罪犯,由于其人自身自并沒(méi)有被完全限制,不同于被收監(jiān)執(zhí)行的罪犯,他們具備“自動(dòng)投案”條件,故此類罪犯在主動(dòng)向司法機(jī)關(guān)如實(shí)供述其尚未被司法機(jī)關(guān)掌握的其他罪行的,應(yīng)該認(rèn)定為一般自首。
二、行為要件
依據(jù)我國(guó)現(xiàn)行《刑法》第67條第2款的規(guī)定,特殊自首的行為要件是“如實(shí)供述司法機(jī)關(guān)還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對(duì)此,筆者認(rèn)為須從以下三個(gè)方面理解:
1.如何理解“司法機(jī)關(guān)”
筆者以為,理論上將“司法機(jī)關(guān)”擴(kuò)展為全國(guó)所有的司法機(jī)關(guān)的觀點(diǎn)過(guò)于寬泛,沒(méi)有考慮到我國(guó)幅員遼闊的現(xiàn)實(shí)國(guó)情,顯然不利于司法機(jī)關(guān)認(rèn)定自首,對(duì)犯罪嫌疑人也不公平。將“司法機(jī)關(guān)”僅限定于直接辦案機(jī)關(guān)的觀點(diǎn)也不合理,對(duì)犯罪嫌疑人顯得太過(guò)寬縱,不利于打擊犯罪。同時(shí),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導(dǎo)性意見(jiàn)雖然規(guī)范的比較具體,但考慮到司法機(jī)關(guān)存在著案件數(shù)量多、時(shí)間短等種種困難,在司法實(shí)踐中并不好把握。故此,筆者認(rèn)為,對(duì)“司法機(jī)關(guān)”的掌握完全可以依照上網(wǎng)通緝的情況來(lái)分析,分為兩種情況:第一,犯罪人沒(méi)有上網(wǎng)通緝的,或者雖被通緝,但被通緝的事實(shí)與其供述的所犯余罪并非同一事實(shí)的,“司法機(jī)關(guān)”即為辦案機(jī)關(guān);第二,犯罪人已因其供述的此項(xiàng)事實(shí)被上網(wǎng)通緝的,“司法機(jī)關(guān)”也應(yīng)包括對(duì)該犯罪嫌疑人上網(wǎng)通緝的辦案機(jī)關(guān)。
2.如何理解“還未掌握”
最高人民法院2010《意見(jiàn)》中進(jìn)一步明確了“還未掌握”的范圍,一般應(yīng)以通緝令發(fā)布的范圍為標(biāo)準(zhǔn),如果辦案的司法機(jī)關(guān)不在該范圍之內(nèi),則應(yīng)認(rèn)定為“還未掌握”,如果犯罪人所犯余罪已經(jīng)在全國(guó)公安信息網(wǎng)絡(luò)在逃人員信息數(shù)據(jù)庫(kù)內(nèi),則應(yīng)視為已掌握。筆者認(rèn)為,“還未掌握”應(yīng)當(dāng)具體案件具體分析,應(yīng)以具體辦案單位的實(shí)際掌握為準(zhǔn)。如該辦案單位在犯罪人主動(dòng)交代其他罪行之前,已通過(guò)網(wǎng)上追逃系統(tǒng)、通緝令或者相關(guān)司法機(jī)關(guān)的信息溝通掌握了該罪行,就應(yīng)該視為已經(jīng)掌握,反之,則應(yīng)該視為“還未掌握”。
3.如何理解“其他罪行”
關(guān)于同種罪行、非同種罪行的認(rèn)定標(biāo)準(zhǔn),在我國(guó)的刑法理論和司法實(shí)踐中,通常以犯罪人的數(shù)個(gè)罪行符合的數(shù)個(gè)基本犯罪構(gòu)成是否一致,作為數(shù)罪是屬于同種罪行還是屬于不同種罪行的標(biāo)準(zhǔn)。如果屬于數(shù)個(gè)性質(zhì)相同的基本犯罪構(gòu)成的,則說(shuō)明行為人所犯數(shù)罪屬于同種罪行,反之則屬于不同種罪行。⑧犯罪人的犯罪事實(shí)所符合的數(shù)個(gè)犯罪構(gòu)成的性質(zhì)是否一致,表現(xiàn)在法律特征上,就是犯罪人所犯數(shù)罪所觸犯的罪名是否一致。觸犯相同罪名的,意味著數(shù)罪是同種罪行,反之,則說(shuō)明數(shù)罪是不同種罪行。⑨筆者以為,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中,將“其他罪行”規(guī)定為“與司法機(jī)關(guān)已掌握的或者判決確定的罪行屬不同種的罪行”,主要出于以下幾個(gè)方面的考慮:第一、體現(xiàn)了特殊自首的嚴(yán)苛:按照我國(guó)刑法理論中關(guān)于數(shù)罪并罰的規(guī)定,同種數(shù)罪一般不并罰,如果將“同種罪行”也包括在“其他罪行”當(dāng)中,在數(shù)個(gè)行為不能按一罪處理的情況下,自首效力是及于部分還是全部則很難界定。如果及于全部的話,那么特殊自首則只要求供述自己的罪行即可,而一般自首中不僅需要主動(dòng)投案,也要求如實(shí)供述自己的罪行,一般自首的自動(dòng)投案則完全喪失了存在的必要。第二、方便司法實(shí)踐中操作:如果“其他罪行”包括“同種罪行”,犯罪人在供述出同種罪行或是不同種罪行的情況下如何認(rèn)定自首,在司法操作及具體量刑時(shí)會(huì)變得更加困難,且容易導(dǎo)致司法工作人員得出不同的結(jié)果。第三、兼顧了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的原則:根據(jù)司法解釋的規(guī)定,對(duì)于供述同種罪行的,雖不予以認(rèn)定自首,但在量刑時(shí)酌情予以從輕處罰,體現(xiàn)了對(duì)犯罪人的公正處理,兼顧了罪責(zé)刑相適應(yīng)原則。
注釋:
①蘇惠漁主編《犯罪與刑罰理論專題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15頁(yè)。
②陳錦新:《對(duì)“以自首論”的理解和適用》,載《中國(guó)律師》2003年第5期。
③陳興良著:《刑法適用總論》(下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80 頁(yè)。
④參見(jiàn)《行政拘留期間交代公安機(jī)關(guān)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shí)的行為能夠認(rèn)定為自首》,載《刑事審判參考》2003年第4集。
⑤參加周加海著:《自首制度研究》,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yè)。
⑥參加周加海著:《自首制度研究》,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3年版,第111頁(yè)。
⑦參見(jiàn)陳興良.刑法適用總論.法律出版社.1999 年.第 481 頁(yè)。
⑧參見(jiàn)周家海著:《自首制度研究》,中國(guó)人民公安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頁(yè)。
⑨參見(jiàn)趙秉志主編:《刑法新教程》,中國(guó)人民大學(xué)出版社2001年版,第290-291頁(y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