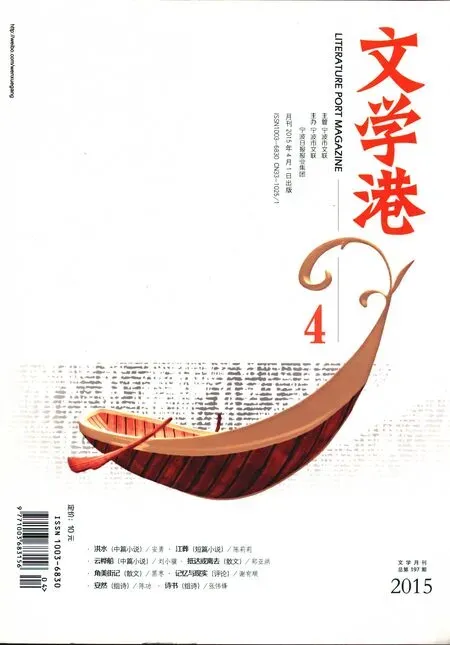記憶與現實
——簡評石一楓的《放聲大哭》
謝有順
記憶與現實
——簡評石一楓的《放聲大哭》
謝有順
石一楓的《放聲大哭》是一個精巧的短篇。一次帶有戲謔性質的講述,一個童年的記憶斷片,過去和現在的不斷閃回,越來越迫近的心理情緒,這些都深得短篇小說的意蘊。短篇寫的就是生活或內心的橫斷面,往往只是幾個簡單的人物,一些場景,作家看準了某處節點,果斷地一刀切下去,露出一些令人難忘的細部,凝視它,描摹它,這就能寫出一個好的短篇小說來。
《放聲大哭》正是如此。一個六歲孩子迷路后,被一個阿姨帶回家,從帶有惡作劇般的玩金魚,到這個孩子最終堅定地向往這個阿姨溫暖的胸脯,并渴望在她懷里放聲大哭,這個過程的轉折,石一楓把握得精微、有趣。同時,這個孩子內心蘇醒的一些方面,也漸漸呈現在我們面前,它是一些情緒,是一個生命原始的欲望,也是人類朝向母體的一個童年儀式。最終,石一楓還把它寫成了當下自我的一個鏡像——六歲的孩子,有著樸質的生命直覺,他需要的就是一次安撫、一個真實的懷抱,那些有暖意的話語和動作,喚醒的是一個人內心柔軟的部分,“放聲大哭”看似只是一次抒懷,卻已成了“我”成年之后難以再有的品質。“我”長大、成熟,越來越嫻熟于人事,知道如何討好一個人,也知道如何隱藏自己,唯獨無法再有“放聲大哭”的勇氣和心情,或者說,世間再無什么事物值得我感動,令我垂淚。人類從一個溫暖的母體出發,找到了自我,卻可能失去了一種最為單純、珍貴的生命感覺,我們帶著面具,失去了愛的能力、感受溫暖的能力,這其實是一種存在的悲劇——“我早已精疲力竭,心里清清楚楚,往事不可重現”。這只是一次童年生活的回憶么?其實更像是對初始生命的緬懷,對失去了愛與抒情能力的人生的祭奠。
盡管作者用了戲謔的口吻,但并不能掩飾其內在的對生命的敬虔之情。童年的一次偶然經歷,影響著一生的“我”,那也許是“我”第一次朦朧的性意識的覺醒,但這種意識里,夾雜著一種愛與溫暖。今天,“我”擁有性,但“愛情有一夜之間就消失的惡習”,我如何留住內心那點愛意?如何找到那種童年對溫暖懷抱的依戀而有的滿足?或許,人生的幸福就在于人有回憶,而現實總是太堅硬,太破敗,哪怕“等待著第一聲忘情大哭能夠如期到來”這點渺小的愿望,最終“我”也發現,“已經沒有這種能力了”。我只能活在回憶中,以回憶抵抗現實,這是我的幸福,也是我的悲哀。
或許還值得提及的是,《放聲大哭》有一種敘事口吻,它不僅用了以現在回訪過去的講述方式,以獲得一種超然回望的視點,更是通過孩子對金魚的殘忍與孩子對一個溫暖懷抱的向往的對照,展示出人性的復雜,或者說,后者是對前者的救贖。而小說有意模糊那個阿姨的面影,“我”無論如何也回憶不起她長什么樣子,由此也揭示出,對于孩子這樣一個初始生命而言,是誰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已無法在現實中找回這種感覺,他失去的不是一個阿姨,而是人類給出溫暖的能力,以及他能感受溫暖、放聲大哭的能力。
正因為有了這種情懷,《放聲大哭》才有了自己的敘事腔調,而是否有自己的敘事口氣、敘事腔調,是決定一個作家有沒有風格化的重要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