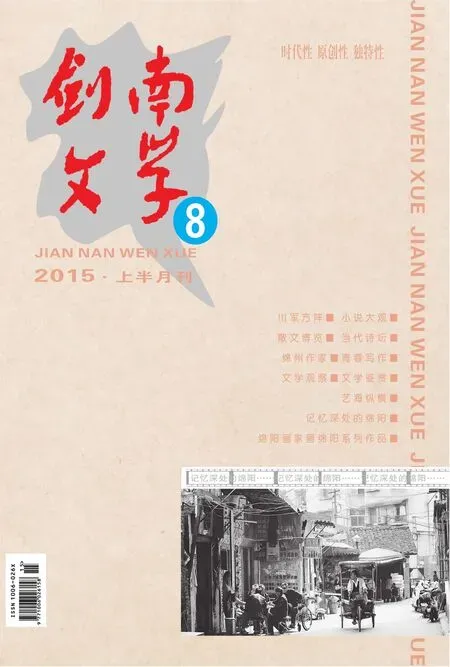悲劇主體的自身角色沖突
——以《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亞》為例
■白玉雪
悲劇主體的自身角色沖突
——以《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亞》為例
■白玉雪
在悲劇的創作過程中,作者對于悲劇主體的角色塑造是拉動整個故事向前發展的動力之一。對于悲劇主體來說,悲劇價值是其行為構成悲劇且震撼觀者的內涵,主體所承擔的多重角色以及角色間的矛盾是對悲劇具體故事情節的執行。本文從《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亞》兩部悲劇中的俄狄浦斯和美狄亞的形象對此進行探究和分析。
起源于祭祀酒神歌舞的古希臘悲劇從誕生起,就以其極富魅力的藝術特點和風格震撼著觀者。它跨越了幾千年的歷史流傳至今,作者對于悲劇價值和悲劇主體的設計,使得故事的內容及釋放出強大的力量是它們未被人們遺忘的重要內因之一;而從某種角度上講,悲劇主體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及角色間的各種沖突,即是在具體實踐悲劇價值與主體的構建模式,使得精彩的悲劇得以在藝術上表現出驚心動魄的效果。
一、悲劇中價值與主體的構建
如果要打造亦或是評價一場悲劇,悲劇價值是一部悲劇最核心也是最富崇高、表現力的地方。若是忽略、輕視悲劇價值這一因素,缺少了這一個近似于故事大前提的設定,那么悲劇故事與主體的存在難以到達其存在的意義。以《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亞》這兩部悲劇為例,當人為因素使得大前提缺失,用一句話去概括所提到的兩個悲劇之時,無疑可以簡寫為扁平的“殺父娶母”與“殺子報夫”這兩個與人倫道德相背離的詞語。而這兩個詞語,令人驚詫恐懼還來不及,更難以說到感動、震撼人心。故而,俄狄浦斯試圖逃避命運詛咒、美狄亞追求愛情與自我的大背景的設定,從這方面來講,使得這些看似荒謬的故事內容得以傳誦與流傳。
另一個方面,悲劇主體的任務和作用也是極大的。作為故事的執行者,悲劇主體就像是故事大前提下的小小齒輪,延續著主基調,看似偶然實則必然的在一個個“突轉”與“發現”中走向被作者既定的命運。對于悲劇主體來說,常常可以被分為這兩大類型:一、凡是那種積極主動去行動的悲劇人物,幾乎無例外地具有“主體動機與結果完全悖反”的悲劇性現象;二、凡是那種由外部矛盾的糾纏而卷入到命運的可怕漩渦中的悲劇人物,都陷入了無從選擇的“兩難”絕境的悲劇之中。就《俄狄浦斯王》和《美狄亞》這兩部古希臘悲劇而言,從內容上來看,《俄狄浦斯王》是一部命運悲劇,《美狄亞》則是一部家庭性悲劇;而對應上述悲劇主體的分類來講,俄狄浦斯是前者的典型代表之一,即“主體動機與結果完全悖反”這一類形象,美狄亞則同時兼有兩種類別。
由此可以得到這樣一個結論:當已經構造好大前提和主體的時候,主體角色的多重性與矛盾性,好似齒輪間的潤滑劑,推動著故事的不斷前進。
二、俄狄浦斯、美狄亞身份的多重性與矛盾性分析
如果將悲劇價值與悲劇主體的設定,比作是畫布上背景與人物站位的確定,使故事的一切井然有序的話;那么悲劇主體其各自角色的扮演與沖突,則像是畫面上的各種細節的描繪,是具體展現畫意、打動人心之所在。
在《俄狄浦斯王》這一部悲劇中,悲劇主體俄狄浦斯的角色設定是多重的。對于社會來講,他既是國王又是罪人;對于他的親人來講,他既是孝子又是逆子,既是丈夫又是兒子,既是父親又是兄長;對于他的命運來講,他既自以為幸又實為不幸。他的身份里,每一個角色都有相對的另一面,并且是與對應角色有著絕對沖突的另一面。這樣極端的多重角色與多重沖突所帶來的沖擊力度,毀滅掉俄狄浦斯的希望與生命,也毀滅掉他高大全的英雄角色。
若將俄狄浦斯的角色沖突總結為 “面對同一對象其角色的沖突”,那么在《美狄亞》這部悲劇中,美狄亞則是“角色間沖突”的主體形象。談美狄亞的故事,不應該回避她在《金羊毛》中的形象,當兩個故事聯系到一起來總結的時候,美狄亞的角色也就這么得以展現了。將她歸結尾“角色間的沖突”是因為她的矛盾一直體現在她所擁有的角色與她作為伊阿宋愛人或是妻子這一角色的沖突。表現在她的國寶金羊毛與伊阿宋的愛的沖突,她的公主身份與伊阿宋的妻子的沖突,她的家庭、親人與伊阿宋的妻子的沖突,她的母親身份與她的妻子身份的沖突。只不過在每次的沖突中,無論是追隨還是報復她都選擇了與伊阿宋相關的那一方行動,到最終導致殺子報仇的行為。
對于角色的多重與矛盾,這兩部悲劇都各自加以展現,二者有別的地方除了前文所總結的沖突類型之外,對于沖突的發生也有差異。《俄狄浦斯王》的沖突是冥冥注定的,從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生子、登上王位那刻起就已經發生,只是一直未被揭露;而美狄亞的悲劇中,沖突是伴隨著事件發展和美狄亞的愛這兩條線索依次產生。
三、認知中的感性與理性并存與俄狄浦斯、美狄亞的角色沖突
基本上,人對于一件事物的認知是感性與理性并存的,在認知心理學領域,感性認識與理性認識被理解成為不同的認知階段。從特點上看,感性認識是直觀的、形象的、融入個人感情的,理性認識是基于概念、判斷、推理這三個過程的。與之相應的,讀者對于悲劇中故事、人物的認知亦是如此。而悲劇主體角色的多重與矛盾性,在感性并于理性的讀者面前所召喚出的悲劇效果,也隨之加劇。
在俄狄浦斯與美狄亞各自的悲劇中,其體現為:理性上,人們認識事物是發展運動的,故而命運是未知的、愛情是多變的;然而在感性中,對于同類間命運與愛情的難以掌控的背景所產生的悲劇背景,能夠使得讀者為之悲憫或是感同身受。理性上,俄狄浦斯殺父娶母,美狄亞殺兄背父,又殺子報夫,有悖于為人兄弟子女父母的身份,都是違反人類現有倫理,聽來十惡不赦之罪過;感性上,讀者清楚事情的來龍去脈,俄狄浦斯與美狄亞自身的遭遇,明白他們各自的不幸以及做這些事的因由,即減弱了人們對其行為的反感,增加了對其的悲哀,也增加了人物本身的爭議性。理性上,他們各自扮演的角色是不可避免的存在,而他們基于角色定位做出的行為選擇也從某方面講是必然結果;感性上,因為讀者對于人物最終的毀滅、生命與愛最終的毀滅本能的不忍,故而被強迫接受如此沖擊性的故事和結局,悲劇效果也不免增加。
在這里,角色的沖突是一組矛盾,而感性與理性的信息接受又是另一組矛盾,讀者在接受過程中自身矛盾的產生,使得悲劇能夠更好的為更多的人內心所了解也為更多的人所接受。
綜上,悲劇人物的自身角色沖突本來就是戲劇沖突中表現得十分激烈的部分,在傳遞信息時就具有強大的悲劇效果;而讀者在接受這樣一個信息的時候,因為本身感知過程中存在的特性,使得角色沖突中的悲劇成分放大。兩者的結合,使得悲劇在悲劇價值的總括、在悲劇主體的執行、在讀者自身的接受這三者同時出力的情況下吸人眼球,進而引發讀者群的悲痛、憐憫與恐懼。正如我們讀過《俄狄浦斯王》后,感慨命運的作弄與難以掌控,為俄狄浦斯悲憫卻也為自己曾經的、現在的未來經歷惶恐一樣;如我們讀罷《美狄亞》后,感慨愛情弄人,憐憫這出婦女心靈的悲劇,卻也可能產生對愛的懷疑一般,悲劇以其強大的力量使得讀者融入故事滋生同情憐憫,也使得讀者與故事人物分離感慨恐懼自身,這其中不乏悲劇主體的多重角色與其角色間的矛盾沖突的作用。
(華中師范大學文學院2013級漢語言文學試驗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