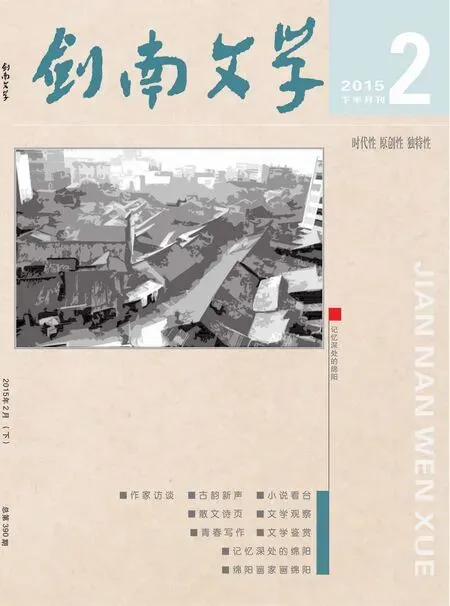《寵兒》中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在結(jié)構(gòu)、時(shí)間和空間的體現(xiàn)
■宋清濤
本小節(jié)主要對(duì)托尼·莫里森的作品 《寵兒》中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寫(xiě)作手法進(jìn)行分析。盡管莫尼森本人認(rèn)為這種認(rèn)知是對(duì)她作品的誤判,過(guò)于以偏概全,然而大多數(shù)文學(xué)家和理論家還是認(rèn)為這部作品主要展現(xiàn)了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寫(xiě)作手法。因而,在分析作品時(shí)我們應(yīng)對(duì)被假定的《寵兒》與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之間的關(guān)聯(lián)性有一個(gè)更深層次復(fù)雜的探討。此處我們將從小說(shuō)的結(jié)構(gòu)、時(shí)間、空間和身份上來(lái)分析《寵兒》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手法。
1.結(jié)構(gòu)上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
評(píng)論家弗洛雷斯(1995:116)指出:“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實(shí)踐者們依附于現(xiàn)實(shí),似乎是為了防止‘文學(xué)’介入他們的方式,防止他們的虛構(gòu)像神話中一樣偏離到超自然領(lǐng)域。敘述在精心準(zhǔn)備著,而情節(jié)日益激烈,最終可能導(dǎo)致不明確和混亂局面。”與此相同,《寵兒》的作者在精細(xì)布置一個(gè)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陰謀的同時(shí),其劇情激烈程度也在日益加深。劇情從小說(shuō)一開(kāi)篇就顯得尤為激烈,作者引用了一些極具吸引力的片段和處于特殊情況下的人物,這都會(huì)引起讀者的興趣和好奇:貝比·薩格斯的死亡,霍華德和巴格拉的逃跑,塞絲和丹佛的與世隔絕以及房子里有冤魂出沒(méi),等待凈化。跌宕起伏的劇情也隨之展開(kāi),更多的答案等待著讀者在之后的故事中尋找。在以下兩頁(yè),旁白更戲劇性的聲明關(guān)于貝比·薩格斯“無(wú)法忍受的”過(guò)去(莫里森,寵兒[1987]1997:4),房子的“粗暴的行為”(4),以及兇手用“割喉來(lái)謀殺嬰兒”(5),母親“在墓碑雕刻間挖槽”(5)以使寶寶的名字至少七個(gè)字母能刻在墓碑上,被稱(chēng)為甜蜜的家的有著苦澀記憶的地方,那個(gè)在塞絲的背上刻上野櫻樹(shù)形狀疤痕的殘忍的男人強(qiáng)行把她的奶水奪走,以及保羅的照料…故事第一章激發(fā)了對(duì)上述發(fā)生事情之間的關(guān)系的進(jìn)一步敘說(shuō)。而在下面的章節(jié)中,對(duì)故事情節(jié)的敘述也逐漸零星展開(kāi)。他角色的記憶穿梭,意外的組成了一個(gè)多重性的圖像和錯(cuò)綜復(fù)雜的回憶。小說(shuō)中的每個(gè)片段具有一種獨(dú)特性質(zhì),因?yàn)樗从沉苏w故事的一個(gè)角度,幾乎奇跡般地組成了一個(gè)完整的敘事方式。當(dāng)塞絲試圖對(duì)保羅·D揭開(kāi)她的故事時(shí):
“她在轉(zhuǎn)圈。一圈又一圈,在屋里繞著。繞過(guò)果醬柜,繞過(guò)窗戶,繞過(guò)前門(mén),另一扇窗戶,碗柜,起居室門(mén),干燥的水池子,爐子——又繞回果醬柜。保羅·D坐在桌旁,看著她轉(zhuǎn)到眼前又轉(zhuǎn)到背后,像個(gè)緩慢而穩(wěn)定的輪子一樣轉(zhuǎn)動(dòng)著。 ”(159)
在閱讀敘事故事片段的時(shí)候,讀者幾乎可以等同于保羅·D這個(gè)聆聽(tīng)者的角色。塞絲在房間里一邊說(shuō)著一邊移動(dòng),在她講述他整個(gè)故事時(shí),頻頻出現(xiàn)和消失在保羅·D的視線范圍。讀者會(huì)在整個(gè)小說(shuō)中陸續(xù)找到前25頁(yè)中提出的問(wèn)題的答案,發(fā)現(xiàn)越來(lái)越多的細(xì)節(jié):塞絲為什么以及如何殺害的寶寶?為什么貝比·薩格斯在死之前一直在琢磨顏色?為什么塞絲和丹佛感到寂寞?學(xué)校老師來(lái)整治后,甜蜜的家到底發(fā)生了什么事情?為什么西克索只是在結(jié)尾的時(shí)候笑過(guò)一次 ?(23)他又是為什么停止說(shuō)英語(yǔ)? (23)。此外,重復(fù)的敘述有利于強(qiáng)度的增加,越來(lái)越多的信息被添加到特定的角色的故事中。
2.時(shí)間上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
分散而重復(fù)的敘述是符合現(xiàn)實(shí)主義文本的另一個(gè)特點(diǎn)。首先,正如評(píng)論家溫迪B.法里斯(1995:173)所說(shuō),“時(shí)間感貫穿整個(gè)文章”和“重復(fù)敘事原則,配合鏡子或其他象征性結(jié)構(gòu)類(lèi)似物,創(chuàng)建一個(gè)神奇的移動(dòng)參考物”(1995:177)。 在作品《寵兒》中,時(shí)移幫助模糊現(xiàn)在和過(guò)去之間的線條。本小說(shuō)以124號(hào)房子開(kāi)始,這是一個(gè)被正式釋放的奴隸的住宅,奴隸制所帶來(lái)的痛苦不愿想起的回憶總是不知不覺(jué)困擾著他們。雖然角色在試圖刻意的抹去過(guò)去的回憶以尋求逃離折磨的途徑,但記憶總是突然閃現(xiàn)在他們的腦海中。他們不得不面對(duì)他們的“記憶重現(xiàn)”的過(guò)去和現(xiàn)實(shí)的重疊。
時(shí)間感的扭曲是來(lái)源于某種悲慘經(jīng)歷后產(chǎn)生的一種情況。在《寵兒》中,這些受奴役者曾經(jīng)所承受的痛苦始終存在著,并使他們的時(shí)間意識(shí)不斷減弱。連續(xù)不間斷的雨暗示了保羅D在做鎖鏈囚犯時(shí)受到的持續(xù)不斷的折磨。不管事情如何變化,不論周?chē)澜缫咽鞘裁磿r(shí)間,雨都沒(méi)有停止。
下雨了。
蛇從短針?biāo)珊丸F杉松樹(shù)上爬下來(lái)。
下雨了。柏樹(shù)、黃楊、白楊和棕櫚經(jīng)歷了五天無(wú)風(fēng)的大雨,垂下頭來(lái)。到了第八天,再也看不見(jiàn)鴿子了;到第九天,就連蠑螈都沒(méi)了。狗耷拉著耳朵,盯著自己的爪子出神。男人們沒(méi)法干活了。鎖鏈松了,早飯廢除了,兩步舞變成了稀乎乎的草地和不堅(jiān)實(shí)的泥漿地上面拖拖拉拉的步伐。”(109)
保羅·D鎖鏈囚犯的生活是一種生不如死的情形。作為一個(gè)奴隸,他不能衡量和管理自己的時(shí)間。監(jiān)督者根據(jù)他的勞動(dòng)情況來(lái)安排他的生活。另外一個(gè)角色西克索,也有一種無(wú)法控制時(shí)間的扭曲感,這象征性地體現(xiàn)在小說(shuō)中,即便他嘗試用計(jì)時(shí)的方法去煮土豆,一整晚仍未成功。“時(shí)間從來(lái)不會(huì)像西克索想象的那樣工作,所以他當(dāng)然從來(lái)沒(méi)有成功過(guò)”(21)
小說(shuō)中的人物們被困在這樣的一個(gè)無(wú)止境的循環(huán)中,時(shí)間無(wú)法被測(cè)量,被過(guò)去的痛苦所束縛,無(wú)法享受現(xiàn)在也無(wú)法建設(shè)未來(lái)。“翻滾”(6)的記憶。塞絲知道當(dāng)她告訴保羅·D關(guān)于她的故事時(shí)“她圍繞著房間、他,以及這個(gè)話題轉(zhuǎn)的圈,也會(huì)是其中一個(gè)”(163)。
3.空間上的魔幻現(xiàn)實(shí)主義
跟時(shí)間一樣,空間在魔法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中也很難把握和衡量的。羅頓·威爾遜(1995年:215)寫(xiě)道:
“空間,我們了解其最原始的感覺(jué)在文學(xué)中好像是無(wú)處不在,但是卻很難精準(zhǔn)到位。似乎沒(méi)有一個(gè)詞匯能大到足以用來(lái)討論空間。你可以大談指示詞,共存,協(xié)調(diào),距離,表面,車(chē)身,內(nèi)飾,體積和可塑性,但缺乏計(jì)量單位:文學(xué)空間中的概念,不能被測(cè)量,但它可以被感知。”
在《寵兒》這一作品中,托妮·莫里森通過(guò)創(chuàng)造一種空間的扭曲的感覺(jué)實(shí)現(xiàn)了對(duì)空間不可測(cè)量性的證實(shí),角色經(jīng)常缺乏屬于自己的一席之地。保羅·D到達(dá)124號(hào)時(shí),他說(shuō),“這些天我去任何地方,任何一個(gè)能讓我坐下的地方“(7)。當(dāng)寵兒在124號(hào)出現(xiàn)的時(shí)候,保羅·D無(wú)法在房子里找到一個(gè)舒適的地方。每當(dāng)他變換位置或移動(dòng)時(shí),例如從塞絲的房間到一把搖椅,再到貝比·薩格斯的房間,最后到儲(chǔ)藏室,他的情況都以同樣的敘述在重復(fù)著:“它以這樣的方式進(jìn)行而且本可以繼續(xù)這樣下去,但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飯后,他跟著塞絲來(lái)到樓下,坐在搖椅上,并不想待在那里“(115)。下面的段落以類(lèi)似的方式開(kāi)始:“它以這樣的方式進(jìn)行而且本可以繼續(xù)這樣下去,但有一天晚上吃完晚飯后,他跟著塞絲來(lái)到樓下,躺在貝比·薩格斯的床上,并不想待在那里”(115)。此外,角色會(huì)突然從一個(gè)地方移動(dòng)到另一個(gè)地方,不僅在身體上,同時(shí)也是在心理上。例如,當(dāng)塞絲講述她殺嬰的故事時(shí),保羅·D并沒(méi)有將談話繼續(xù)下去,雖然他也想知道塞絲更多的經(jīng)歷。他克制是因?yàn)檫@令他回憶起了在佐治亞阿爾弗雷德被監(jiān)禁的日子,為了擺脫這種記憶,他改變了談話主題。
當(dāng)讀者閱讀《寵兒》時(shí),其實(shí)也會(huì)產(chǎn)生一種空間的扭曲感,伴隨著對(duì)于小說(shuō)后面情節(jié)的不可預(yù)知。這種扭曲感也是奴隸們的境遇,他們就“像跳棋一樣”被任人擺布(23),不知道接下來(lái)的幾個(gè)小時(shí)或是幾天他們會(huì)在哪里,因?yàn)槿魏稳穗S時(shí)可以送他們離開(kāi)或把他們賣(mài)到任何地方。作為被商品化的人類(lèi),他們“租出去了,貸出去,買(mǎi)了帶回,存儲(chǔ),抵押,贏了,被盜或扣押”(23)。
然而,為了抵抗這種扭曲感,主人公塞絲拒絕去任何其他地方,她說(shuō),“"我后背上有棵樹(shù),家里有個(gè)鬼,除了懷里抱著的女兒我什么都沒(méi)有了。不再逃了——從哪兒都不逃了。我再也不從這個(g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逃走了。”(15)。而寵兒的魂魄,在游蕩了許多地方和空間后,也最終設(shè)法找到了塞絲并和她一起住在124號(hào),回歸到這個(gè)讓她有歸屬感的地方。寵兒的經(jīng)歷其實(shí)是介于活人和死人之間的重疊空間。當(dāng)?shù)し饐?wèn)寵兒,“那邊什么樣兒,你過(guò)去待的地方?”(75)時(shí),大概指的就是死后的空間,寵兒把那個(gè)空間形容為“滾熱”。下邊那兒沒(méi)法呼吸,也沒(méi)有地方待……成堆成堆的。那有好多人,有些是死人“(75)。首先,丹佛以及讀者,設(shè)想其為某種煉獄,一個(gè)我們來(lái)世的地方。接著,《寵兒》將其描述成了有詳細(xì)情境的奴隸船。
(內(nèi)蒙古科技大學(xué)外國(guó)語(yǔ)學(xué)院)